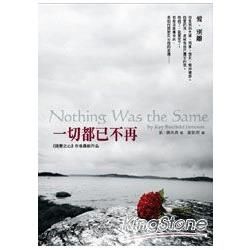愛.別離
他是我的夫婿、同事、朋友、精神導師。
他愛的我,是被我自己遺忘的我。
他病了,就要死了。
他無法教導我的,是如何面對失去他的哀傷……
作者以真摯而抒情的文字,回顧與丈夫理查之間的深刻感情,以及陪伴理查抗癌的漫長過程。書中交織著許多幽默風趣的小故事,以及兩人既濃烈又溫馨的感情所留下的苦甜回憶,緩緩訴說作者如何透過丈夫的勇氣與風範,學習到盡情發揮生命。
以死亡、哀傷、喪親為主題,作者從自身的哀傷經驗,以精神病理學的角度分析人類的哀傷,並以過人的文采,寫成一部感動人心的回憶錄。
如詩般優雅,既華麗又哀傷
這是一部傑出的散文長卷,深摯,優雅,華麗,哀傷。─陳義芝
作者簡介:
凱‧傑米森 Kay Redfield Jamison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精神病理學系教授、約翰霍普金斯情緒失調疾病中心共同主任,以及蘇格蘭聖安卓斯大學榮譽英文教授,著有享譽國際的《躁鬱之心》、《夜,驟然而降:了解自殺》(Night Falls Fast)、《熱情洋溢》(Exuberance),以及《為火所染:躁鬱症和藝術特質》(Touched with Fire)等書,也曾與他人合著躁鬱症教科書,或以情緒失調疾病、創意、精神病藥物學為主題,獨立或與他人共同撰寫百餘篇論文,並獲頒麥克阿瑟獎學金等美國與國際性科學獎項。
章節試閱
一天下午,我們坐在長凳上俯瞰太平洋,像蜥蜴一樣曬著太陽,隨便聊些周遭不重要的小事。過了一會兒,他用平靜的語氣說:「我們該談一下喪禮了。」我盡力不讓聲音哽咽,但卻難以自制。
「對,當然。」我說。
陽光下的寧靜氣氛中,理查的提議似乎有些突如其來,但也不完全在意料之外。我們剛見過歐勒牧師,我住洛杉磯時常去聖公會教堂,他是那裡的牧師,我認識他二十五年了,彼此十分親近,理查也非常喜歡他。我和理查當年在仙納度山谷鎮公證結婚後不久,又在魏斯伍德區的聖阿爾班聖公會教堂舉行婚禮,就由歐勒牧師主持。那天稍早,我們找他討論接下來幾個月必須做的事,也在理查的要求下討論喪禮上使用的音樂與詩篇。現在理查和我坐在長凳上俯瞰太平洋,景色美得出奇,我們繼續討論聖詩、抬棺者,以及人生最後旅程的某些古老儀式。上帝灑在我們身上的陽光再怎麼溫暖,也驅趕不了當時心中的寒意。
……
秋天接近尾聲,理查興致勃勃期待著獅子座流星雨。……我們清晨四點半起床,驅車進入岩溪公園,園內已擠滿車輛;華府市民也許對已人性感到厭倦,但對美麗的事物依然敞開心胸。流星雨的璀璨壯麗果然不負眾望:綠光、白光、藍光爭艷,熾然劃過天際,與來回巡邏的空中預警機的閃爍燈光交錯。一顆顆流星在遙遠的空中爆炸,從四面八方飛馳而來,我心想著:這一切多麼完美,我們一起觀賞這撼動人心的美。理查能活著看到這一切,又是多麼完美的事。這是上天為理查的美德所賜予的禮物。我們抓住隕落流星的片段,收藏起來,留給未來的日子。
流星雨劃過岩溪公園上空時,理查平靜卻感性地說:好美,好短暫。……我們在公園裡坐了很久,看著流星許願,帶著甜蜜忘情地親吻彼此。凝視星野,或許會讓人因為自己在宇宙中的渺小而感到恐慌,但那不是此時的感受。這個夜晚,大自然展現了令人醉心的絕美,而我們倆共同見證了這一切。此時此刻是我們生命珠鍊上的一顆珍珠,無論任何代價,我都不願交換這顆珍珠,或是這晚的吻。
這個耶誕季交織著燈火、耶誕歌,以及友情。理查的狀況尚可,但我們都知道這可能是兩人最後一個耶誕。儘管如此,或許正因為如此,氣氛卻不像去年緊繃;也許是我們已懂得接受,也許是我們已將死亡帶來的負面思考都過濾掉了。這畢竟是歡慶的時節,布置耶誕樹是快樂的工作,每掛上一個吊飾,沈重的陰霾就少一些。我們大多在火爐旁度過這些夜晚,理查總說:「凱,用你的巧手生一盆火如何?」然後我們和母親聽耶誕歌,聊天,啜飲紅酒,凝視火焰,恍惚而快樂。未來並非不重要,只是暫時擱置一旁。理查即將離開,母親逐漸垂老,連狗兒南瓜也白了鼻頭、步履僵硬,儘管如此,我們仍擁抱這一切。我們各自有不同的生命危機,卻也知道必須珍惜此刻。
「哀傷嗎?」有人問詩人登恩關於妻子去世前最後的時光,他說:「確實哀傷。卻也美好。/空氣中有一種寧靜。時間也凝結了。」
和過去每年一樣,我們開車在社區內欣賞耶誕燈火,在耶誕夜看《主教之妻》。理查慢慢品嚐梅子布丁,一邊叨叨絮絮發表意見,說著洛麗泰楊為何不該留在大衛尼文身邊,應該和卡萊葛倫私奔。每年我都會說:「跟大衛尼文比起來,你比較像卡萊葛倫。」也總是真心地說:「跟你比起來,卡萊葛倫差遠了,你是我見過最帥的男人。」
理查看起來總比實際歲數年輕,如今瘦得令人擔心,頭髮也不再濃密烏黑,容貌已洩露出年紀。我靠過去吻了他:「你依然是我見過最帥的男人。」
他對我微笑,但我看到他眼中有淚。
「真的嗎?」他問。
「到目前為止。」我說:「到目前為止。」
日子安穩地過去。冬天的第一場雪下得厚軟,點綴出一月中旬的美景,也把公園和家中的庭院和樹木覆蓋成一片雪白。理查睡得更多、吃得更少,但只要陪在熟睡的他身邊,我便感到倆人的小小世界依然美好。理查仍維持兩個月回診一次,左肺出現了輕微浸潤,艾廷格似乎並不擔心,我則不太樂觀,但我畢竟不是腫瘤醫師。艾廷格認為理查病況「穩定」,並建議延續同樣的療法。恩博德到艾廷格的辦公室探望我們,理查還算合理的健康讓他相當開心。理查說:「每次你看到我還活著好像都很驚訝。」恩博德笑笑,沒有否認。
理查在情人節那晚帶我到家附近的義大利餐廳吃晚餐,氣氛嚴肅又哀傷。這是我們唯一一次討論他死後我會怎樣,顯然他事前已經反覆思考過了,他先說他有多麼愛我、我讓他多麼快樂,他希望走後依然在天上照看我,但我知道他並不相信這些。不過,他確實相信愛可以產生恆久的力量。他說:「你有好朋友、家人、同事,還有一個好醫師、好工作,這些都很重要。你必須自己照顧自己,必須好好吃藥、好好睡覺,以後沒有人在身邊提醒你了。」理查的話似乎經過反覆演練,說完了便不知何以為繼。
「但沒有你我該怎麼辦?」我問他:「我該怎麼辦?」
理查挪到我身邊坐下,雙臂環住我。「我不知道。」他說:「但你一定會好好的。」
自理查三年前確定罹患淋巴癌以來,我不曾在他面前哭過,這天淚水卻不斷滑落面頰。理查拿出情人節禮物,大概想讓我開心些。第一個禮物是國家衛生研究院的檔案夾,封面是個尖嘴玻璃量杯,他還貼了紅色與粉紅色的大愛心,看起來滑稽極了,但我好喜歡。檔案夾裡是兩張紙,一張是他手寫的《癌症故事》謝辭,非常直截了當,非常理查風格:「獻給凱,沒有妳就沒有我。」
第二張是十五年前他寫給我的信的影本,那時我住在倫敦,正深陷於一段揮之不去的憂鬱期。一天晚上他從華府打電話給我,因為我痛苦的程度而憂心忡忡;他很想知道,當我跌落谷底、無比絕望時該如何幫我。他說,他了解的是醫院裡的憂鬱症,不是家裡的,因而也不知所措。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四
致 凱•傑米森博士
碧歐佛爾特花園三十四號
倫敦S.W.3
英國
我最親愛的凱:
我看過綠色的冰、十分鐘的撤軍,但昨晚我聽到的是全然的黑暗。十二歲那年,我去肯德基看長毛象洞穴,導遊說那裡的黑比全黑還要再黑二十度,我一直沒聽懂,始終無法從科學角度理解這句話,但我現在感受到了,那就像吞噬所有光線的黑洞。我感覺自己的生命力透過電話線被吸光了,但我很樂意能夠付出。可惜物質不滅定律在這裡並不適用,從我體內離開的生命力,並未轉移到電話的另一端,好似物質與能量徹底消失,喚回了記憶深處最原始的孩提夢魘。
陪在你身邊似乎是唯一的答案。那樣我就能看見你,可以幫你蓋毛毯,在你床邊放一杯水,幫你找鋰鹽和甲狀腺劑,並且在必要的時候向外尋求幫助。我需要指引,我需要知道何時該開始擔心?憂鬱發作時,比較要緊的是時間的長短、憂鬱的程度,或是兩者的綜合?如果我問妳吃藥了沒,該問得多具體?如果詢問你攝取的食物或飲料,得問多少卡路里或多少杯嗎?有哪些指標代表你用藥過量?在洛杉磯可以找奧爾巴醫師,那麼在倫敦該找誰?安東尼•史脫嗎?達林頓嗎?
我不喜歡黑洞的存在,但很高興我看過了。當你愛上行星,就得接受日車、黑洞等等的一切。
愛妳的 理查
我重讀他多年前寫的這封信,想著我們在這條相互了解的路上已經走了這麼遠,能夠擁有彼此是多麼幸運,而他老是寫錯別字也依然讓我發笑。我帶著鼻音告訴他:「跟正確的『日暈』比起來,我比較喜歡你寫錯的『日車』。」他看看信,說:「這個嘛……,我看起來沒錯呀!」一輩子的閱讀障礙不曾打擊他的信心,他很確信某些字就是該長某個樣子。
他提到最後一段文字,說他一直將我視為火熱的行星,又拿出一個小盒子遞給我。「這個是為了紀念你的日暈和黑洞,還有華府上空屬於我們的流星雨。」盒子裡是一只金戒指,上面有十六個小星星,他拿戒指沾了紅酒,戴在我手指上,旁邊是婚戒和他在羅馬送我的戒指。
「敬行星!」他說。
我曾將一本著作獻給理查,在獻辭中引用拜倫的詩作《唐璜》:「以望遠鏡與蒸氣的力量發現行星並逆風航行的人,向他們致敬!」
「敬你!」我說:「敬安全的航行。」
……
理查的病況再度惡化。兩個星期內,他呼吸困難的狀況更嚴重,體重掉了將近五公斤。他感染肺炎,幾乎沒進食,也睡得更多。每天,我眼看著他的生命逐漸流失。我們在死亡逼近之際彼此相守,這種親密是無法想像的體驗,同時明白,終點已經迫近。我們相擁而眠,敏銳感知對方體內的任何動靜。這是我們親密而綿長的道別。
四月中,艾廷格說理查的病已出現「進一步的狀況」,斷絕了我們任何一絲希望。鮑伯安排理查參加喬治華盛頓大學醫院的實驗性藥物試驗,並把病歷和掃描紀錄寄給范德比爾特(Vanderbilt)大學的一位基因治療師。理查也申請在秋季參加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疫苗療法,但他可能無法活那麼久了。……理查的體力不斷衰竭,坐在電腦前的時間變短,因為舉步維艱,很少下樓來。朋友更頻繁來訪,但停留的時間卻變短了。
從那時起,寧靜的夜晚與凌亂的白天交替而行。我們靜靜等待,懷抱著希望對抗已知的現實。理查的睡眠時間更長了,我躺在他身邊,清醒著。即便他經常都睡著,我仍每天讀幾個小時的書給他聽,朋友和同事也仍繼續前來探望他。四月底,理查和我決定為最親近的好友舉辦晚宴,感謝他們的友情和不斷設法拯救理查的生命。那是最終的筵席,卻無限美好。我在餐桌上放滿長長短短的蠟燭與自種的杜鵑花,準備了萊姆木瓜、糖霜薑、無花果、鮭魚、香檳。在這個閃亮美麗的夜晚,我們與完全知悉現實狀況的朋友聚首,心中備感溫馨。
第二天,我到岩溪墓園挑選理查和我的墓地。理查太虛弱無法前往,但他很瞭解墓園的環境,因為我們曾多次前去觀看聖高登斯雕刻的亞當斯紀念碑。這天是四月的最後一日,園內四處的樹木都盛開著花朵,我站在不同位置打電話給理查,把現場的景象形容給他聽,然後問他喜歡哪兒。後來我們選了一個年代比較久遠的位置,旁邊就是老樹叢,也可以看到蓮花池。理查很高興我們能永遠睡在蓮花池旁;他笑了一下,建議我往後去探望他時可以順便丟隻金魚到池塘裡。這真是件令人傷心的差事。
……
理查和我第一次討論喪禮細節是在加州,五月間又繼續這個話題,只是這回沒有陽光下的長凳,而且也知道來日不多了。我扶起理查,讓他靠著枕頭坐著,我坐在床邊。我們確認他希望哪些朋友負責護棺或擔任招待,誰在喪禮上致詞,誰負責誦讀詩經。……我們把喪禮程序走過一遍,首先是我朗讀《公禱書》(我們在洛杉磯舉行婚禮時也曾朗讀《公禱書》的篇章做為祝福),然後依序播放聖詩,理查最喜歡潔西諾曼(Jessye Norman)唱的〈奇異恩典〉,我們一起聆聽,歌曲結束後,我看到理查臉上有淺淺的笑,他說:「很好聽!就這樣吧!」他自在地笑著,但我卻輕鬆不起來。
日子一天天過去,理查的狀況並未好轉。他睡得更多,雖然有氧氣協助,仍經常喘不過氣,像剛撈出海水的魚那般掙扎著。他對目前這兩種實驗藥物都沒有反應,家裡瀰漫著揮之不去的陰鬱和恐懼。
我再次前往葬儀社,和上次那位服務員討論喪禮。他的態度和善、率真,並向我保證:「我們會好好照顧您的先生。」他說他們曾照顧過名醫霍姆茲(Oliver Wendell Holmes)、前總統羅斯福,還有美國第一位黑人大法官馬歇爾(Thurgood Marshall),以及前總統甘乃迪。我說我先生聽了會很高興,尤其是因為馬歇爾,然後我轉身準備離開。
他說:「過些日子再見。」
我想回答,但我的心已停止跳動。
那是二○○二年六月初,前院的毛地黃茂盛拔高,石牆也爬滿忍冬。我採了滿滿一手粉紅與白色的牡丹花放在臥房裡。我與理查共度了十七個夏天,今年是第一次在六月初見到這麼多的蝴蝶。我想抓隻白色小蝴蝶給理查作伴,不過牠飛得太快了,而且理查說我不該抓蝴蝶,牠們本該在花園裡自由飛翔。
他這麼說著,沒有一絲嫉妒或遺憾。
(摘自本書第四章 流星雨)
一天下午,我們坐在長凳上俯瞰太平洋,像蜥蜴一樣曬著太陽,隨便聊些周遭不重要的小事。過了一會兒,他用平靜的語氣說:「我們該談一下喪禮了。」我盡力不讓聲音哽咽,但卻難以自制。
「對,當然。」我說。
陽光下的寧靜氣氛中,理查的提議似乎有些突如其來,但也不完全在意料之外。我們剛見過歐勒牧師,我住洛杉磯時常去聖公會教堂,他是那裡的牧師,我認識他二十五年了,彼此十分親近,理查也非常喜歡他。我和理查當年在仙納度山谷鎮公證結婚後不久,又在魏斯伍德區的聖阿爾班聖公會教堂舉行婚禮,就由歐勒牧師主持。那天稍早,我們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