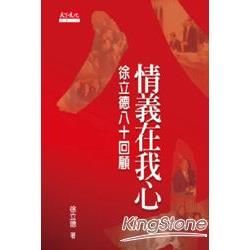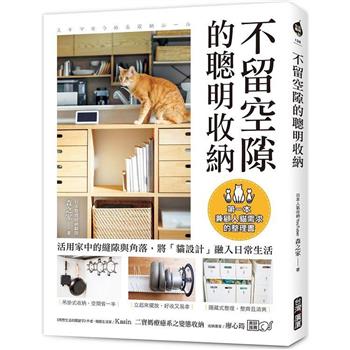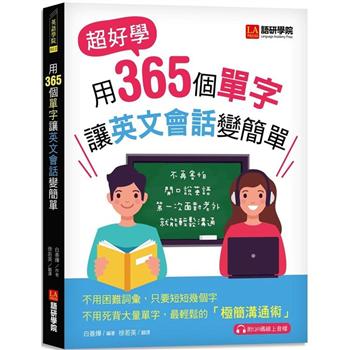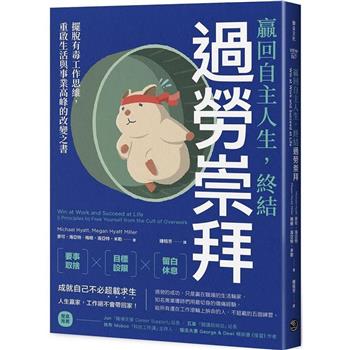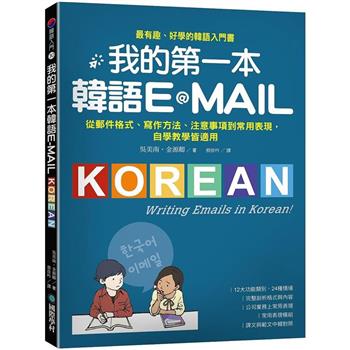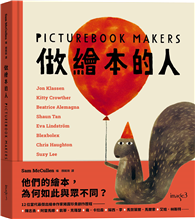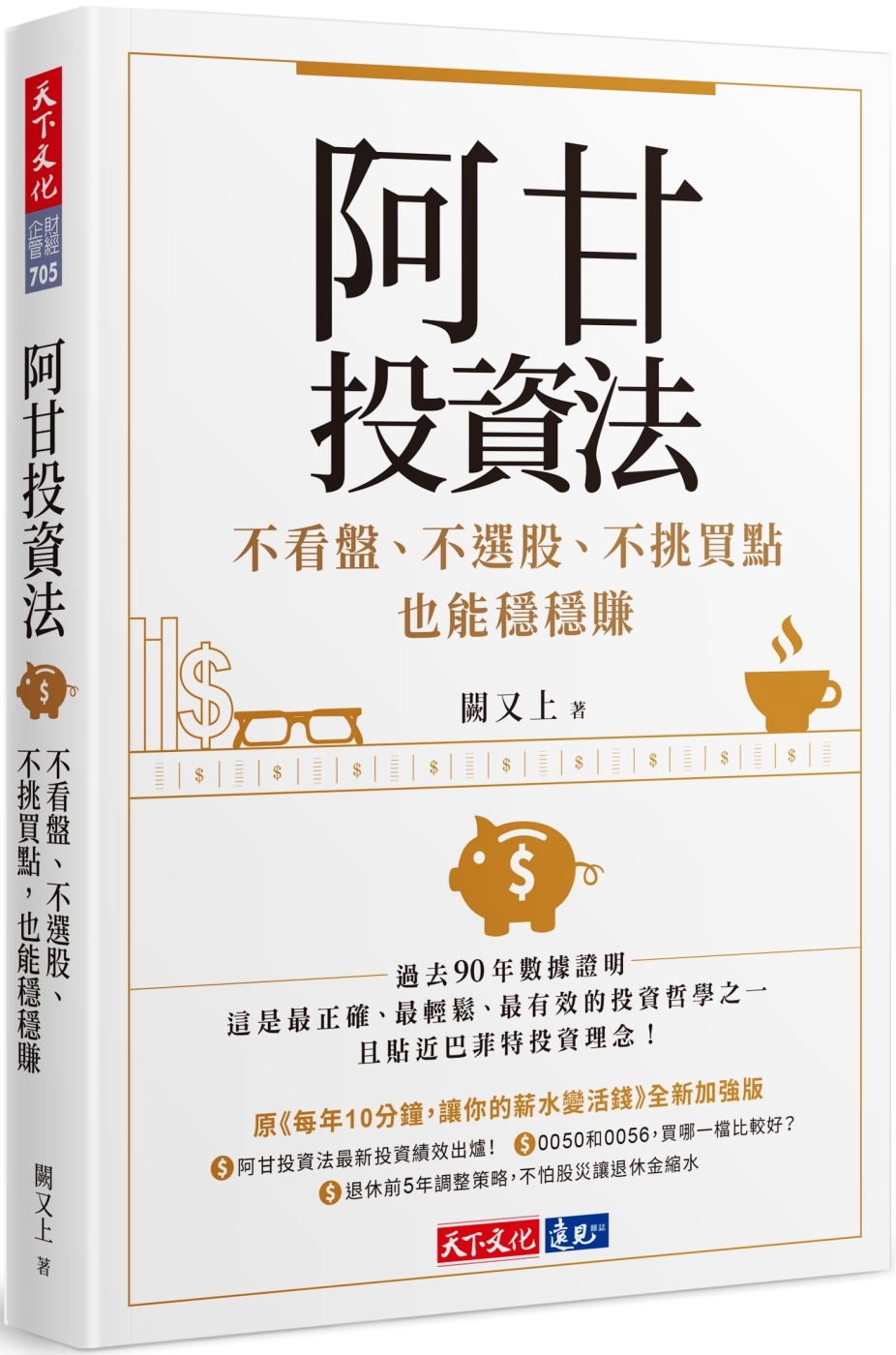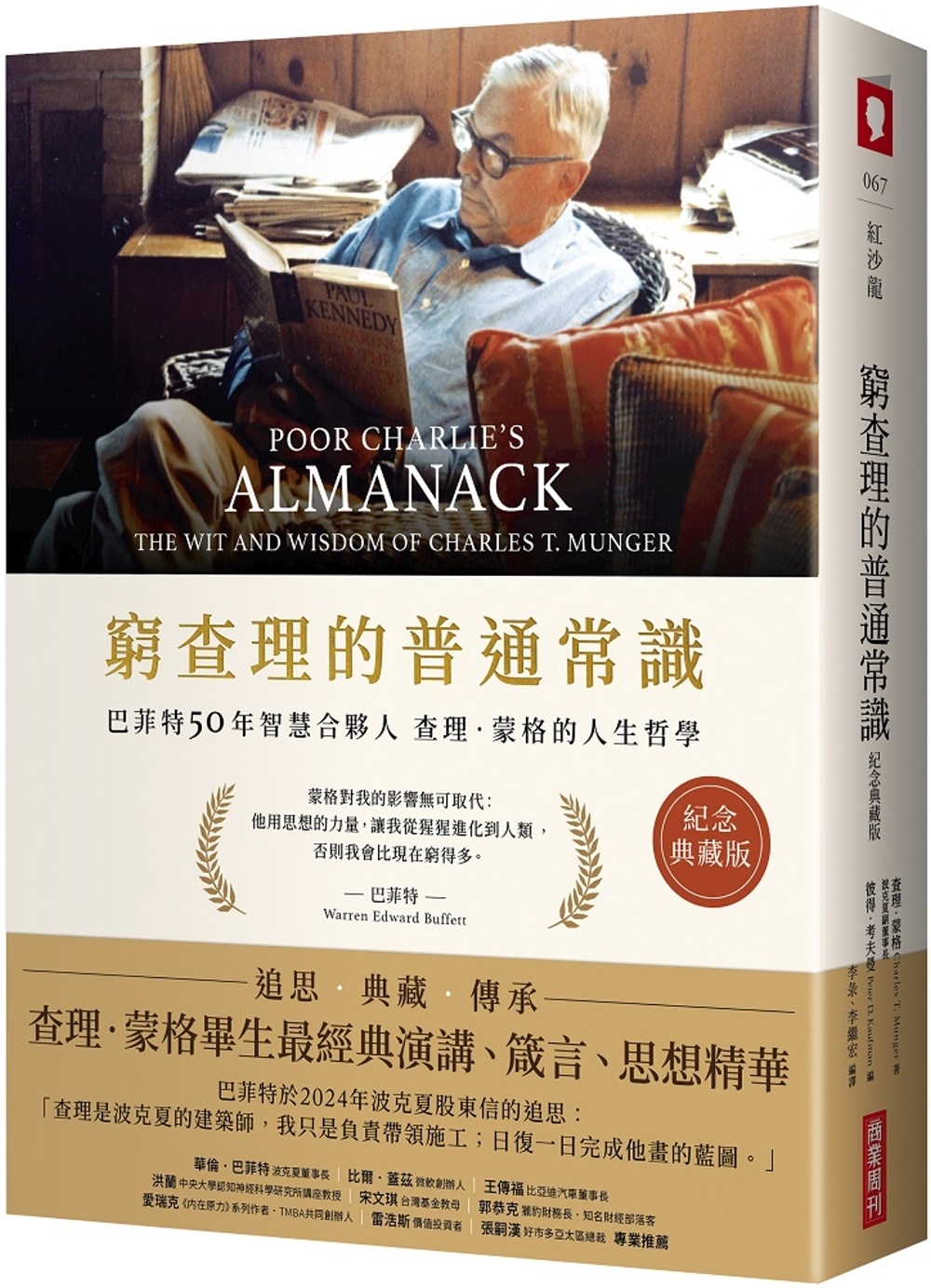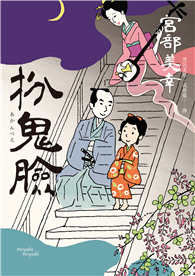出版者的話
成功不必在己—讀徐立德先生回憶錄
高希均
(一)
這本《情義在我心—徐立德八十回顧》新著,將是百年動盪的大時代中,一位重要政治人物在台灣經濟發展、民主轉型與兩岸關係突破過程中的詳實紀錄。它來自作者第一手的分析與直接的參與;兼有現場感與歷史感。
八十年前作者出生於湖北漢口,十四歲隨雙親來台,二十二歲在台灣行政專校畢業,高考及格後分發到考試院擔任薦任科員。他很可能就像大多數公務員一樣,奉公守法、默默工作,然後按部就班地退休。
但是他勤奮好學與力爭上游的個性,以及工作上的優秀表現,在極年輕時就脫穎而出。二十九歲取得了政大政治學碩士,三十一歲就派至美國美利堅大學進修八個月。
四十歲以後就歷任財政部常務次長、省財政廳長。五十歲時,他在事業上達到另一高峰:擔任財政部長、國民黨中央委員,並選為美國艾森豪基金會得獎人。從那時(一九八一年)起,徐先生就在台灣政壇占了一席之地。
從回憶錄第二部開始,他的從政生涯就與台灣經濟發展、國民黨盛衰、李登輝執政、總統大選,及連宋的分與合、兩岸關係的突破,密切相關。關心台灣發展的海內外人士,不能錯過這本書。
(二)
被認為是「青年才俊」的徐先生,擁有很多特質:才思敏捷、有說服力、做事幹練、做人細心、並且潔身自好。他可以廣交四方朋友,但不失分寸;他為了把事情做好,可以委曲求全。他的決策可以有彈性,但把握住原則。
這真是台灣走向民主過程中,政治人物所需要的條件:廉能、認真、肯做事、有效率、會溝通、能調整。
四十歲起,徐先生在財經部會擔任次長,然後擔任財經二部部長,開始逐漸「接近」權力核心人士。除了經國先生,他特別受到孫運璿、李國鼎與費驊三位先生的賞識。然而政治的詭譎多變,五十四歲時因十信風暴坦然辭去經濟部長,雖然問心無愧,但終有壯志未酬,寫出「十信下台功業未竟」的內心感受。文中他寫著:「我極喜愛經濟部這份工作,也認為適合我的個性。當時的確也全力投入,不眠不休地工作,希望在學者專家企業界共同努力之下,有計畫地將台灣的經濟往前推進。」
抱著失落,六月選擇去哈佛進修,那是一段放空自己與放眼天下的難得歲月。一年後得公共行政碩士回到台灣。
我記得那年(一九八六年)暑假在台北,他剛從哈佛回來,聚在一起談起他選過Robert B. Reich、Ezra F. Vogel(傅高義)的課,又細讀Arthur Okun的書:Equality and Efficiency:The Big Trade-off。這些著作也正是我在美國教書時常引述的,我們談得興高采烈。記得曾告訴他:「我的志趣就是推廣這些理念,你的才華就是要把這些理念變成適合國情的政策。」我心中相信這位進修歸來的「哈佛人」,會有更寬廣的奉獻舞台。
等待再被重用的那二年,是他一生中難得的沉潛。
(三)
一九八八年八月,徐先生進入中央黨部擔任國民黨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主席李登輝變成了直接的長官,他更靠近了國民黨的權力核心。
他的事業在六十二歲(一九九三年)時,再攀高峰。那一年二月連戰組閣,他出任行政院副院長(並曾兼任經建會主委一年半)。從那一刻起,徐先生就是權力核心之一。
接踵而來的挑戰一波接一波。台灣的財經與大陸政策,國民黨內部權力的更替,連戰二次參選總統(二000年連蕭配、二00四年連宋配),連戰的「破冰之旅」(二00五年四月),他無役不與;也無不全心投入。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部長、副院長、經建會主委任內推動了不少影響深遠的重大政策(包括推動加值型營業稅制、創設境外金融中心;改組強化中國生產力中心,創立經濟部產業諮詢委員會;推行全民健保、規劃亞太營運中心等等)也以在野之身,策劃連宋配與「破冰之旅」,但自己從不居功。這種「成功不必在己」的風範,在政壇已是鳳毛麟角。
台灣有幾個政治人物是可以立大功、成大業、留名歷史的。可惜在權力巔峰時,他們沒有看清世界潮流,也沒有看清台灣前景,只看到片面的民意,部分群眾的歡呼,身邊人士的忘情慫恿;在權力誘惑下;終至產生一廂情願的推斷,帶來了「一步錯、全盤輸」的結局。可惜的是,因為這幾個人物的政治操作與翻雲覆雨,使台灣社會的進步停滯了二十年。我猜想作者的遺憾是他盡力想對他們有一些正面影響來扭轉大局;但事與願違,帶給他深沉的失落。
(四)
近二十年來,不分晝夜地投入公務與選舉,使他的夫人劉勤生女士十分心痛與不捨。當她於一年前(二00九年)二月往生時,他驀然回首:「我才驚覺對她的依賴如此之深,而她對我的包容,又是如此之廣;……讓家成了溫暖的港灣(堡壘),也讓我在公務上無後顧之憂。……近日每思及此,心中既虧欠又感謝」(引自〈結語〉)。今年二月出版了《劉勤生畫集》,作者又寫著:「她的重要只有在失去之後,才有刻骨銘心的感受。」
老伴的過世,帶來了他沉重的打擊。往日的笑容、豪氣與幹勁突然消失了。自責過去為了工作,沒有常常在家;現在要來補償時間,而她已不在。他沉痛地寫出:「我們未來許多想法與規劃,也都成為夢幻泡影,這種失落與變化,對我來說,實在是無法彌補的缺憾。」心情的鬱卒使他開始研讀哲學與宗教,參悟人生無常的道理。
這是書名中的「情」,這也是他一生的「愛」。
他的全心投入公務,是為了朋友,也是為了國家。這即是他偶然自嘲的「愚忠」。「朋友」是連戰,「國家」是中華民國。
他一直堅信:這個充滿理想的朋友,值得支持;這個充滿顛簸的國家,應當愛護。
十四章「風風雨雨總統大選」的最後一段,出現了他最率真的自白:「在這段人生旅途上,我完全扮演連先生客卿幕僚的角色,並未占有任何名位與酬勞,所作所為都不是分內之事,只是憑著對時局的關懷與私人情誼,來盡自己的力量。」
這是書名中的「義」,這是他政治生涯中一直堅守的「義」。
他關心兩岸和平,他期待國民黨再起,他更希望看到民族復興。這是他在離開公職後,生命的寄托。他往來於兩岸,終於促成連先生展開歷史性的破冰之旅。兩黨領導人的會面,在握手那一刻,開啟了和平之門,機會之窗。連戰主席與胡錦濤總書記發表連胡五項共同願景,更為二00八年接任總統的馬英九鋪了兩岸和平之路。
連先生沒有取得政權,但獲得了民心—台灣與大陸的;歷史地位遠比擔任總統更高。徐先生近十年輔佐連戰的各種犧牲:遭遇的風險、經歷的痛苦、被遺忘的家人,都在兩岸關係突破上獲得了無形的補償:那就是「和平變成了兩岸共同承諾與追求的目標」。在戰亂中成長的他,已把視野與機會提升到民族的融合與發展。
在八十大壽之際,作者回首這段高潮迭起的人生,沒有家世,隻手空拳,卻攀登上了事業的巔峰。偶有風雨,更多藍天。一生不僅無憾、無愧;更是留下了「情義在我心」。
(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
(二0一0年七月三十日於台北)
結語
待參透的人生課題
這本我個人七十八年人生歷程的記述,在許多友人的鼓勵與協助下,尤其是馬紹章先生與陳靜儀小姐的幫忙,的確花了相當長的時間才整理完成,並感謝天下遠見出版公司在我即將邁入八十歲時,大力協助,同意出版發行。
八十歲將屆之前,本來規劃要徹底放下「工作」,開始另一段人生。可是民國九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的巨變,打亂了我一切規畫。勤生因病往生離我而去,不但無法與我分享出書的喜悅,我們未來許多想法與規畫,也都成為夢幻泡影。這種失落與變化,對我來說,實在是無法彌補的缺憾。
勤生與我是大學同學,自民國四十六年十一月結婚以來,五十二年的夫妻情分,不僅僅生活上相互依賴,而且心靈相連,兩人早已合為一體。回想二千年連戰先生代表中國國民黨參與總統選舉失利的那晚,凌晨一時餘,我獨自踏著夜色走回杭州南路家中,勤生獨自坐在客廳中等候我回來,兩人茫然相望,彼此都有無比的辛酸,久久難以置言。
我的妻子在停頓一段時間之後,意味深長地說了一段話。她說:「你的年紀也不小了,一輩子的辛勞,身體狀況也差得很多,應該自公職退休下來,規劃一些自在的生活。」我深受感動。她主張我們立即搬家,就在三個月之內,她獨自張羅,我們遷出住了長達近二十年的杭州南路公家寓所。
自此之後,我雖然婉辭了黨部的職務,卻又投身於環宇公司的經營,並側面參與一些連先生第二次參選與嗣後兩岸聯繫的工作,生活和過去一樣忙碌,陪她的時間並不太多。所幸在我離開公職的這些年,她享受著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習畫、唱歌、旅遊、打球、學習電腦,我也在這段期間,儘可能地陪她與朋友們到國外旅遊,家人與朋友都感受到她的快樂。
不幸的是,民國九十六年發現她患了肺腺癌,在和信醫院醫療團隊的細心照護下,延長了兩年多的生命。兩年多來,我們兩人雖然遭受許多折磨,但也讓我們真正體會到夫妻之間相互依賴與相互關懷的深切情感。
這麼長的歲月,驀然回首,我才驚覺對她的依賴如此之深,而她對我的包容,又是如此之廣;她對家庭的奉獻,又是那麼的多。她所散發的那種安定、知足與守分的氣質,讓家成了溫暖的港灣,也讓我在公務上無後顧之憂。在我一生公職生涯中,她始終默默承受身為公眾人物家屬必須面對的壓力與負擔,儘量把政治隔在家外,把從容與恬靜留在家裡。近日每思及此,心中既虧欠又感謝。虧欠的是,留給她的時間實在太少;感謝的是,她對家庭的付出太多。
從她身上,我深深體會到她對家庭和子女無私的愛,以及中國女性所保有的那種賢慧。更重要的是,她往生後,我對人生有另外一種感受。我原本無宗教信仰,記得在勤生病重最後的幾個月裡,許多朋友勸我們以宗教信仰作為慰藉,承他們的好意,我也閱讀了一些相關的書籍,甚至由他們陪同進了幾次教堂。勤生彌留時,兒子們主張以佛教儀式為她送行,讓她在聲聲佛號中無牽無掛地離開人世間。在作佛事過程中,我進一步接觸佛法,讓我對佛學有些了解與體悟。根據佛法,勤生一生常存善念,行善行,因此必然得以安詳往生。我也相信,善念力量的牽引,能讓她達到更圓滿的世界中,不再有煩惱,不再有牽掛。佛法說:「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無常的生命,有來有去。我用佛法來安慰自己,也減少我對她的掛懷與思念。
經歷這一番刻骨銘心的變化,在我心中,漸漸滋生宗教信仰,希望從中探索生命更深邃的道理。有了這樣的心情,當我再重讀這一部描述我個人過去的一些「人」與「事」的記載時,我有相當多不同的思想與回顧。我既感嘆時代變化的莫測無情,也感受到個人的渺小……
一切生滅原都是因緣。過去將近八十年的歲月,正是中華民族巨變的年代。對日抗戰、國共鬥爭、兩岸的變化,歷史就像巨大的洪流,驅使這一代的中國人向前奔波,有人站上浪頭,有人被浪淹沒。這其間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充滿著悲歡離合;有成就、有幻滅,有幸運、也有悲情。在巨變的時代中,我的確是個幸運兒,因為我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中,求學成長與就業;因為機遇,使我有服務公職的機會,作了一些工作。但是今日檢討起來,我過去所作的工作,雖然努力,相對於許多人而言,論犧牲與貢獻,實在是微不足道,我必須要感恩,要謙卑。
在為人處事方面,雖然有機會奉獻,但因為限於所學以及所處的環境,所見所作還是相當局限。我幼年在大陸出生,就像許多中國人一樣,隨著父母遷居台灣。我所處的年代,很多人都對前途有種未知的惶恐,我們所受的教育,就是擺脫動亂、力求安定與成長,我們所追求的只是一份安定的工作與成長的機會。所以相對而言,我養成一種較保守的性格,努力有餘,開創不足。尤其從小至今,在治學上以實用為先,疏於文史哲理;因此邁入老年之際,深深覺得自己對人生還是缺乏通達,有時也難免流於世俗;面對無常,也常有無措之感,這些都是有待參透的人生課題。最近我常常思索這些問題,還沒有太深入的答案,不過哲學與宗教上的書籍,予我另外一種啟示與體悟。雖已耄耋之年,我認為還是要在求知上有些反思,在為人處世上要有更多的領悟。就像孔子所說,「朝聞道,夕死可矣」。然道在何處?此書付梓之時,讓我以這一種心情,對自己過去作一個總結,也讓我以這些體認,重新展開我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