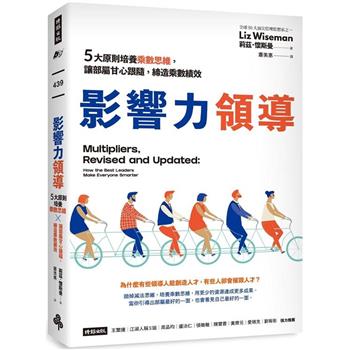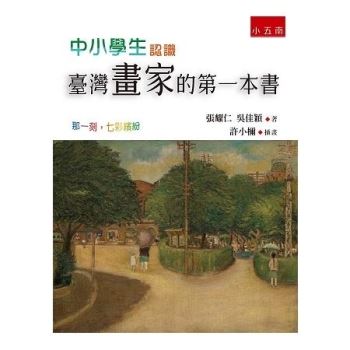令人絕倒的故事,且看時尚俏女郎如何收起Prada,
到法國鄉下拿起油漆刷,暢飲黑皮諾紅酒,享受幸福…
年過35,凱倫決定讓自己的倫敦華麗生活關門大吉,拋下高級公寓、亮麗工作,搬去法國鄉村定居。那裡沒有名牌可買,高跟鞋也無用武之地,等著她的,是需要大修特修的房屋、許多新朋友,和一個接一個的奇怪追求者。當然,還有大把大把的新體驗、新生活--為地板刷上亮光漆、布置花園、用貨真價實的壁爐升火、夏日傍晚騎自行車穿過田野、或是在院子裡小酌一杯餐前雞尾酒……
「幸福不在於多擁有一雙鞋。」我對自己說,著迷地站在巴黎佛布-聖多諾黑路 Roger Vivier精品店的櫥窗前。
幸福不在於多擁有一雙鞋。可是,這雙銀色飾扣的鞋子,高倨在粉紅糖果色的櫥窗裡,魅惑十足地對我眨眼,它們的聲聲呼喚讓人很難招架。
在腦海裡,我一一細數不該買這雙鞋的理由:
1.買這雙鞋的錢,足夠裝一套新的浴室設備。
2.我已經好幾個月沒進帳,信用卡都快刷爆了。
3.一雙新鞋之於我,就好比蠹蛾之於喀什米爾毛衣店一樣。
4.在法國鄉間,螺旋細跟的銀色高跟鞋,功用差不多等同於一雙鞋底破洞的防水長靴。
幸福不在於多擁有一雙鞋。十分鐘後,我離開這家店,手裡提著一只硬挺光滑的購物袋,裡頭裝著那雙銀色的鞋子。
作者簡介:
凱倫‧惠勒(Karen Wheeler)
曾任英國《週日郵報》(Mail on Sunday)時尚編輯,目前擔任《金融時報消費雜誌》(Financial Times How to Spend It)與《每日郵報》(Daily Mail)特約撰稿,作品亦見於《倫敦標準晚報雜誌》(ES)、《你》(You)雜誌、《泰晤士報週日時尚雜誌》(Sunday Times Style)及諸多國際媒體。
章節試閱
老天爺啊,我到底幹了什麼好事!此刻,我正在一艘從普茲茅斯慢慢悠晃到康城(Caen)的渡輪上,套在Miu Miu翡翠綠夾腳拖鞋裡的一雙腳丫冷颼颼的,差點就要凍得冒出冰柱。
三個鐘頭前,我讓自己在西倫敦的人生關門大吉,拋下寬頻網路、浴缸、全功能廚房(全部鋪了地板喔),以及一棟左鄰右舍、樓上樓下都稱得上是有趣朋友的大樓。
現在,距離我在法國即將展開的「新人生」,只剩幾個鐘頭。
稍早前,我坐在船上的咖啡座,看著周遭全是所謂的「移民」,突然覺得:我是不是太早搬家了?還早搬了整整三十年。畢竟,大多數人都是搬到法國去享受退休生活的。但這幾個月以來,我那些朋友整天嘮叨個沒完沒了,說他們有多嫉妒我啦,說我有多走運啦。當初我說要搬到國外住,他們好像真的都激動到不行。「一定棒透了,妳絕對不會想回來的!」所以,當時我一點壓力都沒有。
可是,萬一沒「棒透了」怎麼辦?萬一我討厭那裡的生活,想馬上打道回府又怎麼辦?一年前,我在規劃我的婚禮。現在,我規劃自己一個人搬去偏僻鄉下住,得開半小時車子才到得了最近一家像樣的超市,得跳上火車坐好幾個鐘頭,才到得了最近的一家Prada,而最近的瑪莎百貨(M&S)食品超市呢,得顛簸五個小時(還得越過海峽)才到得了。
我的新家沒有室內廁所,沒有浴缸,沒有廚房水槽,沒有熱水。整棟房子,幾乎每個房間都貼滿褐色的花草壁紙,搖搖欲墜的牆面爬滿濕氣。原本該是廚房地板的地方,卻只有一個開口笑的大洞,低頭一望就看見陰森森的地窖。然後呢,後院還有一堆瓦礫垃圾,高度直逼庇里牛斯山。
我甚至連要過這種生活的衣服都沒有呢。在時尚圈混了十五個年頭,我衣櫥裡掛的衣服,大半都是精心設計來出席雞尾酒會──再不然,至少至少也是到克蕾瑞吉飯店(Claridges)吃早餐穿的,而鞋子,通常都高得像喜馬拉雅山,得靠雪巴人和氧氣桶幫忙才爬得上去。
我那輛老古董福斯Golf車,正停在渡輪樓下,甲板3B,裡頭裝滿了十八年倫敦歲月的遺跡。我的家具和裝滿二十四個褐色巨大紙箱的物品,已經在前幾天裝進大型貨輪運到普瓦圖-夏朗德去了。今天早上,在鄰居傑洛的協助下,我打包剩下的東西,不幸的是,它們足足可以再裝滿一輛貨車。
從早上九點一直到中午,我們都忙著把我剩下來的衣服和私人物品,塞進垃圾袋和塑膠置物箱裡,搬下四層樓的樓梯。
「親愛的,這可真是如假包換的最後一刻哪。」傑洛不以為然地噘起嘴唇說。「就算用妳的標準來看也是如此。大部分的人,起碼會在幾個星期前就拆掉書架,把所有東西都打包裝箱。」
「我也是啊。」我反駁:「這些是剩下的東西。」
倫敦生活的最後三小時似乎不到幾分鐘就溜走了。最後,我推著吸塵器在臥房繞了一圈,在冰箱裡留了一瓶香檳和一些巧克力給新房客,最後一次鎖上門。
來到樓下,我憂心忡忡地打量堆在人行道上那些花花綠綠、雜七雜八的東西。除了塞滿衣服的垃圾袋外,還有我的工作檔案、筆記型電腦、檯燈、地毯、盆栽、雞毛撢子、大大小小的外套衣架、一雙塞在廢紙簍裡的斑馬紋細跟高跟鞋,以及一頂我特別保留用來參加婚禮、綴著玫瑰花的黑色大帽子。
車子行李廂已經裝滿羽絨被、枕頭和十五袋乾果,前座則堆著垃圾袋、好幾盒瓷器、我儲存備用的法珀(Farrow&Ball)塗料,還有我收進儲藏室、然後又搶救回來的皮包和皮鞋。總不能每天都穿髒兮兮的綠色軍裝外套吧,我對自己說。
「妳得先上車。」本行是櫥窗設計師的傑洛說:「然後我才能把其他東西塞進妳旁邊的空隙。」等他把鞋子、衣服和雜誌一股腦胡亂塞進來,我已經看不見後車窗,而拜勉強擠進駕駛座後面那株巨大的棕櫚盆栽所賜,我的鼻子也差不多要貼在擋風玻璃上了。
「祝妳好運!」我開車離去時,傑洛說:「到了以後要記得伊媚兒給我。」
「一路順風!」我的鄰居黛西扯開喉嚨:「我們明年夏天法國見囉!」
車子底盤比正常狀態還低上好幾寸,一路蹦蹦跳跳地開到街尾。這時,我突然想到自己忘了什麼,心裡一陣慌,疾速迴轉,車子撞上路面減速用的隆起丘,聲音大到壓過了瓷器的匡啷噹啷。
幸好,運氣不錯,黛西和傑洛還站在大門口。
「普茲茅斯要怎麼去啊?」我聲嘶力竭地喊道。
「走A3!」黛西也吼回來:「開到漢默史密斯再跟著路標走。」
「我賭一個月,」傑洛搖搖頭說:「一個月,妳就會回來。」
* * *
所以說呢,我的臨去秋波可真不是普通的兵慌馬亂。但是,在八月最後一個週一,在這陽光普照、人車稀少的國定假日,當車子開過我熟悉的西倫敦街道,我卻覺得彷彿從一待十多年的遊樂場裡得到解放。
老實說,過去這一年來,我覺得這座遊樂場開始變得像監獄。我的公寓已經變成充滿傷心回憶的地方,而過去那段感情更是陰魂不散,鎮日在附近街坊流連。只要經過諾丁丘的某幾家餐館,坐在肯辛頓高街後面的法國咖啡館,或漫步穿過荷蘭公園,我就會想起失去的一切,心傷欲碎。
但是,在這個八月早晨,我飛車駛過奧林匹亞,疾馳奔上漢默史密斯的環形交流道──這兩個路段平常都塞到爆,但今天,倫敦似乎一點掙扎都沒有地放我自由。
除了公寓外,我還放棄了許多人夢寐以求的職業:一本光鮮雜誌的美容與時尚編輯。雖然二十幾歲、三十出頭時,我的確熱愛時尚圈工作,但我現在已經踏入另一個階段,再也無法應付服裝設計師和他們荒謬可笑的自我。
我花了足足十五年才得出結論:我受不了時尚圈的那些人,厭倦了和他們串通共謀,編造重大的時尚迷思:每隔六個月花六百多英鎊買一只新的設計師皮包是必要的;再不然就是,熟女穿上蛋糕裙、超短迷你裙,或是設計師在這一季狂推的什麼不成體統的潮品,也都會很好看。
鼓吹讀者快快上街去買「必敗」單品,而我卻明知那是「不必敗」、而且不到六個月就會在流行風潮下被掃進垃圾堆的東西,讓我很有罪惡感。
事實上,當年我是在時任特稿編輯的朋友勸說下才接下雜誌工作的。在見識過報界的慘烈競爭後,我想這會是份安逸輕鬆的工作,而的確也是。在報社只花我五分鐘就可以拍板的決定,在這裡卻要動員至少六個人,耗上好幾天仔細討論、反覆推敲。我們花好幾個小時圍坐在編輯辦公室裡喝咖啡,吃餅乾。唯一的問題(也是最大的問題),是我最後必須和一大串討人厭的攝影師合作。
這些攝影師都是某個編輯挑選的,大半不是他的親戚朋友就是他愛情生活的包袱。我不是和自我大得像非洲的攝影師一起去邁阿密,就是和差不多瀕臨精神崩潰邊緣的攝影師去紐約。而和我一道去澳洲的,是個從來沒拍過專業時尚照片的攝影師,我在沒半點蔭影可躲的海灘一站幾個小時,曬得快變人乾,等他老兄慢條斯理地調整光圈,至於他調整焦距所花的時間嘛,夠我畫完一張風景水彩畫還綽綽有餘。
而且無一例外,他們所做的事總是恰恰和原本的工作規劃背道而馳。花卉與唯美?攝影師一定會叫彩妝師幫模特兒上個煙燻妝,把頭髮弄得「犀利」一點,完全不管僱他們來工作的這家雜誌一點都「不犀利」,而且還很商業取向,專走安全路線。要是每碰到一個自以為把模特兒弄得醜不啦嘰就算挑戰極限的攝影師,就能拿到一歐元,今天我應該可以搬到聖托佩茲(St. Tropez)住豪華別墅,而不是在普瓦圖-夏朗德住小房子啦。
最後一根稻草,或者像法國人說的:「讓花瓶溢出水來的那一滴水」,應該是賴瑞•馬里布。這位時尚攝影師差不多被全倫敦的雜誌編輯列入拒絕往來戶,因為他的行為捉摸不定,也完全無法遵循工作規劃的要求。可是,我們社裡有個編輯曾經和他有段熱情如火的風流韻事,所以我竟然得和他一起飛到加州去拍夏季封面。
這個差事理論上應該很棒──去加州渡假一週還有錢可拿,但我得告訴你:一點都不棒。在飛航途中,馬里布就喝醉酒,發酒瘋,對同志髮型師出言不遜,還把彩妝師罵到哭。第一天,他叫所有工作人員「他媽的滾蛋」,因為他必須和模特兒獨自「黏在一起」,以便「創造一點化學反應」。接著,就和她一起躲進沙丘裡,好幾個鐘頭不見人影。最後拍出來的畫面是模特兒仰臥沙灘上,或上空躍出水面,或是跨坐在沙丘上、一臉狂喜地捧著胸脯──分明是替男性雜誌《Loaded》量身打造的畫面,哪能登在時尚美容雜誌啊,所以沒半張能用。
第二天,他斷然拒絕配合「讓夏日閃閃發光」主題的拍照,說那樣的照片「無聊到爆」。第三天和第四天,他什麼都不肯拍。第五天,他威脅要殺了彩妝師,於是彩妝師要求打道回府。我懶得吵,二話不說就回到倫敦,遞出辭呈。
* * *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們即將抵達康城……」
過去六小時,我和堆積如山的雜誌一起躲在艙房裡,是該出去了。才剛關上靠走道的門,我就聽見隔壁艙房傳出一對三十來歲男女的聲音。
「休-想-和-我-說-話!」男人說,接著就是響亮的巴掌聲,好像想把女伴打得從面前消失似的。他們甚至還沒上車耶!真是個頗激勵人心的好兆頭。我對自己說,自己一個人旅行,總好過和壞脾氣的同伴一起出門吧。
我走到外甲板上,看著康城在慢慢隱褪的夏日晝光中逐漸接近。在半昏半明的暮色中,港口燈火閃爍,輝煌如海瑞.溫斯頓(Harry Winston)的鑽石,但是我腦海中只想著,待會上岸後還得趁夜開五個小時的車到普瓦捷(Poitiers)。
這兩個星期來的拆卸打包讓我筋疲力竭,於是心念一轉,立刻做了決定:我要在渡輪港口附近找家小旅館過夜,明天一大早再出發。如此一來,我新生活的第一天就可以在朝陽而非暗夜裡展開。此外還有個更迫切的理由:在等待上岸時,我發現油箱幾乎是空的。港口附近的自助加油站不收信用卡,我上次來時身受其害,所以這天晚上我除了通關外,大概哪裡都去不了,就算想走也莫可奈何。
一個小時後,我站在「鯨魚客棧」昏暗的接待處。這家店和市中心的大部分酒吧與小餐館一樣,附設幾間還算像樣的旅館房間。一個鐘頭前,餐廳已經不供應港口這一帶每家店都有的白酒貽貝配薯條,酒吧裡半個人影都沒有,看來我是唯一入住的客人。和我搭同一艘渡輪來的旅客,只要沒刻苦耐勞地連夜開車南下,起碼都會到康城市區,住在那裡的諾富特飯店。
接待員急著下班,沒問我要信用卡、護照,或登記入住時通常需要的其他東西。「二樓。」她連頭都沒抬一下地說,然後給我一把鑰匙,指著狹窄的木頭樓梯。
一踏上樓梯平台,我就嚇了一跳,因為有個男人癱倒在樓梯上。我起初以為他喝醉了,但是他牢牢盯著我看,點點頭,好像三更半夜躺在旅館樓梯上很正常。他穿著黑色牛仔褲與短夾克,還帶了個小背包。
我猜想他八成是錯過渡輪,所以偷偷溜上鯨魚客棧的樓梯,想找個比較暖和的地方過夜。「祝他好運。」我想。但他也真奇怪,不在渡輪站過夜,卻跑到旅館樓梯來紮營。不過,這話擺在心裡就好,千萬別說出口。
我打開門,進入一個小房間,四面牆是尼古丁的菸黃色,浴室是黏膩的粉紅。這裡當然不是頂級的克蕾瑞吉飯店啦,浴室裡沒熱水,而八月下旬的此時,房裡竟然非常冷。
在電熱器上胡亂撥弄了好一會兒卻沒反應後,我打電話到樓下櫃台。沒人接。我冷得要命,只好衣服也不脫,爬上床去,躲進藍底黃花的床罩底下。在單薄的床罩和單層被單裡發抖了好幾分鐘後,我起床,在白色美耐板衣櫥裡找毯子,可是裡頭什麼都沒有。我好想念擺在車上的那床羽絨被,可是要拿到被子,就得摸黑在堆積如山的物品裡翻翻找找。
旅館裡一定還有人吧,我想。於是,我躡手躡腳走出房間,走過窄窄的樓梯平台,發現樓梯上那個男的已經睡著了,背包擱在腦袋下當枕頭。
樓下,接待櫃台黑漆漆,門也全上鎖,沒有夜班職員,沒有半個人。我突然想到,整棟房子裡很可能只有我和樓梯上那個一身黑的男子。我急忙轉身跑上半明半暗的樓梯,躡手躡腳穿過平台,深怕吵醒他。可是,走過他身邊時,他翻了個身。
我心臟跳得比子彈列車的引擎還快,匆匆打開門鎖,一邊很擔心他會突然出現在我背後,強擠進房間裡。我衝進房裡,盡快鎖上門,突然想到櫃台後面的板子上掛有房間備用鑰匙!
這哪裡是我「法國新人生」的好兆頭啊。孤伶伶在康城一家荒僻的旅館裡,房門外還有個陌生人,這可從來沒在我的劇本裡出現過。我想起自己所放棄的一切:那間舒適的公寓,我可以不必擔心被謀殺,安心上床睡覺,讓我可以享受所有物質奢華,從四百支紗精梳棉床單到配有最新式強勁淋浴設備的石灰岩浴室。我根本不需要這麼做,我可以繼續過舒舒服服的好日子,再過上好幾十年。
我坐在床上思索可以打電話給誰,終於我明白,答案是「沒有」──不管打給誰都非常丟臉。才和那些熱情洋溢的朋友揮手道別,第一天晚上就從旅館房間驚慌失措打電話求救,豈不是代表天大的失敗,連第一道跨欄都跳不過就摔倒了。
我甚至不能打給我媽,因為我沒告訴她說我打算搬到國外住,她八成會像個典型北方人那樣,一點同情心都沒有地說:「妳這是自作自受啊。話說回來,妳到底搬去法國幹嘛?」環顧冰冷孤寂的房間,我彷彿看見了未來人生的縮影。
此刻,困在旅館房間裡,聽見走廊上突然響起走動的聲響,我覺得,就連和賴瑞•馬里布在加州度過的那星期都比現在好得多。我驚恐莫名,知道是樓梯上的那名男子在房門外走來走去。我該怎麼辦?沒有人知道我在這裡,我連法國的報警電話是幾號都不知道。衝到窗邊,我看見兩層樓底下有個小小的中庭花園,可是窗戶很高,而且上鎖了。我聽見那個陌生人就在我房門外面──那道門看來輕輕一推就能長驅直入。
我打起精神,準備隨時迎戰他破門而入時的猛然撞擊或衝撞。驚慌之下,我把體積如小型櫃子、塞滿雜誌的包包擋在門後。要是他真闖進來,這至少可以絆住他,讓我多個幾秒鐘逃命。誰想得到啊,上一季「必敗」的包包竟然搖身一變,成為自我防衛的武器。
我坐在電話旁,突然瞥見上面有個緊急救助部門的號碼:17。謝天謝地!我趕緊撥號,接著,有個不甚友善的男聲傳來:「喂?」
「我在康城的旅館,鯨魚客棧。我很害怕,因為有個我不認識的男人在我房間外面。」
「在妳房間外面?」
「沒錯,他在走廊上走來走去。」
「妳房門鎖上了嗎?」
「鎖了,但是他可以闖進來。」
「他有想要闖進來嗎?」
「沒有,可是他一直在外面走來走去。太奇怪了。」
「女士,要是妳房門鎖上了,那就沒問題。」
「可是,拜託,你們能不能到旅館來,看看那個男人到底在幹嘛?」
緊急救助部門的那個聲音祝我晚安,然後掛掉電話──恰恰就在我聽見走廊上砰一聲的當下。有人用力敲門──不是我的門,但還是很嚇人。接著,我聽見腳步聲又朝我房間走來,然後又走開。這人到底在幹什麼?他顯然是精神失常嘛。
我又撥了17,「又是我,在鯨魚客棧,我剛剛打過電話來。」
「是的,女士。」疲累的聲音說。
「現在那個人就站在我房間外面,他在走廊上弄出奇怪的噪音。」
電話那一頭再一次問我門鎖了沒,我給了肯定的答案後,就再一次告訴我說那就沒問題了。我懇求他派個警察來查看一下,他不為所動,只祝我晚安,然後又掛掉電話。走廊上,樓梯男還是很嚇人地在我房間外面走來走去。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我打了四次電話給警察,卻始終無法讓他們相信我身陷險境。而門外的踱步聲持續不輟,後來我甚至聽見他在自言自語,嗓音低沉粗暴。我直挺挺地坐在床上,嚇得要死,沒想到法國新人生的第一夜竟然變成了希區考克電影的場景!
老天爺啊,我到底幹了什麼好事!此刻,我正在一艘從普茲茅斯慢慢悠晃到康城(Caen)的渡輪上,套在Miu Miu翡翠綠夾腳拖鞋裡的一雙腳丫冷颼颼的,差點就要凍得冒出冰柱。
三個鐘頭前,我讓自己在西倫敦的人生關門大吉,拋下寬頻網路、浴缸、全功能廚房(全部鋪了地板喔),以及一棟左鄰右舍、樓上樓下都稱得上是有趣朋友的大樓。
現在,距離我在法國即將展開的「新人生」,只剩幾個鐘頭。
稍早前,我坐在船上的咖啡座,看著周遭全是所謂的「移民」,突然覺得:我是不是太早搬家了?還早搬了整整三十年。畢竟,大多數人都是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