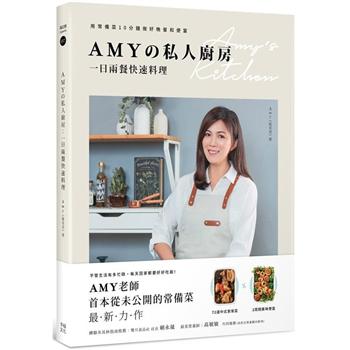推薦文一
空城裡的私眼睛
伍軒宏
保羅.奧斯特小說裡,八百萬人口的紐約大都會,感覺起來像座空城。
也許,這就是奧斯特對紐約市的看法,一座「人口眾多的空城」。因為他對紐約有自己的詮釋,以及描述手法,這三則描寫紐約客流落在自己城市的故事,才有資格叫《紐約三部曲》。不然,只因故事發生在紐約、背景在紐約、人物在紐約活動,這些消極因素並不足以讓小說被冠以紐約之名。奧斯特的三段故事,被稱為「三部曲」,表示三者間主題連貫;被稱為「紐約」三部曲,表示它們點出了紐約市的某種性格特質。
在我們的印象中,紐約人口眾多、異質多元、熱鬧繁榮,是主宰全球化資本的金融中心。為什麼把如此充滿力量的地方寫成空城?科幻電影裡,由於病毒或外星人入侵,都市城鎮遭劫成為空城,只剩僵屍。奧斯特小說呈現的紐約市,並未遭遇劫難,其實運作如常,但感覺像空城,那是因為在他的世界,空城是一種心理狀態,一種投射,或情境。
三部曲中,奧斯特的小說人物對大都會的芸芸眾生,興趣缺缺,卻尋尋覓覓,執著於少數特定的他者,到了失去自我的地步。
行走空城
紐約是行人之城。我在紐約住了五年,當初最欣賞、如今最懷念的,就是那裡寬闊平坦、閃閃發亮的人行道。紐約客憑藉雙腿,沿著人行道,可以暢行無阻(只要避開危險區域),愉快走到任何地方。所以紐約是全美胖子最少的地區。每次有訪客來,我都會拉他們到街上好好走上幾回,一條街一條街,走啊走啊十幾二十條三十條,沿街處處有趣。但來自上州或中西部的朋友,習慣開車代步,早失去行走的力氣與興趣,很可能覺得我在整他們、操練他們,甚至累壞了他們。他們不知道,行走紐約才能認識紐約。
奧斯特三部曲中,有大量穿梭紐約街道的情節,不乏我熟悉的區域,相當令人懷念。〈玻璃之城〉裡,身分隱密的推理小說家昆恩,在家中接到電話堅持要跟名叫「保羅.奧斯特」的偵探通話。昆恩受聽筒裡的聲音召喚而回應,冒用奧斯特的偵探身分,受雇跟監一名甫出獄的神祕男子,跟隨他走遍曼哈頓大街小巷,被莫名力量牽引,積極投入跟監任務後漸漸失去自己,「變成別人」,不再是作家,也不是偵探,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其中有一段,昆恩從西區一○七街走到七十二街,持續往下到最南端的世貿大樓,再轉向東,經下東區與中國城,往北走到第一大道聯合國的所在,幾乎涵蓋半個曼哈頓島。
另一段,冒偵探奧斯特之名的昆恩跑到河濱道與一一六街一帶,拜訪另一位奧斯特,作家奧斯特,尋求協助,形成假奧斯特vs.真奧斯特的場面!那一帶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勢力範圍,距離我住過的河濱道學生宿舍大樓只有幾步之遙。三部曲第二部〈鬼靈〉裡的行走,主要在布魯克林區,以跟曼哈頓一水之隔的布魯克林高地「橘街」(惠特曼製作第一版《草葉集》之處)為核心:職業偵探「阿藍」受「阿白」之雇,監視「阿黑」,但他慢慢發現「阿黑」並非不知道自己被盯上。如此一來,「阿藍」真的是跟監者嗎?「阿黑」與「阿白」有什麼關係?
在城市中行走,可以是漫步、漫遊、散步,或行乞、流浪,或只是走路而已。但奧斯特的主角穿梭街道,急急忙忙,躲躲藏藏,受制於人,不像塞杜(Michel de Certeau)的都市行人,有「空間實踐」的作為,而是愈走愈失去自我,失去身分,從熟悉走到不熟悉,如困在迷宮裡的老鼠。大都會的豐富於是轉成空,行走其間的人只是空城的遊魂。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曾說,城市漫遊者(flaneur)跟偵探故事的起源有關:法國大革命後的巴黎,人人都是密探,相互窺伺,城市漫步對窺探私密有很大幫助。漫遊者看來懶散,卻也具觀察者的警覺性。犯罪學上的聰穎加上漫遊者的輕鬆,構成十九世紀偵探的基本成分,而探案的重點之一,就是獨立個人(individual)的痕跡如何消失在大城市的人群中。
遺失身分的偵探
三部曲中的主角,在故事開始的時候,無論受僱或受託,都被賦予尋人、監視或搜索的任務,都具有某種偵探的地位。我們知道,偵探是知識主體的原型,尋找、偵察、跟監、監視、窺伺、觀察、分析、判斷、詮釋,這些是知識主體對客體進行控制的基本動作,因此所有「求知」的作為都有偵探的成分在內。
結果,在連續空間中大量行走移位之後,奧斯特筆下的偵探角色失去知識主體的優勢。獵捕者與獵物、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之間的結構易位,偵探在探索的認知過程中,並未得到知識的確認,反而失去掌握主動的能力。當然,我們也不應忘記,〈玻璃之城〉的推理作家昆恩兼差當起偵探,〈鬼靈〉的「阿藍」是職業偵探,他們是「私家」偵探,不同於警察或FBI那樣,代表國家權力的介入。所以,在故事情節推展下,當僱主的身分與權力來源都呈現卡夫卡式的不明時,當偵察對象不再只是客體時,偵探的地位和意義都被改寫。
寫推理小說的昆恩曾說, 對他而言,private eye 一詞有三層意義,eye 可指小寫的 i,private investigator (私家偵探)之意;也是大寫的 I,private I (私密的我)之意。可是 eye 也就是 eye,肉眼、單眼、眼球的肉體,所以 private eye 是「私眼睛」。從傳統上代表知識權力的偵探,到脆弱的私眼睛,奧斯特在敘事中探索「消失主體」的變化,因此我們在他的小說裡看到一連串「主體消失」的相關表現手法:鏡子、擬象、分身、替身、雙生造成視覺的混亂,凝視的威力不再,「玻璃之城」也是「鏡像之城」,真相∕真實退位。這些手法在傳統小說中已經存在,但在後現代小說變成加強版,到了顛覆主客本體地位的地步。
偵探查案,常常需要偽裝,「誰是誰?」(含「我是誰?」)的身分問題自然凸顯。我們看到冒名奧斯特的昆恩(Quinn,與Twin同韻),在〈玻璃之城〉某段情節用「昆恩」做為假名欺敵;另一次,昆恩以校友身分,到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查閱論文,得知詩人彌爾頓的秘書曾寫《新巴別塔》鼓吹恢復伊甸園的原初語言,後來才曉得此人出於杜撰,論文章節是虛構;〈鬼靈〉中的「阿藍」在盯梢過程中發現,只要覺得愈接近「阿黑」,自己好像愈獨立,進入「阿黑」的世界等於是進入自己的世界;原來在〈玻璃之城〉的人物與姓名,也在三部曲最後一部〈禁鎖的房間〉出現;〈禁鎖的房間〉裡的敘述者「我」,是〈玻璃之城〉裡的小說人物,還是〈玻璃之城〉與〈鬼靈〉的作者?奧斯特玩弄後設小說技法,充分發揮語言的多義性、名字的符號性,以及「身分只是分身」的效果,導致小說內與小說外的界線難分。
「我是彼德.史提曼。那不是我的真名。」或「我是保羅.奧斯特。那不是我的真名。」可以說是三部曲中最具代表性的陳述。
紅色筆記本
講到後設小說,就不能不提書寫行為,也不能不提紅色筆記本。
偵探查案要記錄線索或跟監流程,要書寫報告,更要查閱紀錄、驗證文件、解讀私密書寫,加上三部曲中偵探與作家的身分再三重疊,奧斯特於是把偵探變成在手稿、筆記、書籍、信函、日記、論文裡面找蛛絲馬跡的解碼人,同時也是勤於記錄的書寫者。〈鬼靈〉中的「阿藍」,愛看黑色電影(尤其是經典的「漩渦之外」),但他的監視對象「阿黑」持續研讀《湖濱散記》,並用紅色墨水在筆記本上書寫,「阿藍」只能寄給僱主非常「表面」的例行報告。他想知道,筆記本裡寫了什麼?
〈玻璃之城〉裡的昆恩,為新任務選購筆記本時,對放在一大疊最下層的那本紅色筆記本,感到「一股無法抗拒的衝動」。(像「紅菱艷」中的紅色舞鞋那樣!)他一面跟監一面寫,記錄他的思想、觀察、問題,愈來愈認同紅色筆記本,覺得它可以「提供救贖」。
問題是,書寫不見得鞏固作者的自我,書寫主體往往愈寫愈不是自己。
神祕的紅色筆記本也出現在三部曲中最好、最完整、最耐人尋味的〈禁鎖的房間〉。自幼特立獨行、才氣過人的范修,少年時無所不會,無所不能,但征服一切後,決定轉向開拓內心世界,疏遠大家。後來,哈佛讀到一半棄學,上船當水手,再到巴黎沉潛,回國後娶妻成家卻不就業工作,鎮日書寫,手稿成堆,直到有一天范修消失了,無影無蹤。半年後,范修的妻子跟敘述者聯絡,目的不在尋人,而在依范修失蹤前所囑,整理、出版其手稿。故事於是開展(我沒有洩露多少驚人情節)。敘述者是范修少年時期的鄰居兼最好的朋友,是在紐約文化界掙扎存活的雜文作家,被范修的手稿拉進一場無比迷離、身分錯亂的欲望風暴中。失蹤的作家,遺留的作品,創造了成功之外更多的懸疑。
〈禁鎖的房間〉的敘述者不是偵探,但做為范修手稿執行人,在不斷探索范修的真相與下落的過程中,他變成被客體牽引、控制的偵察者:「找了他幾個月後,覺得似乎是我被找到。與其說我在尋找范修,不如說我在逃避他。」他發現自己跟范修愈來愈接近,愈來愈像,愈來愈認同,幾乎形成「男同欲望」透過女性(范修之妻)中介的三角結構。
三部曲的最後一部也許玩太多後設遊戲,但絕對值得細品。尤其是,〈禁鎖的房間〉把三部曲的共同主題「消失」,做了最佳展示。如何消失?如何在空城裡找自己,如何在空城裡失去自己?我們甚至可以說,三部曲教我們從紐約消失的(至少)三種方法。
在不能洩漏偵探小說重要情節的前提下,我無法透露〈禁鎖的房間〉接下來如何了,也不能解釋什麼是禁鎖的房間?《紐約三部曲》以早期奧斯特小說的極簡主義、零度書寫、無肉風格寫成,在國外有毀有譽,在台灣二度翻譯,二度出版,廣受歡迎,讀者會願意像偵探那樣找答案。
我只能說,答案就在紅色筆記本裡。
推薦文二
歸零與無限──在台灣重讀小說《紐約三部曲》
紀大偉
把半瓶水倒乾,讓液體歸零,瓶中空間就無限了。把人的液體 / 體液瀝乾,讓這個人歸零,此人就身置無限了。紐約就是讓我留美十一年歸零的地點。深夜開車不斷在紐約外圍的拉瓜地亞機場和花旗銀行的巨蛋之間繞行,iphone沒電了,GPS導航系統秀逗了,車子油箱已空。張愛玲寫,「妻子在樓底下開無線電聽新聞報告,丈夫認為這是有益的,也是現代教育的一種。他不知道她聽無線電,不過是要聽見人的聲音。」開車徒勞的我,打開新聞電台來聽。你不接我的電話。
然後我打包回台灣,成為台灣文學研究界的新人,從零開始,眼前是無限的文史工作,但我可能還有點幸福。
保羅奧斯特的《紐約三部曲》(含〈玻璃之城〉、〈鬼靈〉、〈禁鎖的房間〉三卷)從一九八○年代出版以來,在全球書市享譽數十年。十五年前我初訪紐約的時候,就有歐洲朋友跟我大推此書。當年我離開紐約飛回台灣的前一夜,我在時代廣場的電影院看了奧斯特本人編劇的電影「煙」(Smoke,一九九五年)──此片跟《紐約三部曲》高度相關。十一年前我飛往UCLA攻讀比較文學博士之前,我看過《紐約三部曲》全書,但只擱在心底一角,沒有多想──畢竟我去了洛衫磯,這個城市向來是紐約的死對頭,紐約跟我無關。但後來意外搬到美東,常跑紐約,在我心中冷藏十年的《紐約三部曲》才重新發熱發光。在紐約街頭失神迷路的時候,我常想到〈玻璃之城〉;搞不清楚是人在跟蹤我還是我在跟蹤人的時候,〈鬼靈〉就上身;打了電話對方不接,電話留了言對方不回,〈禁鎖的房間〉有聲書就在我腦中自動播放。如今編輯促我重讀《紐約三部曲》,我幾乎想婉拒──書中情節我太熟悉,讓我痛楚。在紐約,conversation(對話)難為;在《紐約三部曲》,conversation永遠短路;在你我的conversation中,兩人故意假裝不熟,避開彼此的目光。要比賽誰比較難搞嗎,當然我認輸。
不過我既然歸零,進入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重新做人,那麼我就假裝客觀專業一點,試論如何從台灣文學界(而不是英文學界)的位置來談《紐約三部曲》。我本來擁有的英文版和漫畫版早就被我丟在洛杉磯,幸好從政大圖書館借出一本嶄新的版本,打開一看,發現蓋了「國科會城市與文學主題購書計畫」紅印。或許此書比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曾經橫掃台灣文壇學界的城市主題書──更貼近台灣。《看不見的城市》太像安藤忠雄,而《紐約三部曲》卻像「大開眼戒」(Eyes Wide Shut) 一樣假掰濫情。
在台灣文學研究界進行研究,恐怕就是要從台灣起飛,且採取各種別出心裁跌破眼鏡的國內外航線,這樣台灣才飛得出國,外國也才能夠飛進台灣。這種歸零與無限,就是台灣文學研究的命脈、生機。所以我建議:在後現代的台灣談後現代小說代表作《紐約三部曲》,不妨繞路而不直飛紐約──在日本轉機吧。從台灣飛紐約,一定要途經日本。我甚至主張,要不是途經日本,台灣人到不了紐約。所以我不要直接飛向《紐約三部曲》,而要在朱天心的後現代小說《古都》轉機。在《古都》中,主人翁飛到京都卻苦苦找不到理當現身的旅伴,旅伴爽約了──我常說,最爽的約會就是「爽約」,因為爽了才更刻骨銘心。堅持爽約(含熟人猛敲門卻硬是不開門,熟人來電卻硬是不接,熟人來電留言卻硬是不回)就是〈禁鎖的房間〉這一卷的主梗,爽約也是紐約客的神髓,不過紐約客通常淡淡裝傻,比如謊稱:啊,手機沒電,怪我嘍。〈紅玫瑰與白玫瑰〉最淺白的一句話,「風吹著的兩片落葉踏啦踏啦彷彿沒人穿的破鞋,自己走上一程子。……這世界上有那麼許多人,可是他們不能陪著你回家。」正是在寫紐約。或者該說,「他想陪你回家,但是他鼻要」,這樣就更紐約。《古都》的主人翁被爽之後失神迷途,莫名其妙回到台灣,驚覺自己回家(台灣)卻不認得家(台灣)。這就是佛洛伊德說的「認不出自己家的詭異感」(uncanny,即un-homely)──這就是〈玻璃之城〉這一卷的主梗,也是我自己從紐約回台北的內心戲。《古都》主人翁這個漫遊者(台灣文學的研究者──含朱天心的粉絲們──和猶太作家保羅.奧斯特的讀者,豈敢忘記猶太哲學家班雅明的雋語?)是在跟蹤誰,還是被誰跟蹤?這種跟蹤 / 被跟蹤監看的動力,是否是以神經質發作(paranoia)之名行愛情之實?(是說,有哪種愛情少得了paranoia呢?)〈鬼靈〉這一卷,一言以蔽之,如果你被人肉搜索了,就是因為有人在愛你,再不然就是紐約或台灣在愛你嘍。
把朱天心的《古都》跟《紐約三部曲》合併閱讀可以拉出新的航線,航線愈多愈好。所以我再加一筆書目:馬嘉蘭(Fran Martin,在澳洲墨爾本大學執教,研究台灣同志文學十餘年)在二○一○年出版一部討論中港台女女之愛的重量級專書《頻頻回顧:當代華文文化與女女情欲的想像》(Backward Glances: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s and the Female Homoerotic Imaginary )。在台灣文學界從事性別研究的學人不能錯過此書,朱天心作品(從《擊壤歌》到《古都》等等)的研究者更該引用馬嘉蘭,不過《頻頻回顧》此書不只可以啟發朱的粉絲,也可以觸動《紐約三部曲》的台灣讀者。馬嘉蘭在《頻頻回顧》的主梗就是她提出的「記憶模式」:在朱天心等人的小說和小說人物,一旦進入記憶模式,身陷美好舊時光,就可以在方舟上的日子裡歸零而且身置無限。我們常戲稱在聚餐場合(尤其是婚宴或是同學會這等叫人欲哭無淚的時空)突然沈默放空的朋友「進入了省電模式」,但他們大有人進入了「記憶模式」:我們以為他們在省電,其實在歸零。
後現代小說難以輕鬆搞定,後現代台灣亦然,所以在後現代台灣(且慢,後現代是在「現代性」的「後面」,在「上面」,還是「下面」?)重看後現代小說就要加添許多方便空氣流通的排氣孔,不然死守《紐約三部曲》這部書而不參照其他的文本 / 排氣孔,怎麼可能看得懂?所以我要用張愛玲、朱天心、馬嘉蘭作注,標示進出《紐約三部曲》的多元入口。入口不嫌多,從「背面」進入更好,我還要再加舒國治《理想的下午︰關於旅行也關於晃蕩》,以及政大同事柯裕棻《恍惚的慢版》。借用柯姐的說法,「進入了省電模式」的朋友可能身陷「記憶模式」,但他們也可能進入「恍惚模式」。在柯姐的書中,我寫的導讀〈前途無效〉,借用東京地鐵票上的漢字自嘲,但「前途無效」不只描述了我在東京的迷途,也可以貼切形容你我在紐約,在台灣的情境。
建築大師庫哈斯的奇書《小號中號大號特大號》(S M L XL,比較文學研究者必讀)就是以紐約為例,提醒我們城市都是大同小異的(generic),都帶來video cleaner之後的昏炫感。在紐約難免滑入省電、恍惚、記憶模式,畢竟此城販賣鄉愁(nostalgia),而不販賣未來。在紐約看不到未來。在紐約的大叔們總是忍不住跑去康尼島(Connie Island)看海──如果你聽到「康尼島」而心頭震動,你必然是大叔大嬸了,而且你還裝可愛,身上一串「gloomy bear」和懶懶熊,世界上可有像你這樣老的底敵嗎?
本所同事范銘如的《文學地理》強調要把文學置回地理空間來重新審視,我頗有同感,好想在這篇文章畫出大紐約的地圖,不然我好怕讀者無從想像《紐約三部曲》書中角色──以及我自己──在紐約內外的散步路徑。我怕你找不到康尼島在哪裡,我簡直像《古都》的主人翁一樣在水邊放聲大哭。我在哪裡?我從古根漢美術館走到附近的傳奇甜點鋪「Lady M」,點一份法式千層派,然後繞行中央公園一周,走向「Good Enough to Eat」家常餐廳排隊吃草莓鬆餅。我頻頻打電話給你,你也不接,你以為你在演《紐約三部曲》嗎?我要在中央車站上車回康乃迪克州了。無數的煩憂與責任與蚊子一同嗡嗡飛繞,叮你,吮吸你。你以為第二天起床,就可以改過自新,又變成了好人,是罷。
專訪
保羅.奧斯特近身錄
王寅
紐約的四月,丁香花已經開放,但是依然春寒料峭。保羅.奧斯特的家位於布魯克林區公園坡附近,那是一套典型的褐石公寓。
點燃細枝雪茄的奧斯特身穿黑色襯衣,梳油頭,金魚眼,臉膛微紅,聲音渾厚,頭髮已經有些花白,側面望去,臉部輪廓就像古羅馬的塑像。同為小說家的奧斯特夫人希莉.哈斯特維特(Siri Hustevedt)買回來一大棒梅花和紫色的鬱金香,在敞開式的廚房裡修剪花枝,將花一一插入花瓶,花香瀰漫在有著一百多年歷史的建築空間裡。
一九四七年,保羅.奧斯特出生於美國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一九六九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大學畢業之後,奧斯特漫遊歐洲,過著漂泊無定的生活,「做了各種各樣瘋瘋癲癲的事」,做過翻譯、參加舞團的排練等……。
迄今為止,保羅.奧斯特總共發表了十三部小說、五部傳記、兩本詩集,以及大量的書評和影評文章。奧斯特目前已經躋身一流作家的行列,他在西方,尤其是歐洲擁有眾多崇拜者。《華盛頓郵報》給予他高度評價:「保羅.奧斯特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具特色而罕見的作家!」日本作家村上春樹也極其欣賞他:「能見識保羅.奧斯特是我此生的榮幸。」
奧斯特的小說大多有著偵探、犯罪小說的外殼,有「實驗偵探小說」、「後現代偵探小說」之稱,「憑藉著對推理小說的全面翻轉,保羅.奧斯特開創了一種全新的小說敘述方式。」(《村聲雜誌》)奧斯特的小說中,經常有一個與現實存在疏離感的孤獨偵探,這個普通人常常迷失在城市的人群中,他一直在創造屬於他自己的故事。
《紐約三部曲》之一的〈玻璃之城〉講的是偵探小說家昆恩的故事。一天,昆恩接到一個打錯的電話,電話那頭找一位原名叫保羅.奧斯特的私人偵探,昆恩冒奧斯特之名去見了這位行為古怪的求助者,這個叫彼得.史提曼的人是他同名父親的犧牲品,老史提曼是一位瘋狂的神學家,他把兒子長期幽禁。幸虧一場大火,小史提曼才被人救出,老史提曼被法庭認定為精神失常而收容。小史提曼擔心的是瘋子父親即將釋放,他想請偵探盯住老頭子以防再遭威脅。於是昆恩冒充保羅.奧斯特盯梢老史提曼。有一天他醒來以後,發現老史提曼不知去向,而小史提曼也忽然聯絡不上了,於是昆恩只好轉而監視小史提曼的住所,但他從此以後再也沒有見到小史提曼的蹤影。昆恩失去了隱居的家,甚至失去了原來的容貌,成了一個一無所有的流浪漢。
「事情是從一個打錯了電話開始的,在那個死寂的夜裡,電話鈴響了三次,電話那頭要找的人不是他。」這就是〈玻璃之城〉開頭的一段文字。在回憶這部小說的創作經歷時,保羅.奧斯特告訴記者,他寫的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在寫第一本書《孤獨及其所創造的》的時候,一天,外面來了一個電話,問奧斯特這兒是不是一個很有名的偵探社?奧斯特回答說不是,然後掛了電話。過了一段時間,又打來一個電話問是不是那個偵探社?奧斯特本能地再次說不是。把電話放下的剎那,他想應該說我就是。於是他就把這次經歷寫成了小說。後來,在寫完《紐約三部曲》之後,他又接到第三次打錯的電話,這次的巧合更為離奇,電話中問奧斯特是不是昆恩先生?
保羅.奧斯特喜歡故事套故事,一邊是作家創作的故事,一邊是作家自己的故事。他也因此被稱之為製造迷宮的作家。其實,這只是作家包裝作品的手段,奧斯特更著迷的是虛幻的真實、現實的偶然和人生中的悲劇因素。
批評界認為奧斯特深受貝克特和博爾赫斯的師承,但奧斯特心儀的作家卻都是現實主義作家,排在第一位的是賽萬提斯,此外還有狄更斯、托爾斯泰、杜思妥耶夫斯基、霍桑、梅爾維爾和梭羅。保羅.奧斯特在十五歲那年,讀到杜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非常震撼,那時候就立志以後也要寫這樣的小說。在後來的小說創作中,奧斯特始終試圖嘗試對生命中的重大問題提問。「我沒有解決任何重大問題,這就是我還一直堅持提問的原因。如果找到了答案,可能也不是正確的答案。我雖然沒有答案,但是還是對尋找答案有一種迷戀,所有的作家窮其一生都是一個尋問的過程,而且推動他們追尋的動力是他們所未知的東西,而不是已知的東西,一開始似乎都是潛意識的東西,然後再繼續挖掘、探索。」
在保羅.奧斯特的不少小說中都可以看到紐約做為背景。紐約不僅是奧斯特生活的城市,更是他小說中的真實的場景,就像電影外景地一樣。荒誕情節中的細節都發生在真實的場景之中:布魯克林的街道,曼哈頓的地鐵,唐人街的車衣廠……在〈玻璃之城〉中,奧斯特這樣寫道:「我來到紐約,因為她是最迷失也最淒涼的地方,一切都很脆弱,到處紊亂不堪。你只要睜眼瞥一下,到處充斥著脆弱的人、易碎的東西、軟弱的思想,整座城市是一堆破銅爛鐵。」這些以紐約為背景的小說形成了奧斯特鮮明的創作特色。《週日泰晤士報》評價道:「透過筆下鮮明的紐約,秉承偉大的美國傳統,迸放活力四射的文學創造力。」
「我最主要的身分還是作家,主要的任務是寫小說。在寫小說之前的十年是翻譯、寫詩、寫文章,但我一直想寫小說,一直在想怎麼寫小說。一九七九年開始小說寫作之後,就一直寫到現在。」寫小說的時候,保羅.奧斯特和每個有正常工作的人一樣,七點到九點左右起床,坐在餐廳的椅子上,喝下去一大壺茶,看完報紙,然後去住所附近不遠的一個小屋子,在那裡開始寫作。路上買個三明治,午飯時間,餓了就邊吃邊寫,下午四、五點的時候結束工作。平時不用電腦,更不會使用電子郵件。
奧斯特身分繁多:小說家、詩人、劇作家、譯者、電影導演。他與華人導演王穎合作了兩部電影--「煙」和「面有憂色」。一九九○年,《紐約時報》的編輯給保羅.奧斯特來電話,報紙預留了耶誕節那天倒數第二版整版,請他寫一個短篇小說。奧斯特從來沒寫過短篇小說,但還是答應了。小說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王穎看到後,覺得很有趣,就打電話給奧斯特,想把小說拍成電影。奧斯特以前看過王穎描寫三藩市唐人街的電影「陳先生失蹤」,對王穎很是欣賞。後來王穎來到紐約,奧斯特帶他在布魯克林轉了轉。王穎說,我要把你的這個短篇小說做成真正的劇情片。王穎請另外一個作家把小說寫成了電影大綱,然後寄給奧斯特。奧斯特看了之後,不太滿意,和太太一起又編了一個電影腳本。王穎看了之後認可了這個版本。接下來尋找資金的過程也頗為順利,王穎去東京辦事,和一個日本製片人談起這個電影腳本。這個日本製片人正好又讀過奧斯特的作品,很喜歡。日本製片人說,你真要做的話,把作者拉進來,我提供一半的資金。王穎回來之後,在美國又碰到一個美國製片人,解決了另一半資金。找到拍攝資金之後,王穎拉著奧斯特一起物色演員、編輯、拍攝,一共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奧斯特對這段經歷念念不忘:「王穎是我的老師,教了我很多電影方面的東西。」「煙」後來獲得柏林影展銀熊獎和最佳編劇獎。後來拍第二部電影「面有憂色」,那時候王穎已經病了,大部分導演工作是奧斯特承擔的。
由於「煙」的成功,保羅.奧斯特應邀擔任坎城電影節評委,那一屆的評委中還有鞏俐。鞏俐說的是普通話,而給她派的翻譯講廣東話,結果無法溝通,只能請鞏俐的經紀人做她的翻譯。看完電影之後,評委發言,鞏俐對參賽影片進行藝術評判,前後講了五分鐘。但是翻譯只講了一句:鞏俐喜歡這個電影,鞏俐不喜歡那個電影。就完了。令保羅.奧斯特印象深刻的是鞏俐非常漂亮,他盡量靠近鞏俐,坐在鞏俐旁邊,「她的皮膚非常好,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好的皮膚。」
二○○七年四月,紐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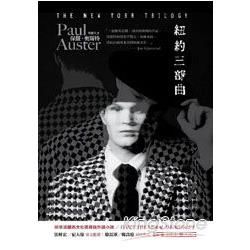
 2014/09/01
2014/09/01 2011/12/11
2011/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