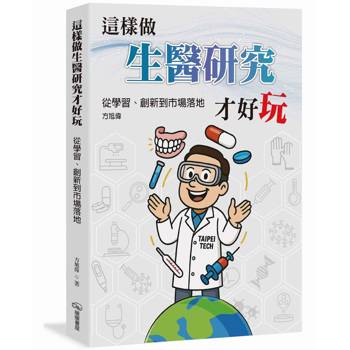願記憶與歷史同步前進
十九世紀英國文壇巨擘托馬斯.卡萊爾在一八四○年作了六次演講,他開宗明義說:
我在這裡談談偉人,有關他們在世界事務中出現時的風采,他們如何在世界歷史中塑造自己,人們對他們有何想法,以及他們做出何種功績。
這些演講後來集結成一本書《論英雄及英雄崇拜》,百餘年後仍是經典名著。
近世的美國作家羅伯.唐斯與卡萊爾遙相呼應,他在《巨人及其思想》這本書中指出:
在每一個歷史時代,我們都可以找到證明偉大人物及其思想力量強大的證據,沒有他們就不可能有高度的現代文明和文化。
這些人物,這些議論,不僅在西方,中國同樣也有。梁啟超因「戊戌政變」事敗遠走海外十餘年,於一九一二年秋天返國。胡適在日記中寫道:
閱《時報》,知梁任公歸國,京津人士都歡迎之,讀之深嘆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任公之賜。……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今年適逢辛亥革命一百年,我們重讀胡適對梁啟超的評價,尤覺意義深長,而且感慨殊多。
百年來的民國,飽嘗憂患,歷經艱險,失敗過,屈辱過;但是也曾有奮鬥的激情,有成功的喜悅。回頭細數這些印記,都一一刻在國人心底:
──辛亥革命,烈士們的頭顱與熱血,換來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度過了建國初期的逆流與險灘,結束軍閥割據,國家完成初步統一;
──但日本不容中國站穩腳步,就發動了長達八年的侵略戰爭,中國人民生命傷亡之巨和財產損失之重,世界史上少見;
──抗日雖然勝利,內戰繼之而起,中華民國政府倉皇遷台,幾至覆亡;
──所幸朝野勵精圖治,不僅使台灣屹立不搖,且創造了經濟奇蹟,也完成民主轉型、政黨輪替,並充分發揮了文化創造力。
無庸諱言,慶祝百歲華誕的民國,在外交上仍有局限,在內部也有族群意識等問題,但大體上說,以台灣為基地的中華民國,安和樂利,欣欣向榮,無負於革命先烈和時賢的犧牲奮鬥,也正努力踐履他們當年對國民所作的承諾。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遺囑中叮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此處的「革命」,應不僅指推翻滿清、建立民國,而有「革故鼎新」之意,亦即要不斷追求國家的進步與富強。而此處的「同志」,亦非僅意在國民黨人,而是泛指信仰和支持民族、民權和民生主義之全體國人。是則,參與辛亥起義的黃興和宋教仁固然是「同志」,推動民主思想的蔡元培和胡適也是「同志」;在科學和藝術上成就卓著的吳大猷與張大千,以及在台灣戮力經濟建設以強國富民的孫運璿和李國鼎,一樣也都是「同志」。有了這些人的努力,中山先生「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的理想,才有逐步實現之可能。
民國百年,我們感念這些「同志」們,心中興起無限的景仰與感懷,特別編輯《百年仰望──二十位名人心目中的民國人物》這本書,一方面向他們致敬,一方面也藉他們的言傳身教,給後人一些啟發與指引,讓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對未來的前路能看得更清楚,因而走得更穩健。
百年來先烈時賢的英雄榜,別說二十位,就是兩百位、兩千位也不能盡數。我們這次邀請二十位學者專家,請他們分別寫一位他們心目中的民國人物,俾能各自彰顯這些人物的功業與代表性。這樣的一本書,自然有它的不足之處,第一、名額不夠充分;第二、領域不夠寬廣。但如前面所說,除非我們編輯數十巨冊《百年民國名人傳》,否則這類遺憾一定無法避免。
所以,我們雖僅標舉二十位先烈時賢,實則是向所有曾為民國戮力獻身的先行者致欽敬和感謝之意,他們的大名不一定要在本書中,甚至不必在任何一本書中。
最後我們還想說的是:今天,我們回憶先人為我們所做過的事;但我們留下了些什麼,供明天的人回憶我們?
願記憶與歷史同步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