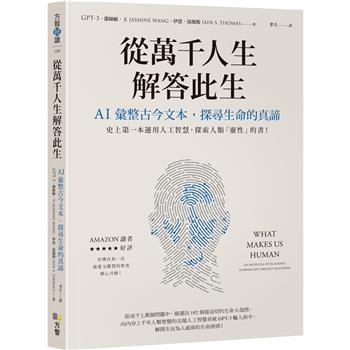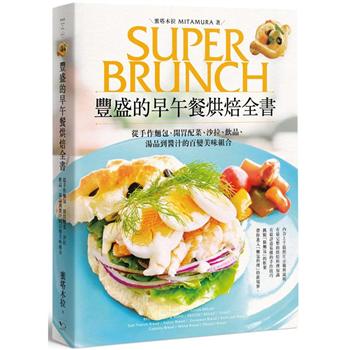自序
遠方的召喚
雷驤
在異地旅行。寄宿的旅邸女掌櫃,忽一日向我要求畫圖,並拿出三張八開大小的厚白紙來,說:如果畫不出,就不能證明你畫家的身分,本店謝絕續住!
這當然是夢境。我在夢中竟毫不躊躇,繪畫題材立即成竹在胸,便在攤開的白紙上提筆畫起水彩。但是奇怪,怎麼調和顏料,總是跑出一大堆白色來,開始還好,能用出現的粉藍 / 淡紅 / 灰褐塗好一塊塊底色,之後要用彩度較高、調子較深的顏色進一步勾勒形象的時候,白顏料仍然自動跑出來相混,只能重疊一片片灰塊,以致怎麼也畫不成一幅圖景,令我焦慮不堪。此時有些覺得自己已醒來,用清明的理智在挽救一幅畫,可那甩不掉的混白現象,違背我的經驗,幾不能辨別何者為真……。
我畢生多夢,對于夢境的奧義也許並不自明,但覺情節常呈異趣,有時便記寫出來如上者。
現實生活中,對繪事與寫作兩樁從未自疑過,乃日日無間之事。當憂傷來襲的時候;當失去目標的時候,提筆繪、寫便是我召回注意力和感覺性的方法吧。
在此書中的諸篇即為專欄稿集,素材看似貼近實生活的樣相,每當提筆梳理它們的時候,總有一種非現世的對待態度,那是我的性情。
某一天黃昏,閒坐起居室的時候,無意間聆聽遠遠近近鳥鳴不已,心境寧靜有如兒時唱的歌:「天甚青,風甚涼,鄉愁陣陣來」,然而思索之下那鄉愁是什麼呢?自己生誕之地?少時嬉遊之所?似乎是,但細究下去卻都不是!那鄉愁可說來自某種隔世的意識,十分熟稔,卻畢生絕未之見的風物。彷彿我靜靜的坐在這兒,收悉到一種啟示與召喚;或者覺著「現下才是夢境,而另有一個醒後的真實世界。」
古記事中也記載著類似的感覺:一個人碌碌奔波,宦海幾度浮沉,經過了大半輩子,在南柯郡做過太守,一切歷歷。醒來卻見自己在廊下臥塌小睡而已,兩個送他回來的朋友,還在一旁洗腳唷。
當這麼想的時候,就恍然覺得:自己當下寧非活在夢境之中邪?
推薦序
冷眼看繽紛
吳念真
曾經常常想起一些名字:張照堂、阮義忠、莊靈、杜可風、雷驤….。
不知道為什麼。
直到有一天意外地搜尋到張照堂先生的部落格,看到一些當自己還是一個「文藝青年」的時候曾經被深深地觸動的照片,那時候才恍然大悟,原來這群人都是自己在「影像」這門功課上的啟蒙者,無論是sense、技術或態度,無論是靜態攝影或者動態的紀錄片。
是因為他們的作品的誘導,讓我在一九七六年標會買了人生的第一部照相機,並且在之後認真且嚴肅地想過:文字創作如果連你所關注、所描繪的對象都由於閱讀能力的不足而得不到一些許安慰的話,那影像會不會是一種比較直接、有力的工具?
我不敢說自己後來的工作選擇是被這些人所左右,但影響絕對有。
而「雷驤」這個名字好像不只是和影像有關係而已,記得報紙副刊上一些直到今天都還記憶猶新的文章的刊頭上都會經常出現,寫著:插圖 / 雷驤。
他的圖畫很容易認,顫動、扭曲的如糾纏的鐵絲一般的線條擱在濃淡相間的墨痕上,有時候讓人覺得:怎麼再曲折複雜、驚心動魄的故事在他的「冷眼」下好像都不過是幾筆清淡、無色彩的素描勾勒而已?
當陸續讀過他許多文字創作、看了許多他的紀錄片之後終於明瞭,當初對他那種「冷眼」的直覺並沒錯,因為無論文字、影像或圖畫就像他這個人,始終以冷靜的眼光凝視著世事的變換和時光流轉;或說是因為這樣人,所以必然出現這樣冷靜、素樸然而卻又後勁十足的文字、影像和圖畫。
不知道《浮日掠影》這本書的寫作時間橫跨多久,也沒細數它到底涵蓋了多少的人、時、事、地、物,但在閱讀的過程裡,老有一種奇特的幻境出現:好像雷驤就站在我身邊,不動聲色地拍拍我,指著一處風景、一個人或者一個正在發生的事件、一段即將被遺忘的情感要我看,而當自己在情緒還沒來得及抽離的時候,他又拍拍我,緩緩地伸出手來,指著另一個方向。
記得曾看過他的一篇文章,寫的是一次生死瞬間的經歷(但你一定知道,用的必然是極其冷靜的筆調),說有一次他去拍紀錄片,所搭乘的直昇機意外失事墜落在中央山脈,他護著一部昂貴的攝影機安全脫身,之後他走回直昇機殘骸時,才發現另一部在緊急狀態下被他棄置的小攝影機竟然還繼續錄影,「忠實地隨著鏡前的風吹草動自動對焦呢。」當我讀到這裡的時候,幾乎忍不住笑了出來,想說:雷驤自己到底知不知道這樣被他描述著的攝影機其實正是他自己呢?任世事變換、時光流轉,他不也是始終用冷靜的眼光凝視一切,且忠實地為我們自動對焦嗎?
不過,他應該不知道吧?因為他一如以往,依然忘我地為我們搜尋、記錄或導引我們的眼光看向那些我們所無暇顧及的、所冷落、漠視甚或早已遺忘的人、時、事、地、物。
推薦序
親愛的人
傅月庵
我認識雷驤老師時,他已過了不惑、知天命、耳順的生命階段,漸漸從心所欲了。
這時候的他,總是微笑的,幾乎沒什麼脾氣。對世事人情,自有其看法,姿態卻十分隨順。喝酒時,也會聊到文壇種種,我愛跟他打聽這位那位作家,他信手拈來就是一段故事,但總是敘述多,評點少,最常聽到的結論大概就是「世間怎麼也有這種人?到底在想什麼,我都不知道了。」這話是以台語發音,前面還會加上一個感喟兼好奇的語助詞:「ㄏㄟ ~ 」,彷彿真希望有機會更深入理解這人的思維模式。
這種好奇的探索,在我看來,或即是構成整個雷驤創作的原始動力。從文學、攝影、繪畫等創作,乃至,嗯,教學。跟雷老師學過畫的人都知道,不管你再怎麼不行,畫得如何差,雷老師總是有辦法讓你尋回信心,確認屬於自己的繪畫之道。他總是能在你覺得一無是處的畫面裡,找出某幾個筆觸,某幾筆線條,或者從構圖角度,發現你的特殊之處,然後向你解釋、告訴你:「這個處理得很好,ㄏㄟ ~ 不簡單哩。」--雷老師的這句話,與其說是「因材施教」的鼓勵,毋寧還是那個好奇在作祟,他總是想知道且很快能知道學生的特質與可能,將之點顯出來,回答了自己的好奇,也讓學生有種「嬾嬾馬嘛有一步踢」的自得,而竟有了動力繼續探索、學習下去。
好奇心其來有自,嬰兒、小孩的好奇,純屬上天的恩賜。隨著入世漸深,卻還能對這個世界保持濃烈好奇心的,總不外乎「懷疑」或「相信」。由於懷疑既有的秩序,不承認「凡存在的必屬合理」,因而好奇想探索秩序背後的東西,此種懷疑的好奇,多半伴隨某種不滿,對體制、對人間的不滿;相信的好奇,則有種敬愛,也許在碰撞太多之後,更深刻地體悟出「凡存在的必有可能」,從此不敢小覷人間既有的一切,轉而想窺探可能的極限。因為有敬有愛,也就有了悲憫,我深信,當我認識雷驤老師的時候,他對人間的好奇,已從懷疑轉為相信,對於萬事萬物都有了一種悲憫。這種悲憫,讓他終日微笑,文章繪事教學滿溢溫情與敬意,而竟不知老之將至了。
那是一九八○年代中期,退伍歸來略識人間大難的我,依然不改逛舊書攤的習慣。某次偶然買到一本當時剛成立不久的圓神出版社的《矢之志》,第一篇為〈犬〉,講一隻沉靜的粟色土犬,日夜奔走了遙遠的道途,前來咬死一名新婚婦人的故事,內容夾雜靈異、愛情、驚悚等元素。使我最感興趣的,卻是冷靜得像攝影機的敘事方式,由於這一自制的冷靜,犬之怨念遂擁有強大能量,讓人讀著讀著竟不寒而慄起來了。「我喜歡這作者!」於是決定收集他的作品。彼時雷老師僅有另一本名為《青春》的散文集,從那本開始,一路收集,未必緊盯著不放,但過個幾年,總會揀拾一番;入手也不一定即看,往往累積二三本看了又看。但總之,經過十多年之後,因緣得與雷老師相見相識,跟他學畫畫時,我幾乎毫無生分之感。他的整個家族、他的北投居所一草一木一犬一池、他的身世流轉友人聚散,老實說,我早熟得不得了。此時相遇,絕非「一見如故」,而是「如故一見」!
「畫人之眼」是什麼?用繪畫來講,是視角是顏色是物我關係。轉換成文字,成了敘事角度、用字輕重和憫人體物的一點念想。雷驤慧眼獨具,利如鷹隼,熱在心頭,冷在筆下。
曾經在一篇《刑台與手風琴》的書介裡,這樣談論過雷老師的書寫本質,自認雖不中亦不遠矣。但我始終縈懷難解的一件事是,明明可以具體感受到他從「懷疑」到「相信」,從「不滿」到「敬愛」的幽微風格轉變,卻一直無暇去細辨這一關節——到底誰讓他去信、去愛了呢?
某年秋天,我又想起了這件事。於是,自秋徂冬,我經常睡後又起身,深夜裡,把書架上一本又一本的雷驤作品,拿下來翻看,邊看邊追憶,追憶初次閱讀的心境,也用更多的理解去探索熟悉的篇章。第一道寒流來襲之夜,我又讀到了一九九八年雷老師到日本追索楊逵、魯迅、周作人、郁達夫等人文學蹤跡時,於異鄉寫給「親愛的人」的家書片段:
. 啊,這樣繁瑣、吃重的旅行,我幾乎應付不來,能有什麼斬獲,實在毫無把握啊。疲累中幾度飄過妳往日笑顏,有話同我說嗎?
.收到兩封傳真一並--前一封在京都時已收到過一次了,但閱信時的溫慰無比,簡直到了激動的程度。……。妳的久咳難癒,即使妳自己如何故做輕鬆帶過,但那苦,唯只愛憐妳的人才深烙上心。臨走前,妳為我整行囊、熨衣服的舉動,此刻忽又重現,予我竟生一種懺情!
.雪,大約還下不起來的。讀了信,我想媽一定能渡過此難,祇是更且衰弱下去罷。人的生命實在堪憐,如何面對自己的生命相,在此也想了一想了。……。外面寒風呼號。即擁抱!
「外面寒風呼號。即擁抱!」前次閱讀時,未婚無子的我,但覺得這句子寫得好,插入文章的家書片段用得巧,如今結了婚也生了子,再讀一遍,竟感動莫名,字字都有了著落。--「啊,六十歲時,我也還有心寫這樣的情書嗎!?」--「寒風呼號」而為「擁抱」,「懷疑不滿」終成「相信敬愛」,看來都因「親愛的人」了。我又想起了酒後老師老愛說的昔年為伊獨立平交道不斷朝火車揮手的青春少女時的那份靦腆神情,以及我們在閒話彼此「親愛的人」時,他所透露帶著飽足愛憐與好奇的苦惱:「真正係沒話講,有夠好的啦。但是嘛有一點點煩惱。最近又跟我說想買一套義大利鍋子,十幾口哩。煮一個料理敢愛這麼多?真正讓人想攏無哩。」道假諸緣,復需時熟。如今,我也終於能瞭解其中更深刻的意義了。ㄏㄟ ~ 不簡單哩。
四十多年來,雷驤一切創作,只為一個女子,名叫Amy。如今,我們或稱之「師母」而不名。二○一一年的新書扉頁,一仍舊貫,我相信還是會有「獻給Amy」的字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