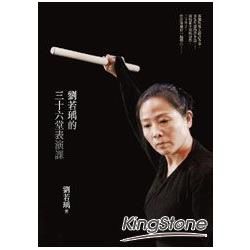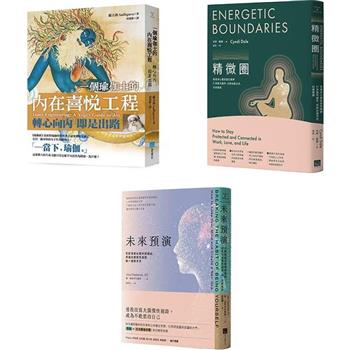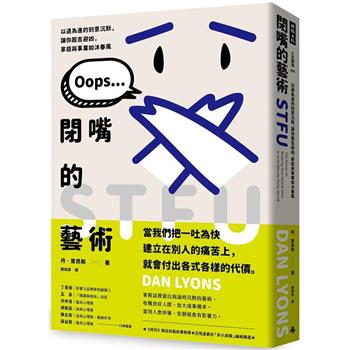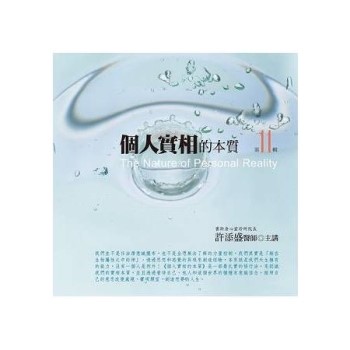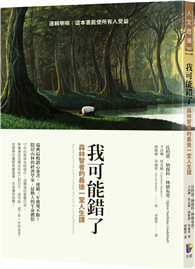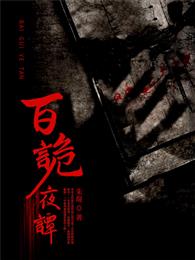推薦序一
是禪?還是秀?
李安
多年前,在紐約看了一場優人神鼓的演出。表演非常精彩,結束時掌聲如雷,歷久不歇。秀秀〈老友們慣稱她小名〉最後上台謝幕。其體態寧靜了然,眼神不理不露,一副已然得道的模樣,我看了覺得很有意思。
當晚,我請團員們吃消夜,席間我丟給秀秀一個無厘頭的問題:「你們是在參禪,還是在做秀?」秀秀愣了一下,眉頭隨之深鎖,思尋了好一陣子。之後大家吃飯聊天,這問題也就不了了之了。
很高興讀到她這本書,對表演或生活有興趣的人,這本書值得一讀再讀。雖然以前我問秀秀的是一個不會有答案的問題,但從這本書中,我讀到對這個議題許多深刻的探討,她讓我了解到秀秀這些年來刻骨銘心的發展歷程。
在我做學生學表演的時候, Growtoski就一直是我的一個偶像。這本書最可貴之處是,他不只是一個 Growtoski訓練的見證,他是一個學子上課後多年驗証的一個反思。一位西方的劇場高人,參了東方的禪理,反芻教導東方學子,再由她從自身文化的根源,印証到她的本性,來回三十年,其內容自有許多發人深省之處。
真虧秀秀一切記得那麼清晰,也講述的這麼確切易懂,想來這些道理與體驗,對她來說一定是極深刻的,謝謝她把這些寶貴享嘉惠我們。
我從事影劇工作多年,對表演與人生是有「人生」因為我們必須與他人並存共處,需要得到別人的認可,壓抑本性,表演出最合理討喜的一面是必要的。而演戲,因為只是揣摩角色,並非本人,反而我們更願意真心投入,顯露真性。所以戲劇〈演戲也好,看戲也好〉是不是我們更應該正視的功夫與課題呢?
禪也好,秀也好,它們不都是追求真性的努力嗎?有甚麼好問的!
推薦序二
修行和藝術的扎實結合
賴聲川
我第一次看到秀秀(大家都叫若瑀的小名)是一九八二年。她年輕、亮麗,散發出不可思議的青春力量,正在和一群夢想家共同創造「蘭陵劇坊」在台灣實驗劇場史中不朽的地位。這一群朋友,包括她、金士傑、卓明、尤慶琦、黃承晃、金士會、杜可風等,正在創造一個重要的另類文化,台灣從來沒有見過的創意表現。
時間轉到一九八五,我已經回台灣常住,在國立藝術學院(今日台北藝術大學)任教。除了在學校做的幾個實驗性即興創作作品之外,我和蘭陵合作了一部戲叫做「摘星」,當時秀秀出國了,沒有機會跟她合作。一九八五年,「表演工作坊」已經成立了,第一個作品「那一夜,我們說相聲」,令我們意外的成功,尤其是在大眾方面。第二部戲要做什麼?我們壓力很大。秀秀剛從美國回來,我知道她在和世界實驗劇場之父果托夫斯基學習,當然希望她加入我們正要發展的「暗戀桃花源」。但我心中有些疑慮,因為我在柏克萊的時候,有幸見過果托夫斯基,聽過他的演講,後來也知道他一個特別有野心的計畫被柏克萊否決了。之後才知道這個計畫移到爾宛,那也就是秀秀參加的表演訓練計畫。
我當時的疑慮是:果氏那些年正在創造一種結合修行、演員訓練和藝術表現的訓練,其實就是一種修行的方式。那個時代很流行自創心靈修行方法,我擔心的是果氏所尋找的人生真理未必會出現在他希望創造的修行中。有更多早已成形成熟的修行傳承,在世界上已經普遍實行了幾千年,是已經被證實能成功的方法,目標是一樣的,一個人為什麼要自創修行方法?他的實驗尚未成熟,他的學生有沒有任何風險?
一九八五—八六年在「暗戀桃花源」排練的過程中,我和秀秀充分討論過這些問題,當然也感受到她在果氏訓練之下學了一身功夫。但奇怪,這些功夫未必能運用在我正在成立的「即興創作」體系上。我那次的工作是要把她從果氏訓練中拉回到她最本能的表演才華,同時尊重她的果氏訓練,因為我也感覺到那是很珍貴的。最後她交出了漂亮的成績單,「暗戀桃花源」的『春花』於是成形了,後來所有演春花的演員也要根據秀秀所塑造的人物來飾演這個角色。
事隔多年,我知道秀秀開始走向打擊樂,也感覺到她這個新追尋背後真正的支撐力量是人生的修行,這兩者對秀秀來講是從來不分開的。看著她這些年的藝術呈現,我更欣賞到她在爾宛受果氏訓練所帶來的豐碩成果,因為我感覺到她真正把這些訓練融合到她的生活與藝術之中。
鏡頭轉到二○○九年,我在籌備台北聽障奧運會的開幕式。我請秀秀訓練八十位聽障高中生,希望他們能夠和已經世界著名的優人神鼓同台在開場時演出。秀秀表示保留,她不認為這些聽障青年能夠禁得起優人神鼓嚴格的訓練。我還是請她盡量試試看。過不到兩星期,她電話來了,激動的罵我:「不可能!這根本不可能!他們聽不見!要我怎麼訓練!」這時我們也接到許多家長的來函,嚴重關切此事,說我們這樣送孩子去做這嚴格的訓練,等於是讓他們受他們人生最大的挫折和侮辱。我還是希望秀秀耐心,因為我認為,她做不成就沒人做得成。
過了一段時間,有些進展。秀秀和優人神鼓的老師們找到一些方法來帶這些孩子,又過了一段時間,我親自去看他們排練,整齊劃一的表現讓我感動到熱淚盈眶。秀秀說:「還不行,他們還差一段距離。」
二○○九年九月五日晚上台北聽障奧運會開幕,讓全世界看到這八十位聽障孩子與優人神鼓共同精準的打出振奮人心的鼓聲。優人神鼓要求的所有精氣神,全部準確的釋放出來了,震撼並感動全場。後來家長也跟我寫信謝謝我們,謝謝優人神鼓,讓他們的孩子享受到此生最大的榮耀。
這些點點滴滴,是我所認識的秀秀。這些年我看著她的優人神鼓跑遍世界,賦予觀眾豐富的精神糧食。我非常佩服看到一個本質上是修行人的秀秀,其實本質上也是藝術家。她把這兩者融合得這麼巧妙,讓她的藝術與人生同樣散發出高度的品格、尊嚴、紀律與智慧。這是她的第一本書,來的實在很晚,但我相信讀者朋友能夠在這三十六堂課中,不但學習表演,更學習人生的修行。
自序
三十年釀就的體悟
劉若瑀
從優劇場到優人神鼓,轉眼劇團已成立二十多年。從第一天開始,我就想告訴團員們,深埋在心中的「表演者」是什麼;雖然斷斷續續的提及,但始終片斷,也難深入。
這本書終於在忙碌的工作之中整理出來了。我想,在這期間,除了團員的好奇外,還有很多對表演好奇的年輕人,想一探當年我在加州的經驗。離開加州已三十年了,這麼多年來,從優劇場開始,我並沒有直接教導當年老先生的方法,大多數的訓練都已經過我個人的轉化,也不能稱為是老先生原來的訓練方法了。但是當年老先生智慧的引導,至今受用無窮。這本書裡的大多數故事與資料,都只是老先生當時的一句話,有些是刻意說的,有些也許只是不經意說的,但在心中成為一個對自己反省的觸動,多年來,仍然令人記憶深刻,也從中再發現了新的感觸。
這也是我為什麼在本書中不直接指明老先生的名字,因為這本書中,除了一些具體的英文字之外,大多數內容都是我的領悟與思想,所以其中的人名也都不是當時同伴們的真實姓名,也有一些情境、故事是重新架構的。這本書雖然是那一年的體悟,不過終究加了三十年。然而,沒有這三十年,恐怕也難看見真相。
不過,終究所有靈感都來自當年在加州跟著老先生的學習,所以我仍要將這本書獻給我的老師,「老先生」。
跋
表演課尚未結束
劉若瑀
整理完這本書時,我眼中泛出淚光。已經三十年了,才將內心深處的記憶整理出來;一個很大功課完成了,感謝大師,在我生命懵懂的年紀遇見了他,雖然現在在實際對學生的訓練課程中並沒有大多直接相關的方法,但,所有的觀念和觸動都在即時啟發。
關於研究表演這門課,似乎是自己最大的直覺;雖然優人神鼓在打鼓,但所有的表演者除了鼓之外,每一個眼神、走路、舉手和工作方式,都在這門表演課堂的影響中,慢慢成長。表演課尚未結束,這只是上半段。一個真正的表演者,是老師終生的職志;在我心中,也早已種下基因,在對觀照自己的的深入解後,有一些事已在開始。
那年阿襌到印度旅行。那是他第四次到印度,住在菩提迦耶的一座緬甸寺廟裡。有一天早晨打坐的時候,他看到稻田裡有一隻正在覓食的鸛。鸛的動作輕盈靈巧,讓阿襌不禁看得入迷。看著,看著,阿襌發現自己跟這隻鸛的起心動念同步了,鸛一啄食轉、轉頭、抬腳,他都感同身受。這是一種與物體打成一片、物我合一的階段。我想一位真正的表演者,是需要一種真功夫。老師當年說,在東方那未知的古人智慧裡。
下一階段的表演課,我們將探討「一位真正的表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