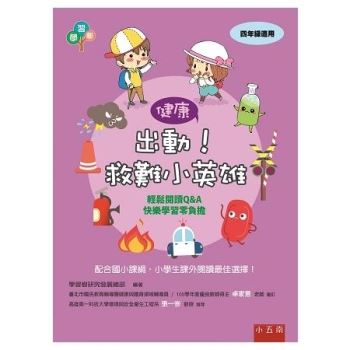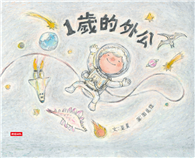許多人都讀過陳之藩先生寫的〈謝天〉、〈失根的蘭花〉,他的散文《旅美小簡》、《在春風裡》、《劍河倒影》更為許多書迷所津津樂道。
陳之藩先生學的雖然是科技,在心裡卻始終為文學保留著一席之地。他曾說科學與詩很相近,「科學界的研究科學,與詩人踏雪尋梅的覓句差不太多。」寫作風格高雅純淨的他,在撰文紀念胡適先生時寫道:「並不是我偏愛他,沒有人不愛春風的,沒有人在春風中不陶醉的。」讀他的散文,也很難不沉醉在他文字的「春風」裡。
《花近高樓》,由童元方教授從陳之藩文集《蔚藍的天》、《旅美小簡》、《在春風裡》、《劍河倒影》、《一星如月》、《時空之海》、《散步》中,編選最精采的四十五篇文章,分為四個部分:〈花近高樓〉、〈月色中天〉、〈晴開萬樹〉、〈溫風如酒〉,有關於文明的思考的,有涉及價值的取捨的;有觀照人世的體悟的,有偶寄閒情的隨筆的。童元方教授形容:「陳之藩早期的散文,比如《旅美小簡》的語言華麗多姿,而情感澎湃,沛然莫之能禦。問題思考的層次分明,表達的手法漂亮,展露出陳氏在文學創作上的才華,機鋒處處。到後期的作品,一如滿天的華采隱隱收攏在浩渺的烟波之中,清光凝定的氣派,令人想起『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
從二十多歲滿腔熱血的知識青年,到成為走過二十世紀最光燦的科學歲月的智慧長者,陳之藩一直用獨特的、兼具理性感性的筆,記述他對當代、對科學、對文學的見解,文中處處流露知識份子憂國憂民的情懷,卻不盲目的人云亦云。即使早期文章相隔已有半個世紀,現在看來仍經得起時間檢驗,歷久彌新。
作者簡介:
陳之藩(1925~2012)
北洋大學電機系學士,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科學碩士,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副研究員,休士頓大學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波士頓大學研究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系榮譽教授。年輕時即是胡適的忘年小友,梁實秋的暢談夥伴。除了科技領域的一片天,他始終在心裡為文學保留著一席之地。著有電機工程論文百篇,《系統導論》及《人工智慧語言》專書兩冊;散文集《大學時代給胡適的信》、《蔚藍的天》、《旅美小簡》、《在春風裡》、《劍河倒影》、《一星如月》、《時空之海》、《散步》等;作品多篇選入臺灣和香港的中學教科書,對青年學子產生極大的影響力。此次由《陳之藩文集》中編選四十五篇文章而成《花近高樓》。
編者簡介
童元方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士、美國奧立岡大學藝術史、東亞研究雙碩士,哈佛大學哲學博士。曾任教哈佛大學、並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教授,現為東華學院教授兼人文及社會科學學系系主任。中文著作有《一樣花開──哈佛十年散記》、《水流花靜──科學與詩的對話》、《愛因斯坦的感情世界》、《為彼此的鄉愁》、《田間小徑──走向科學的人文隨筆》、《選擇與創造──翻譯論叢》、《遊與藝──東西南北總天涯》、《閱讀陳之藩》,譯作有《德日進思想簡介》、《愛因斯坦的夢》、《情書:愛因斯坦與米列娃》與《風雨絃歌:黃麗松回憶錄》。英文著作有:Two Journeys to the Nort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oetic Journals of Wen T’ien-hsiang and Wu Mei-ts’un, 譯作有明代女子曹靜照、馬如玉以及清代女子吳規臣、梁德繩的詩,收在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一書中。
章節試閱
哲學家皇帝
到此做工已半月,不像是做工,像是恢復了以前當兵的生活。如果我們中國還可以找出這樣緊張的工作,那只有在軍隊裡了。同事的有從韓國剛當過兵回來的,有遠從加州大學來的學生。我問他們,美國做工全這樣緊張嗎?他們異口同聲說:「這裡可能是最輕閒的。」
如不置身其中,可能怎樣說也不容易說明白。在日光下整整推上八小時的草;或在小雨中漆上八小時的牆,下工以後,只覺得這個人已癱下來,比行軍八小時還要累得多。
今天下工後,已近黃昏。我坐在湖邊對著遠天遐想。這個環境美得像幅畫。當初造物的大匠畫這個「靜湖」時,用的全是藍色。第一筆用淡藍畫出湖水;第二筆加了一些顏色用深藍畫出山峰;第三筆又減去一些顏色,用淺藍畫出天空來。三筆的靜靜畫幅中,斜躺著一個下工後疲倦不堪的動物。我想整個美國的山水人物畫,可以此為代表。
雖然眼前景色這樣靜、這樣美,我腦海中依然是日間同事們的緊張面孔與急促步伐的影子。我的脈搏好像還在加速的跳動。我昏沉沉的頭腦中得到一個結論:「這樣拚命的工作,這個國家當然要強。」
中學生送牛奶、送報;大學生做苦力、做僕役,已經是太習慣了的事。這些工作已經變成了教育的一部分。這種教育,讓每一個學生自然的知道了什麼是生活,什麼是人生。所以一個個美國孩子們,永遠獨立、勇敢、自尊,像個哲學家帝王。
希臘哲人,想出一套訓練帝王的辦法,這種辦法是讓他「從生硬的現實上挫斷足脛再站起來,從高傲的眉毛下滴下汗珠來賺取自己的衣食。」這是做一個帝王必經的訓練,可惜歐洲從未實行過這種理想。沒有想到,新大陸上卻無形中在實踐這句話,每一個青年,全在無形中接受這種帝王的訓練。
做卑微的工作,樹高傲之自尊,變成了風氣以後,崢嶸的現象,有時是令人難以置信的。耶魯大學有個學生,父親遺產三十萬美金,他拒絕接受。他說:「我有兩隻手,一個頭,已夠了。」報紙上說,「父親是個成功的創業者,兒子真正繼承了父親的精神。」
青年們一切都以自己為出發,承受人生所應有的負擔,享受人生所應有的快樂。青年們的偶像不是叱吒風雲的流血家,而是勤苦自立的創業者。《富蘭克林自傳》,是每個人奉為圭臬的經典。
我們試聽他們的歌聲,都是鋼鐵般的聲響的:
人生是一奮鬥的戰場
到處充滿了血滴與火光
不要作一甘受宰割的牛羊
在戰鬥中,要精神煥發,要步伐昂揚
─朗費羅
我很欽佩在綠色的大地上,金色的陽光中,一個個忙碌得面頰呈現紅色的青年。
然而,我在湖邊凝想了半天,還是覺得,這個美國青年畫幅裡面仍缺少一些東西。什麼東西,我不太能指出,大概是人文的素養吧。我在此三、四個月的觀感,可以說:美國學生很少看報的。送報而不看報,這是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
「哲學家帝王」,不僅要受苦,還要有一種訓練,使他具有雄偉的抱負與遠大的眼光,可惜這一點,美國教育是忽略了。忽略的程度令人可哀。
愛因斯坦說:「專家還不是訓練有素的狗?」這話並不是偶然而發的,多少專家都是人事不知的狗,這種現象是會窒死一個文化的。
民主,並不是「一群會投票的驢」;民主確實需要全國國民都有「哲學家帝王」的訓練。在哲學家帝王的訓練中,勤苦自立,堅忍不拔那一部分,美國的教育與社會所賦予青年的,足夠了。而在人文的訓練上卻差得很多。
晚風襲來,湖水清澈如鏡,青山恬淡如詩,我的思想也逐漸澄明而寧靜。
天暗下來,星星,一個一個的亮了。
明善呢,還是察理呢?
劍河的水是很清澄的,橋邊的柳是很嫵媚的。但,我想,這些並不是劍橋獨有的特色。倒是這樣大的草地,這麼細得如絲、柔得如絨的綠草,看來令人出神。聖約翰學院的草像一片海,而那堆樓倒像海上航行的古船;克萊爾學院的草像一片雲,而那座橋像雲堆裡浮出的新月。耶穌學院的草地像一個鋪滿了綠藻的湖面;艾德學院的草地又像一個鑑開半畝的方塘。如果沒有草地,那麼多孩子的那麼多樣的夢,何處寄託呢!所以,穿過了五步一樓,又轉出了十步一閣以後,必然是一片藍天與一片綠野湧現眼前。
最能殺風景的倒是我自己。有一天我與一位神甫一同散步,我不由得問他:「這麼大的草地,誰來剪呢?」
好多人都有剪草的經驗,那是件比理髮還頭痛的事。好像昨天剛理了髮,為什麼今天又要理髮了?草地呢,西邊的還未剪完,好像東邊又長出來了。易實甫有兩句詩:
「春風吹花花怒開,春風吹人人老矣。」在美國時,我常常一邊推草,一邊哼哼這兩句詩。後來索性杜撰了四句:
「春風吹草草怒生,春風吹髮髮怒長,幾時才得綠滿窗前草不除,且留白髮三千丈。」
我實在是由於劍橋草地這麼多這麼大而想到殺風景的問題,沒有想到竟由草地而引出一個很耐人尋思的故事:
神甫告訴我:
「這麼多學院的草地,都是由誰剪,我不太清楚。我們樓前這塊草地,是由赫伯特、阿伯特剪的。」
「他是誰?」
「不是他,是他們。這是兩個人。」
「赫伯特一定是德國人了,阿伯特呢?」
「赫伯特是德國猶太人,阿伯特是由赫伯特在公園裡拾來的!」
「拾來的,是個小孩?」
「不是,也是個老頭兒。小孩當然容易被人遺棄,可是,老頭兒更易被人遺棄。」
我讓他這種倒插筆的敘述法愈說愈糊塗,我說:「請你從頭說起罷!」
「你知道劍橋有個『明善』會嗎?當然劍橋的學會太多了,不過這個會是很特殊的。如果把其他的會可以歸併成一個總稱,叫做『察理』的會,那麼,赫伯特、阿伯特這個會可以叫做『明善』的會。
「這個會覺得理是察不完的。如果把『理』都『察』完再做一件事,那就什麼事也不要做了。人生的目的是見到受餓的人,分給他一塊麵包;見到受凍的人,送給他一件衣服。把那個醉倒的人扶住,把那個跌倒的人攙起,凡是自己覺得是善的就直截了當的做出來。
「人生的光榮,是不踏死路旁快死的蟲,是不摧殘樹下受傷的鳥,是把自己口袋裡的錢分出一半來,給一個需要那一半錢的同類!
「赫伯特是這麼個會的會員。他很可能是在希特勒執政時對於猶太人的悲慘如蟻的殘酷命運,所受刺激過深,所以他變成一個服膺明善會的會員。
「他是二次大戰時移民到英國的。很早就住在劍橋了。他好像最初還租所房子,有點營生;但因每天房裡睡滿了他撿來的餓漢,廊前倒臥著街頭拾來的醉人,鄰居們把他趕出來,於是,他變成了這裡的推草的工人。
「推草的工作並不重,他一個人管也儘夠了。可是他又到公園裡拾了個阿伯特來。學院的院主說,我們既沒有可做的工作,又沒有這份錢糧,可是赫伯特願意把床改成兩層,把麵包分成兩半,把阿伯特在人生的孤崖上挽回來。
「於是,我們學院裡有一份錢糧用兩份人工的事。你看,除了草地他們推得特別平整外,那邊的樹叢不也是修剪得格外有致嗎?
「我想你看到過他們的。他們住的屋子距你不遠。你有工夫時可以約他們到你屋裡喝點酒,酒是可以溫暖的,在這蕭瑟的秋天。」
「神甫,我知道了,你不必再說了。」
當然劍橋有的是可歌可頌的故事:牛頓樹的艱難移來,拜倫像的進退維谷,培根的手澤,羅素的巨帙,馬克士威爾的論電波以通鬼神,盧森弗德的裂原子而驚天地……等,都是有光,有電,有色,有聲。可是,像赫伯特、阿伯特的傳奇,卻是我所意想不到的。
我站在草坪前,凝望著那一片綠煙,在想:幾百年來,不知有過多少劍橋人注視著這片草地在那察理,在那窮天;而赫伯特、阿伯特呢?卻是把草剪平、掃淨,並灑上自己一些謙遜的夢想。
自己的路
劍橋有個很大很新的學院,叫做邱吉爾學院。它離校中心相當遠,建築也不是傳統式的。一走近時,好像到了一個美國西部的大學。進入大廳後,有一個邱吉爾的雕像在那裡凝視,沒有一絲笑容。從四面八方而來的研究科學及藝術的人,很多是進這個學院。院長呢,是霍桑教授。我初到此地,他請我喝酒那天,我想問問他劍橋何以有邱吉爾學院,我準知道邱吉爾與劍橋沒有關係。但因喝酒時我順便送給霍桑教授一本我去年出版的書;他翻閱時,就談起一些自動控制界的老人。話題一轉,把我想問的問題給忘了。
有一天喝茶時,碰到一個也在邱吉爾學院的病菌學教授,我又問他,邱吉爾與劍橋究竟有什麼關係。他似乎說,二次大戰時邱首相要隨時諮詢開溫第士實驗室的研究情況,大概這是邱首相與劍橋最有密切關係的時期。但他也說不出劍橋與邱吉爾的特殊關係來。沒有想到這位病菌學教授比我興趣更濃;沒過幾天,他忽然約我星期天坐巴士到牛津大學去玩。他說要路過邱吉爾的出生地與邱吉爾的墓園。為了路上聊天方便,他說不要自己開車,坐巴士最好。
巴士在英格蘭的原野上奔馳。看來是一副典型的半陰不雨的英格蘭天氣。如果用畫筆畫呢,兩筆似乎就夠了。先用有墨的筆沾點水,在上面一抹,那是天;然後再加點綠在下邊一抹,那是地;這幅灰、暗、冷、清的畫面差不多就算完了。當然在這兩抹之間,偶爾有些笨樹,像八大山人之筆所畫的,乍看起來很笨的樹;偶爾有些老屋,像美國那位老祖母畫家所畫的類似童畫的那種老屋。這整幅天氣給人的印象,正似英國人的言談與神色:低沉又黯淡;可是為什麼竟出現了一位聲如雷霆,光如閃電的奇才─邱吉爾。
我忽然想起我小時念的祖父論申包胥的文章,至今仍能背誦如流:
四海鼎沸之日,中原板蕩之秋,不有人焉,屈身為將伯之呼,則宗社淪沉,萬劫不復。士不幸遇非其主,無由進徙薪曲突之謀。一旦四郊多變,風鶴頻驚。……
哎呀,我連一個字也不必改,就可以說成邱吉爾。當然英國的君主沒有申包胥的君主有權。這裡的「主」可以解釋成英國人民。我們看只要是英國岌岌可危時,邱吉爾一定是事先再三提出警告,而人民也一定不聽他的。但等到草木皆兵時,邱吉爾卻總是從容受命,拜閣登臺,扶大廈於將傾,挽狂瀾於既倒。他好像知道大任所在,非他莫屬。比諸葛亮高臥隆中時,對於天下大事所作種種出山準備還要充足。及至狂風已起,山雨已來,好像天地間只有這麼一個巨人,領袖群倫,安然應變。我們試聽他所擂起的鼓聲:「我們要戰,在海灘,在天空,在巷角!」「我們所有的是汗,是血,是淚!」他在美國演說與求援時,說:「我身上流著一半美國的血!」因為他母親是美國人,這話沒有一字不對;可是那話後的辛酸,出自一個傲岸的英人之口,已經近乎秦廷七日之哭了!我沒有辦法不低首膜拜這樣一位令人神為之迷,目為之眩的亙古少有的英雄。
我正在想他那些作珠玉聲,作金石聲,作春雷聲,作時雨聲種種從沁人肺腑,到震人心弦的詞藻,我們的巴士已到了邱吉爾家八世祖所傳下來的裂土封王、世襲罔替的漢宮。
我下車後,好像剛從夢中醒來似的。定睛一看,這幅眼前的畫卻太誘人了。
左邊這半邊天好像都是宮殿,像山似的一片黃色的宮殿;右邊呢?是兩個大湖,像海似的兩座藍色的大湖。中間有一長橋,長橋過後是一古塔,古塔過後是兩排直到天邊的樹。不知是開天闢地時,大匠特別細緻;還是當初建宮時,工人格外用心,這裡的草坡是明媚的,草坡下的湖水是明媚的,湖水中的島是明媚的,島上的樹是明媚的。不像是自然的,不像是畫的,而像湘江少女一針一針繡出來的。
大家站在橋上,有人醉在這忽現的風光裡,有人醉在如雲的夢境裡。在一片驚訝,而又一段安靜之後,有一個人說:
「邱吉爾的媽,到這兒來野餐,一不留神,生出邱吉爾來。」大家全笑了。另一個接著說:「邱吉爾捉迷藏所跳的橋,該不是這座橋罷?」「大概不是,因為這橋邊無樹叢,如果沒有樹叢緩和一下,他在三丈多高的橋上跳下來,是活不了的。那我們現在該在納粹的集中營裡了。」「邱吉爾為什麼從橋上跳下去呢?」一個小孩揚著好奇的臉在問。「他們捉迷藏,他不願讓人捉住,而橋的兩端均有人堵住,只有從橋上往下跳了,皮破血流,三天不省人事!」小孩的母親俯著身回答她的孩子,同時拉緊了小孩的手。
再上車後,大家的話題全轉到邱吉爾身上。但談話剛要開始,車就在一小鎮上停下來。這樣大的巴士,在這樣狹的街上,顯然轉不過彎來。所以人下車後,巴士就去轉彎去了。我們排成單行沿著磚砌的小徑往土坡上走。是一個比我家鄉土地廟還小的教堂,旁邊有橫七豎八幾塊墓碑。靠路邊最近那塊大理石有四尺長三尺寬罷,上面刻著邱吉爾的全名及生年和卒年。而我們這群人中,有的人還半信半疑的繼續張望找邱吉爾的墓;有的人搖頭,硬是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有的人一臉嚴肅在畫十字祈禱;有的人一臉驚訝,說邱吉爾恐怕是葬在倫敦的西敏寺,而並未在此;我卻陷入洶湧的思潮裡。
邱吉爾幼年所遭的坎坷是史無前例的。同班同學,人家都學拉丁文了,把他編入低能班,只有資格念英文。人家都用希臘文作詩了,他依然在低能班念英文。鄰居指手劃腳的嘆息,為什麼這樣個名門貴族出這種白痴;連他父親也不理解自己的兒子,委婉著勸他投考軍校;同學們當面惡作劇,老師們當眾給難堪。天之昏,地之暗,不是一個孩子所能承受的。
我記得我二十年前讀他的幼年自傳時,就激動得想哭;現在想起來,還是五內如沸。邱吉爾好像只有一個老師威林頓安慰過他:「你會奮鬥出一條自己的路來!」
是的!這句話成了邱吉爾心上的座右銘。於是以這樣一個受盡了奚落的少年白痴,而天下風雲因之變色,世間江海因之倒流,他挽救了英國的危亡,扭轉了人類的命運。
我想劍橋的邱吉爾學院,與其說紀念他的蓋世功勳與彌天文采,不如說掬全國之至誠向這位自己開路的人致由衷之感激與無上的崇敬罷!
哲學家皇帝
到此做工已半月,不像是做工,像是恢復了以前當兵的生活。如果我們中國還可以找出這樣緊張的工作,那只有在軍隊裡了。同事的有從韓國剛當過兵回來的,有遠從加州大學來的學生。我問他們,美國做工全這樣緊張嗎?他們異口同聲說:「這裡可能是最輕閒的。」
如不置身其中,可能怎樣說也不容易說明白。在日光下整整推上八小時的草;或在小雨中漆上八小時的牆,下工以後,只覺得這個人已癱下來,比行軍八小時還要累得多。
今天下工後,已近黃昏。我坐在湖邊對著遠天遐想。這個環境美得像幅畫。當初造物的大匠畫這個「靜湖」時,...
作者序
有斜陽處 童元方
近人沈祖棻喜填浣溪沙,有半闋我和陳先生愛不忍釋:
三月鶯花誰作賦?一天風絮獨登樓,有斜陽處有春愁。
最初是我的哈佛同學提起的,也許是他的南方口音,我一開始就聽錯了,以為是:有斜陽處有春草,立時生出了一種淒美的意象與感覺。是春草苦戀斜陽罷?在自己正欣欣向榮的時刻,夢想留住已緩緩西沉的太陽。
我來晚了,但幸而趕上了。
‧
事情已辦完,回到家裡。床上自然是沒有人。窗外的木棉逐漸開了,橙紅的花朵映著蔚藍的天,分外好看。陳先生還在醫院裡嗎?我彷彿身在夢中,一切都不像是真的。
自此,日子一天天過去,花開得更加燦爛,卻不見有人回來;平時轉往輪椅通路的木門,再不見有人打開;輪椅長駐在窗前,也不見移動。四年來幫忙照顧陳先生的菲傭,竟自動開始把陳先生的衣物逐件裝箱,我看著受不了,說:「什麼都別動,我是個人哪!」
陳先生第二次中風後,在香港的威爾斯醫院住了三個星期,救回一命,但已半身癱瘓,不良於行。接著轉往沙田醫院復健與療養。三個月後,醫院裡的職業治療師來家裡視察,看看怎麼加建一個可供傷殘人士出入的輪椅小徑,也就是臺灣所謂的無障礙通道。我希望陳先生一如既往,可以從正門進出,就像我在美國所見的一樣:波士頓的公家機構、學校大樓、屋苑公寓,傷殘小徑都在正門,即使是老房子也可從側面迂迴而入。但在香港,限於各種條件,那小路最後仍然是從後門開出去的。又三個月,陳先生出院回家,我每星期帶他出去逛。沙田的商場設施尚算完備,可是港島那邊的大樓,寸土寸金,連輪椅小徑都省了。不但是從大廈後面入口,並且電梯一進去頗有異味,才悟出是運貨的,可能也運垃圾。然而我們沒有因此而不出門,只是一定會帶備口罩。香港這樣的國際大都會,人權的進展如此緩慢,讓弱勢的陳先生備受委屈,屢屢使我黯然神傷。而今每去一個未曾去過的地方,我都會下意識地尋覓無障礙通道。
‧
每次要出門,一星期或十天前打電話預約叫做「易達轎車」的復康車,全港一共二十部。粥少僧多,非常難訂。也還是因為二○○八年北京奧運的馬術比賽在香港舉行,馬會為有需要坐輪椅的觀眾預備的車子,奧運後捐了出來服務大眾,我們才有這福氣,不必悶在家裡坐困愁城。也因為這車,我們重遊了山頂。在開揚闊落的山景餐廳,隔著窗玻璃看微雨中的香港,遠處的高樓似一堆模糊的剪影,縱然看不真切,心情是愉快的,精神是舒暢的。餐後推著陳先生在商場散步。看著他喜歡,我買了一個小紅舞獅,回來閒掛在臥室窗前的小鈎上,陳先生抬眼便能望見,給那年的舊曆年帶來了不少喜氣。也曾去西貢吃海鮮,當晚清蒸的那條星斑是他自己指著水盆挑的。
除了邱吉爾,陳先生最喜歡愛因斯坦。去年四月,愛因斯坦的專題展覽在香港科學館開幕,展品由瑞士的伯恩歷史博物館與聯邦外交部共同提供。幾年前有過一個小型的愛因斯坦展覽,由以色列的希伯來大學協辦。比如愛氏生平,大部分以展板中英對照來介紹,有些翻譯甚至有錯。而在愛氏出生地烏爾姆看到的展覽,連他在伯恩專利局的辦公桌都搬來了,也還是以這個專題展的內容最全面,呈現的方式最精采。
許多經典照片放得很大,往往占了半堵牆。我們看見鏡式電流計、旋轉線圈儀器的實物,也看見許多重要文件的副本,比如瑞士聯邦理工大學發出的入學許可與中級文憑;看見愛氏的美國護照、瑞士護照與在柏林任教職時所使用的德國外交護照。兩個兒子漢斯.阿爾伯特與愛德華給他的信,幼嫩的字跡讓人心疼。其中最不忍目睹的是愛氏的離婚聲明,那語氣真是嚴厲。但他許諾米列娃可以得到他們在蘇黎世的三所房子,以及日後準知會得的十二萬瑞典克朗的諾貝爾獎金等等。多數的史實我們都很熟悉,但專題展籌備當局擴大了愛氏生平的語境,前半期是整個歐洲,後半期跨越大西洋到了美國。一戰、二戰當時的世界大勢均以影音材料補充說明,從奧匈帝國到日本原爆。連以愛氏為封面的《時代》雜誌亦在展場排列成行,使人歎為觀止。美中不足的是展櫃的高度沒有顧及輪椅人士的視點,輪椅既無法靠近,陳先生又不能低頭,所以有許多展品他都看不到。我的解釋只是聊勝於無。太遺憾了。
看完展覽出來必經一大廳,中間擺著一輛自行車,面對著大螢光幕上的伯恩街道。我爬上車,拚命騎,街道兩旁的屋宇不停向後倒退,越來越快。意思是看看在接近光速的速度時會怎樣,結果當然是氣喘吁吁,不但不可能再加速,反而頻頻自動減速。那車,我上去了,同行的朋友上去了,菲傭也上去了。大家都開懷大笑。陳先生雖不能親自實驗,卻非常高興。之後我們再坐復康車去附近洲際酒店的咖啡廳,為的是看看香港的天與海,再次複習麗晶酒店時代已愛上的撲天蓋地的美麗的藍。這樣的快樂真是單純,然而是幸福的。
不過陳先生最喜歡的,還是要數半島酒店的大堂咖啡座。那大家的勢派,最合他的個性。養病期間,我們去了無數次。最難忘的應是去年聖誕。不坐復康車了,而是包一輛計程車,信馬由韁,任由司機載著,隨意又隨興地專程去看夜香港的燈飾。又時而在忽然出現的一片璀璨之前,停車欣賞。黃埔從來沒有去過,那夜不經意地穿過,燈海如煙花,相遇即驚喜。又因為寵著陳先生,為看維港兩岸高樓上的燈火,我們來回兩次尖東,最後來到半島大堂的咖啡座吃晚飯。整個大廳只有一種裝飾:滿天縱橫交錯的枝椏;兩個顏色:白與金;是深雪的冬日與魅惑的森林。我們坐在靠近樂手的一角,往另一頭遙遙望過去,迷離恍惚,如在夢幻的王國。陳先生露出兒童似的笑顏,我的心也逐漸溫暖起來。
與復康車建立的關係,不可謂不親密。告別禮當日,似乎還看見一輛停在街角,司機好像也是相熟的。他是否知道陳先生再也沒有機會坐他的車了?「不在」已是事實,但我只要在路上看到救護車、復康車的蹤影,心跳加劇,腳底加速,不由自主地奔跑起來。
‧
四年中,我們回臺四次。兩次到成大赴會,兩次回臺北過年。我問陳先生「去不去?」只要他說去,我就敢千里迢迢把他搬回去。事前的準備要做足,醫生證明更不可少。而看見陳先生像小學生遠足似的那樣興奮,我還得特別求他別開心得失眠了。且總是儘早到機場,可以去貴賓室吃早餐,小籠包與餃子是他最期待的了。但從登機門上到機艙的過道就很費勁。雖然空服員都很熱心幫忙,常常三、四個一起來,以為可以在機艙口把陳先生抱下他自己的輪椅,再抱上他們的小輪椅,直上過道。小輪椅非常輕省,撐不起陳先生的重量,而七手八腳其實很危險,真怕把他給摔著了。何況還要把陳先生從小輪椅再搬上座位。我平時與菲傭已練就一套功夫,可以自己負責陳先生上下輪椅的安全。
四次旅程,屢有驚險。一次華航臨時取消班機,我們改搭港龍,新航班較原訂時間早到一個小時。港龍地勤竟然在飛機快降落時才通知接機的人。於是在小港機場等人從臺南飛奔至高雄,已經慢了,好心的司機又怕修路拖延行程而臨時改行省道,結果反而更慢,時間拉長了許多。陳先生不堪久坐,痛得他一路呻吟。
年初回臺,住進臺北的寓所。陳先生說周身疼,這是以前沒有過的。是不是旅途勞頓呢?就讓陳先生休息,以為在床上躺著會好些。但痛楚沒有減輕的意思,他已開始哼哼。我心中焦急,不可能如此等待天光,隨便披上件外套,把陳先生推過馬路去中心診所掛急診。凌晨時分,忠孝東路四段上已沒有什麼車聲與人聲,安靜得可愛。但中心診所的看護說醫院沒有神經科的人駐診,將我們轉介去仁愛醫院。而此時陳先生已痛得在低聲哀嚎了。
攔下計程車,才發現臺北道路右行和香港左行的不同與司機位置的差異對我們甚有影響,我們平時練就的本事居然不大派得上用場,陳先生幾乎要被逼到馬路中才上得了車。仁愛醫院我不認識,漆黑的臺北也是陌生的。我是多麼地惶然無助而又悽然無告。
進了急診處,見到醫生那麼投入他的工作,護士們又個個熱情洋溢,我的精神立時為之一振。照了X光,做了些檢查,是筋膜炎,即時打了一針,又開了些藥。我已經知道,臥床既久,陳先生身體的情況又差了一截,連坐起來都變得比從前困難。但不論多不舒服,陳先生憐我惜我,總是默默承受其苦。他「乖」得讓我更加心痛與不捨。
出到大街時,不知何時飄起濛濛細雨來。凌晨五時,車子已經很多,在我們面前一輛輛呼嘯而過。我站在路邊,看不出可以如何叫車,呆望了一陣,悟出是單行道,才推著陳先生轉了個直角叫了車。有幾分鐘,竟不知自己身在何處處……
‧
坐在陳先生病前常坐的角落,背對著常玉的裸女。另一面牆上從前是愛因斯坦重孫媳卡桑德拉的油畫,現在是他微笑的面容與成大為他舉辦文物特展暨論文研討會「雲淡風輕」的海報。抬頭但見門楣上,以他的簽名式為設計圖案的當日剪綵的絲帶,特別裱褙後裝框的。是熟悉的環境,看起來一切都沒變,而我卻是那麼的惆悵。
今年的六四,我終於去了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晚會。從油麻地到銅鑼灣,人又多又擠,我彷彿是跋山涉水過去的。廣場上消失的人群,他們到底有沒有存在過?抬頭望,十五的月亮又大又圓,清光悠悠,我分不清身上的淚與汗。是不是很傻?好想告訴陳先生這些事,多少年來,我們居住的城市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地方?接著是新特首上臺,國情專題教學手冊面世,我又好想告訴他最寶貴的言論自由如何開始遭打壓。如今沒有了傾訴的對象,我真正明白了什麼叫做失落與茫然。
就這樣坐著發呆。這屋子裡怎麼可以沒有陳先生呢?在全然寧謐中想他以及他說過的話。「你放不放心我?」我問。「放心」他答。這是何等的信任!正因為信任,所以放心;因為放心,所以交託;因為交託,所以無言。
‧
日前高希均先生囑我為陳先生編一本選集。我拿出陳先生的文集,一頁一頁看下去,慌亂的心逐漸安靜下來。突然間這樣的句子撲進眼簾:
有對哲學抱有希望的人,自甘磨鏡生活;
有對科學抱有希望的人,自願深鎖斗室;
有對新大陸抱有希望的,無睹海濤的驚險;
有對新世紀抱有希望的,無聞目前的嘈雜。
所以說:本為空虛無物的生命,因為各式各樣的絢麗的希望而充實起來。
這文字中有一股力量,使我不自覺涵泳其中:
藍天如洗,白日正中,我願你在此萬物甦生的初春,生命裡洋溢著光明快樂的希望。
一貫溫柔的語氣,這一刻好像是特別對我說的。〈談希望〉自然成了選集的第一篇。我的心也在此原已凋殘的春天重新開出了花朵,雖然是細碎的。
如此低廻往復,選出四十多篇散文,大致分成四類:有關於文明的思考的,有涉及價值的取捨的;有觀照人世的體悟的,有偶寄閒情的隨筆的。並沒有刻意尋求什麼主題,選集在形成的過程中自有其獨立的生命。我與陳先生於詩人之中最愛杜甫。有一次在床前跟他說話,忽然想起了「花近高樓傷客心」的詩句,卻怎麼也想不起下一句。老弱病殘的陳先生在昏黃的燈下輕輕地說:「萬方多難此登臨」。啊!這就是我一生傾心相愛而至委身相隨的陳先生了!永遠的錦心與繡口。這兩句本是雙重倒裝,在河山易色、家國動盪之秋,有此登樓,乃見花開。而登高可以望遠,遠望可以當歸,或思鄉,或懷人,自身恆是客,故心為之傷。這也反映了初到臺灣又旋即赴美的少年陳之藩的心境。老杜憂中原文化的陷落,陳氏感時代世局之荒涼。
但在時間的流淌中,從望盡天涯到欄杆拍遍,我們看到長在征途、踽踽獨行的中年陳之藩。但再看下去,幾度時空轉換,已是空山新霽,大笑朗朗的老年陳之藩。如果四類作品是四首歌,那曲名必然是:花近高樓、月色中天、晴開萬樹、溫風如酒;而羅斯科的那幅畫「天與海的窗」,就是可以安身立命的曲終收撥了。
二○一二年七月十五日於香港容氣軒
有斜陽處 童元方
近人沈祖棻喜填浣溪沙,有半闋我和陳先生愛不忍釋:
三月鶯花誰作賦?一天風絮獨登樓,有斜陽處有春愁。
最初是我的哈佛同學提起的,也許是他的南方口音,我一開始就聽錯了,以為是:有斜陽處有春草,立時生出了一種淒美的意象與感覺。是春草苦戀斜陽罷?在自己正欣欣向榮的時刻,夢想留住已緩緩西沉的太陽。
我來晚了,但幸而趕上了。
‧
事情已辦完,回到家裡。床上自然是沒有人。窗外的木棉逐漸開了,橙紅的花朵映著蔚藍的天,分外好看。陳先生還在醫院裡嗎?我彷彿身在夢中,一切都不像是真的。
自此,日子一天...
目錄
前言:有斜陽處/童元方
花近高樓
談希望
並不是悲觀
鐘聲的召喚
迷失的時代──紀念海明威之死
科學與詩
哲學與困惑──六十年代憶及金岳霖
實用呢,還是好奇呢?
理智呢,還是感情呢?
一夕與十年
風雨中談到深夜
取傷廉、與傷惠、死傷勇
月色中天
選擇就是創造
興趣與成就
成功的哲學
哲學家皇帝
明善呢,還是察理呢?
自己的路
談風格──在麻省理工學院為中國同學會演講
莫須有與想當然
進步與保守
晴開萬樹
智慧的火花
釣勝於魚
失根的蘭花
智者的旅棧
寂寞的畫廊
願天早生聖人
謝天
褒貶與恩仇
把酒論詩──悼雷寶華先生
看雲聽雨
天容海色
溫風如酒
山水與人物
週末
垂柳
河邊古屋
閒雲與亂想
山色與花光
日記一則
敲門聲
散步
疇人的寂寞──談談陳省身的詩
帕華洛帝與郝壽臣
笑與嘯
揮棒與司鼓
儒者的氣象──紀念邢慕寰教授
前言:有斜陽處/童元方
花近高樓
談希望
並不是悲觀
鐘聲的召喚
迷失的時代──紀念海明威之死
科學與詩
哲學與困惑──六十年代憶及金岳霖
實用呢,還是好奇呢?
理智呢,還是感情呢?
一夕與十年
風雨中談到深夜
取傷廉、與傷惠、死傷勇
月色中天
選擇就是創造
興趣與成就
成功的哲學
哲學家皇帝
明善呢,還是察理呢?
自己的路
談風格──在麻省理工學院為中國同學會演講
莫須有與想當然
進步與保守
晴開萬樹
智慧的火花
釣勝於魚
失根的蘭花
智者的旅棧
寂寞的畫廊
願天早生聖人
謝天
褒貶與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