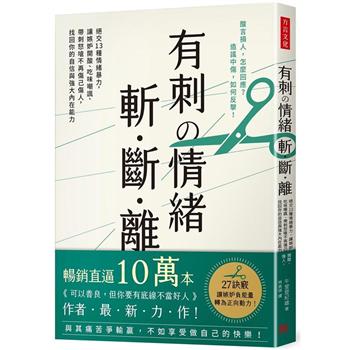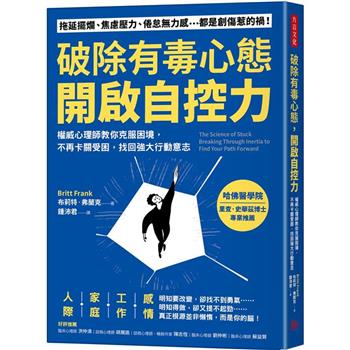有一日我從心裡看見一朵薔薇的肉體和她的血跡,此後便為她的美所撞痛。是的!薔薇是我的青春,我的肉體,我的愛,我的血……
這是詩人郭成義的創作集,集合了自十八歲以來,發表在國內各大報刊雜誌的小說、散文、情詩及札記等作品。作者說:「十八歲我迷戀薔薇,把薔薇當成自己的肉體那麼崇拜,四十歲我知道,薔薇的美顏是一種意象,是我青春的圖騰,而四十歲的我依然在心中栽植薔薇,但薔薇不是美,只因它有我的十八歲。」這本書可以說收集了作者的青春美學,裡面有瑰麗的思想與激情的愛戀,篇篇都是引人深思的作品。
作者簡介
郭成義
1950年生於基隆,現居台北,高中起即在報刊雜誌發表詩及散文、小說等作品。曾任《首都早報》言論版主編、《自由時報》撰述委員,主編《笠詩刊》、《詩人坊》,著有詩集《薔薇的血跡》、《台灣民謠的苦悶》、《國土》,評論集《從抒情趣味到反藝術思想》等。曾獲青年詩人獎、吳濁流新詩佳作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