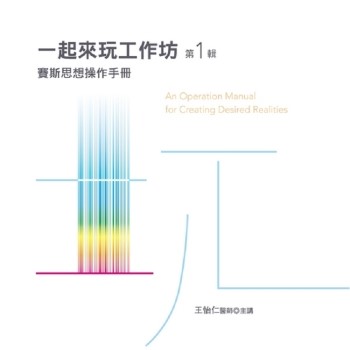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他還活著:澳華文壇掠影‧第一集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315 |
散文 |
$ 337 |
中文書 |
$ 356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396 |
小說 |
電子書 |
$ 450 |
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他還活著:澳華文壇掠影‧第一集
這本集子是認識被稱為「第三文化空間」的澳華文學的重要書寫。同時這些文章也是一流的散文、抒情小品、報告文學。
奉讀何與懷的《他還活著:澳華文壇掠影》,我愛不釋手……如果每個國家都有一些像何與懷那樣的學人/作家,我們的世界華人文化/文學將更受到應有的重視與承認。
──台北元智大學國際語文中心主任
王潤華教授
何先生的著作大多不是我們經常見到的那種學究式的研究成果……在閱讀過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何先生的文字間流淌著的溫暖的人文情懷。他善於從瞭解、理解等多層面去感受作家的內心世界,他對於有成就的作家、文化人,似乎都懷有一種敬重之情……
──重慶西南大學
蔣登科教授
與懷兄的著作是適時的。雖然他寫的只是澳華文壇的「掠影」,而不是「全貌」,但仍能使讀者感到澳華文學的深度和廣度。何況,在書末,還附有鳥瞰性的文章:〈追尋新大陸「」崛起軌跡〉,此文為深入研究澳華文學提供了一些線索,也是一種點面結合的做法。
──上海復旦大學博士生導師
吳中傑教授
在一個大多數人只關心自己的時代,在一個文人比文多的海外,將大量的時間精力花在別人的作品上面,而且敢說敢評,可能我孤陋寡聞,我想說,何博士是澳新兩地的第一人。
──新西蘭奧克蘭梅西大學
艾斯講師
何博士最能打動人的,應是他既有一種追尋式的對於自我人生的執著,還有一份給予性的熱情和仁慈。正如他的真誠表白:「薪傳和弘揚中華文化永遠是世界各地華夏子孫義不容辭、或者說自然而然的職責,也是一種宿命。」這種理想姿態、倫理精神所凝聚的情懷,讓我們更加深切地理解到在海外、在異國他邦總會有那麼多的華人依然在承傳自身文化的薪火,以及自覺地尋找文學、人生與世界的樸素的真理。
──廈門華僑大學
莊偉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