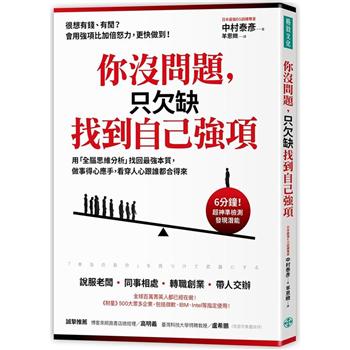作者簡介
馬森
知名戲劇家、小說家、文學評論家。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及國研所,一九六一年赴法國巴黎電影高級研究學院(IDHEC)研究電影與戲劇,巴黎大學漢學院博士班肄業;繼赴加拿大研究社會學,獲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曾先後執教於台灣師大、巴黎語言研究所、墨西哥學院、加拿大亞伯達及維多利亞大學、英國倫敦大學、香港嶺南學院、國立藝術學院、國立成功大學、南華大學、佛光大學等校。並曾一度兼任! 《聯合文學》總編輯。現已退休。 作品包括論著《馬森戲劇論集》、《當代戲劇》、《中國現代戲劇的兩度西潮》、《東方戲劇?西方戲劇》、《燦爛的星空─現當代小說的主潮》、《戲劇──造夢的藝術》、《文學的魅惑》、《台灣戲劇──從現代到後現代》等,劇作《腳色》、《我們都是金光黨》、《馬森戲劇精選集》等,小說《孤絕》、《夜遊》、《海鷗》、《巴黎的故事》、《生活在瓶中》、《M的旅程》等,散文《愛的學習》、《墨西哥憶往》、《大陸啊!我的困惑》、《追尋時!光的根》等,文化評論《文化.社會.生活》、《東西看》、《中國民主政制的前途》、《繭式文化與文化突破》等近五十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