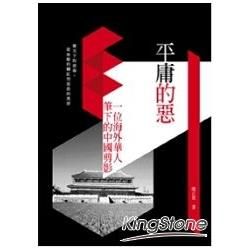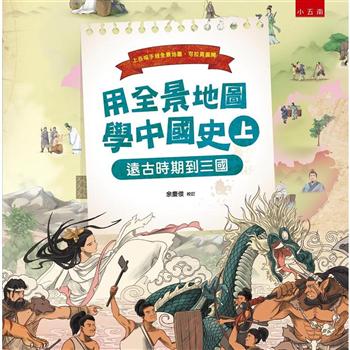夾議的事件紀實,也有當代名家名作的詮釋讀解。從遭遇國安的經歷到曝光五毛黨、新左派的行徑嘴臉,從讚譽底層作家和民運論壇到評介海外華人英文創作的最新成就,全書的每一篇文章都從所討論的特殊問題出發,對「平庸惡」這一中國症候的形成及其危害分兩條途徑展開深入的剖析。一方面對底層意識、平「狼圖騰」 熱、「愛國賊」義憤、「通三統」論述和後共產綜合症做出尖銳批判;另一方面,則從與之對抗的角度講述一批走出中國的作者如何堅持語言的自覺,伸張良知的辯護,從事其掏糞者的事業,召喚靈的復原,發出義不容辭的友聲……
作者簡介
康正果
美國耶魯大學中文教師。已出版的著作有《風騷與艷情》、《重審風月鑒》、《交織的邊緣》、《鹿夢》、《出中國記——我的反動自述》和《肉像與紙韻》等。網上文章見「博訊博客」中的「康正果文集」(www.boxun.com/hero/kangz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