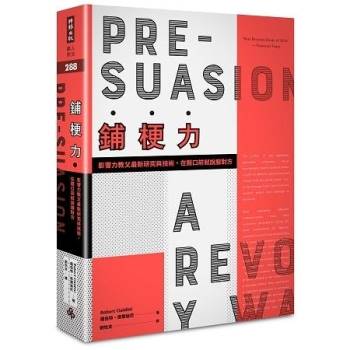這是一本有趣的、可輕鬆閱讀的「散文史論」。 作者以「閑話」筆調娓娓道來,對中國散文由文言向白話轉換作出了全新的闡釋;並從胡適、周作人、魯迅、林語堂、錢鍾書、梁實秋等人的文字中,梳理出今天「中國文章」的基因和奧秘。 「上編」從「談話風」入手,圍繞胡適、魯迅、周作人三大重鎮,闡明白話散文綿延有序的源流;「下編」涉及散文「消費性」一面,細緻剖析林語堂主編的三種半月刊(《論語》、《人間世》、《宇宙風》),探尋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及八九十年代散文創作的「中興與沒落」,對白話散文的創作規律與未來走向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正如文壇耆宿鯤西先生在序中所言:「本身不是文學史,但它的視點將來必有助於文學史的編寫。」。
作者簡介
劉緒源
作家,學者。一九五一年生。上海《文匯報》副刊「筆會」主編。對中國現代文學、中國思想史、兒童文學等領域均有研究。著有《解讀周作人》、《兒童文學的三大母題》、《文心雕虎》、《冬夜小札》、《橋畔雜記》、《見山是山 見水是水》、《翻書偶記》等。另有與哲學家李澤厚先生對話集《該中國哲學登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