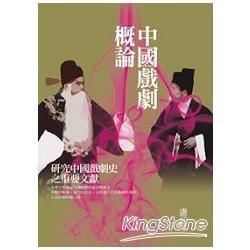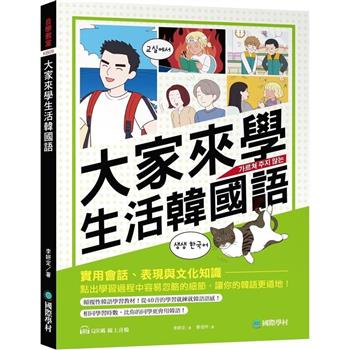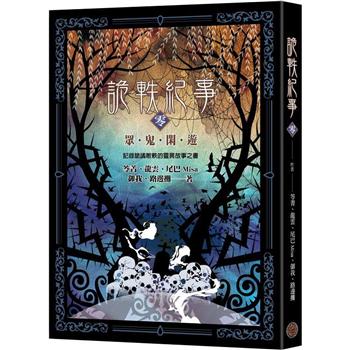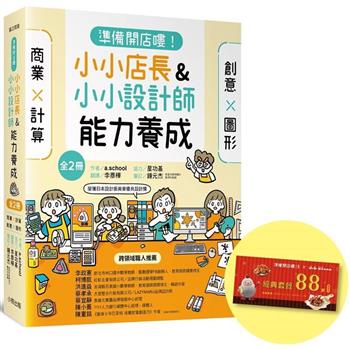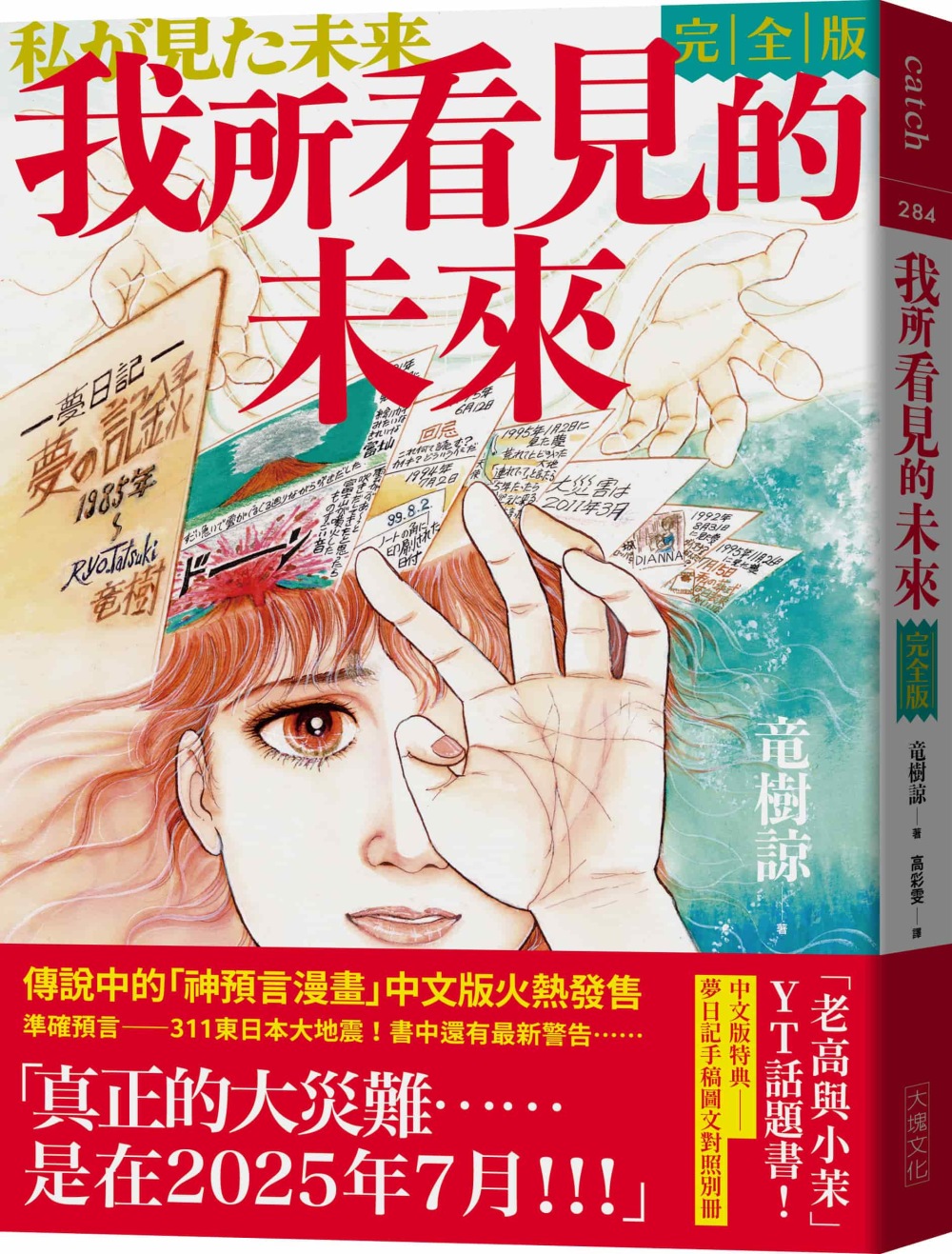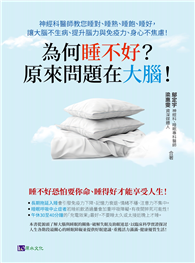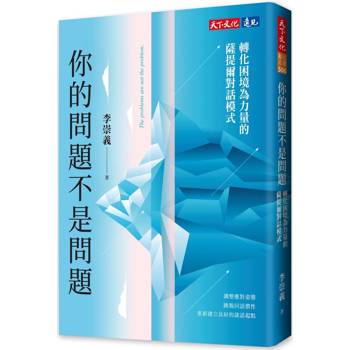本書全面闡述了中國戲劇的歷史。從上古的巫尸、唐宋前的歌舞、宋代的雜戲、元明清的雜劇與傳奇,直到後來的崑曲、皮黃和現代的話劇運動。均給予詳細的和統覽地介紹。還在一定程度上的分析了中國戲劇所受到外來的影響,以及它對世界其他文化所起的作用。書內各章及附錄有詳備的資料。
作者簡介
盧前(1905~1951)
字冀野,江蘇南京人。人稱「江南才子」,為知名詩人、散曲家、劇作家、學者。師從吳梅、王伯沆、柳詒徵、李審言、陳中凡等。畢業後曾受聘於金陵大學、河南大學、暨南大學、光華大學、四川大學、中央大學等校講授文學與戲劇課程。亦長期主編《中央日報.泱泱副刊》,並主持編纂《南京文獻》二十六冊。
主要作品包括新詩集《春雨》、《綠簾》,小說集《三弦》,古典詩集《盧冀野詩抄》,詞集《中興鼓吹》,散曲集《飲虹樂府》,劇作《飲虹五種》、《女惆悵爨三種》、《楚鳳烈傳奇》,報導文學《丁乙間四記》、《新疆見聞》,以及譯作《五葉書》、《沙恭達羅》兩種等。學術著作則有:《中國戲劇概論》、《明清戲曲史》、《論曲絕句》、《讀曲小識》、《詞曲研究》、《散曲史》等。以及《何謂文學》、《近代中國文學講話》、《八股文小史》及《酒邊集》等散論。
盧前一生熱衷於保存、傳播中國古代文化典籍。他搜集、整理、彙校並刊刻了大量的中國元明清三代的曲籍,經其整理出版者達數百種之多。其中最著名的即《飲虹簃叢書》、《飲虹簃所刻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