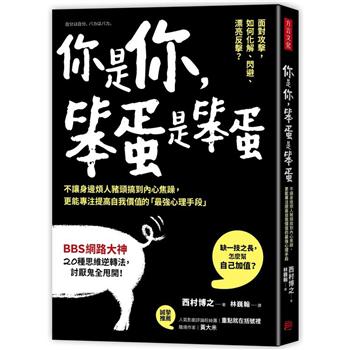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傳統起源
中國新文化運動與傳統文化之間的歷史關係如何?這是「五四」以來迭招物議、聚訟紛紜的一個問題,對它的解答不僅伴隨著緊張的史事爭辯,而且包含著激烈的文化衝突。以現代新儒家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者站在反對派的立場上,指斥新文化運動拋棄傳統、毀滅「國粹」、一意西化,造成中國傳統文化的「斷裂」;與此相左的極端反傳統主義者則以這一運動的繼承者相標榜,認定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是整體否定傳統,是「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儘管二者所持的文化立場截然相反,但否認新文化運動與傳統文化的歷史關係卻有著驚人的一致。正因為如此,他們不願意,也不可能去追溯中國新文化的傳統起源。
站在今天的歷史高度,重新審視上述觀點,我們不難發現他們的文化偏見和學術缺陷。從文化理論上言之,他們以中西之爭代古今之爭,僅僅從中西文化衝突這一歷史背景去認識和把握新文化運動,看不到外部的中西文化衝突畢竟要受到中國人文傳統自身演進的內在規律的制約,看不到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生、發展畢竟要以傳統文化作為自身的歷史基礎。從歷史材料上分析,他們以價值判斷代歷史判斷,與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實際相脫節,與倡導這一運動的領袖對這一問題的看法相抵牾。胡適晚年在回顧總結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時指出,它作為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不過是宋代以來「這個一千年當中,中國文藝復興的歷史當中,一個潮流、一部分、一個時代、一個大時代裏面的一個小時代。」胡適的看法是否精當,可容商榷。不過,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見證人,他承認這一運動是中國人文傳統自身演變的產物,這是顯而易見的。基於文化的、歷史的理由,我認為有必要就新文化運動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關係重新加以全面探討。這裏我們通過對新文化人和他們的反對派(主要是現代新儒家)與傳統文化繼承關係的粗略比較,勾勒兩者的分野之處,理清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淵源,以期澄清長久以來人們在這一研究領域積存的某些誤區。
一、清代樸學與新文化人的治學路徑
中國傳統文化在其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六個重要階段,每一階段都有其佔主導地位的學術思潮,這就是先秦之諸子學、兩漢之經學、魏晉之玄學、隋唐之佛學、宋明之理學、清代之樸學。若以中國傳統文化與新文化的歷史關係之密切而言,則首先不得不言及新文化的前身─清代樸學。曹聚仁曾謂:
在今日要讀古書,得把科舉時代的觀念拋開,把漢學、宋學的病根切斷,首先要接受清代樸學所已整理了的業績。不讀清儒所已整理了的經子古籍,尤其是諸子,那就不必讀古書。對於皖學、揚學、浙學沒有瞭解的人,就不配讀古書。
要讀古書是如此,因為樸學是開啟中國傳統學術的一把入門鑰匙。要追朔新文化運動的傳統起源,自然也得從其前身清代樸學入手。
清代樸學又稱漢學、鄭學,它以推崇漢儒樸實學風、反對宋儒空談義理著稱,與同時期繼承理學的「宋學」抗衡。其治學特徵是「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於客觀的考察」,研究內容則是從文字音韻、名物訓詁、校勘輯佚等方面從事經書古義的考證。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者蔡元培、陳獨秀、胡適、劉半農、錢玄同、魯迅、周作人、李大釗、沈尹默、劉叔雅、吳虞、易白沙諸人生長於晚清末年,在其青少年時代無不受過典型和嚴格的傳統式教育,其文化背景可謂以傳統舊學為底色。由於他們的治學興趣主要集中在文史方面,故他們大都接受了在晚清學術界仍據正統地位的樸學訓練,邃於國學。或有所師承,或有所專精,或有所撰著。以新文化人早年與清代樸學的關係而言,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茲述如下:
第一種類型以蔡元培、陳獨秀為代表,他們擁有前清進士、舉人、秀才的傳統功名,為謀求進身之階,他們自然受過系統的樸學訓練。
蔡元培先生23 歲參加浙江鄉試就中了舉人,27 歲進京補行殿試,被錄為二甲第三十四名進士,旋授為翰林院庶吉士。清廷戶部尚書翁同龢十分欣賞青年蔡元培的才華。1892 年6 月11 日,蔡元培拜見翁,翁在日記中讚歎地寫道:「新庶常來見者十餘人,內蔡元培乃庚寅貢士,年少通經,文極古藻,俊材也。」1894 年,蔡又由庶吉士升為翰林院編修。這時,不過而立之年的蔡元培已是才華卓著,「聲聞當代,朝野爭相結納」的士大夫了。蔡先生博學多聞,舉凡關於考據、詞章、醫學、算術等書均隨意拾讀,涉獵極廣。他明白交待:
我的嗜好,在考據方面,是偏於詁訓及哲理的,對於典章名物,是不大耐煩的;在詞章上,是偏於散文的,對於駢文及詩詞,是不太熱心的。
他曾想編一部《說文聲系義證》和一本《公羊春秋大義》,惜後未成書。
陳獨秀雖從小即具叛逆性格,但迫於祖父的權威,不得不隨兄鑽研經學,年僅17 歲即以第一名考取秀才,足證其舊學修養不錯。對有清一代的學術重鎮「樸學」,他亦曾下過功夫,尤擅長文字聲韻之學。1908 年周作人在東京曾目睹陳獨秀與古文經學大師章太炎討論清代漢學問題,說他「那時也是搞漢學,寫隸書的人。」1910 年陳獨秀以陳仲的筆名,撰〈說文引伸義考〉一文在《國粹學報》連載。1913年他亡命上海,閉門過冬,又著《字義類例》一書,序中自稱:「對
解釋假借有點特殊的意見」,「近代學問重在分析,此書分析字義底淵源,於中學國文教員或者有點用處。」窺察這些事例,可以看出陳獨秀早期與漢學的密切關係。
第二種類型以吳虞、周氏兄弟和錢玄同為代表。雖未具傳統功名,卻曾拜業於經學大師門下,接受了紮實的樸學訓練和正統的經學教育。
吳虞19 歲即入四川經學名門─成都遵經書院,師從經學家吳伯竭學習詩文。受其影響甚大,「側聞緒論,始知研討唐以前書。」逐步登入漢學門堂。
周氏兄弟和錢玄同東渡日本留學時,因仰慕「革命的學問家」章太炎先生的大名,前往東京《民報》社,參加他主辦的「國學講習會」。所用課本為許慎的《說文解字》,每週一課,從1928 年到1929年,持續了一年多的光景。章太炎先生上課時「一個字一個字的講下去。有的沿用舊說,有的發揮新義,乾燥的材料卻運用說來很有趣味。」章太炎對他的弟子們的影響主要是在文字方面,引導他們走上了「文字復古」的道路。魯迅曾憶及當時自己做文章,「又喜歡做怪句子和寫古字,這是受了當時的《民報》的影響。」周作人亦承認章先生的講課「實在倒還是這中國文學的知識,給予我不少的益處,是我所十分感謝。」錢玄同則乾脆進入了古文字的研究園地。著有《說文窺管》、《小學答問》(四卷)、《新出三體石經考》等書,1911 年後又追隨經學大師崔適,由古文學派轉向今文學派,對清末今文經學大師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一書頂禮膜拜。以為崔適所言「《新學偽經考》字字精確,自漢以來未有能及之者」,「實不為過」。由於章太炎在古文字研究中所占的特殊地位,周作人遲到20 世紀60 年代仍以為「章太炎先生對於中國的貢獻,還是以文字音韻學的成績為最大,超過一切之上的。」章太炎的學生,「一部分到了杭州,在沈衡山領導下做兩級師範的教員,隨後又做教育司(後改稱教育廳)的司員,一部分在北京當教員,後來匯合起來,成為各大學的中國文字學教學的源泉,至今仍有勢力。」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的圖書 |
 |
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 作者:歐陽哲生 出版社: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1-10-21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61 |
歷史 |
$ 290 |
中文書 |
$ 290 |
中國歷史 |
$ 297 |
中國歷史 |
$ 297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
View more documents from TAAZE 讀冊生活.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近代中國文化發展的一個關鍵點。論者對這一運動聚訟紛紜、爭議不斷。對它的研究由於政治、黨派等因素滲入,深深打上了意識形態的烙印。本書作者多年來從事五四運動史研究,力圖撥開意識形態的迷霧,以原始材料為依據,回到歷史現場,對五四運動史作出符合歷史原貌的客觀解釋。本書圍繞新文化運動與傳統文化的關係、蔡元培、陳獨秀、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思想主張、《新青年》編輯演變、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等問題作了深入、獨特的解釋,是五四運動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作者簡介:
歐陽哲生
1962年5月生於中國湖南省長沙市。現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之現代闡釋》、《新文化的傳統——五四人物與思想研究》、《科學與政治——丁文江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等。編有:《胡適文集》等多種文集。
章節試閱
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傳統起源
中國新文化運動與傳統文化之間的歷史關係如何?這是「五四」以來迭招物議、聚訟紛紜的一個問題,對它的解答不僅伴隨著緊張的史事爭辯,而且包含著激烈的文化衝突。以現代新儒家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者站在反對派的立場上,指斥新文化運動拋棄傳統、毀滅「國粹」、一意西化,造成中國傳統文化的「斷裂」;與此相左的極端反傳統主義者則以這一運動的繼承者相標榜,認定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是整體否定傳統,是「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儘管二者所持的文化立場截然相反,但否認新文化運動與傳統文化的歷史關係卻有著驚人...
中國新文化運動與傳統文化之間的歷史關係如何?這是「五四」以來迭招物議、聚訟紛紜的一個問題,對它的解答不僅伴隨著緊張的史事爭辯,而且包含著激烈的文化衝突。以現代新儒家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者站在反對派的立場上,指斥新文化運動拋棄傳統、毀滅「國粹」、一意西化,造成中國傳統文化的「斷裂」;與此相左的極端反傳統主義者則以這一運動的繼承者相標榜,認定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是整體否定傳統,是「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儘管二者所持的文化立場截然相反,但否認新文化運動與傳統文化的歷史關係卻有著驚人...
»看全部
目錄
自序
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傳統起源
一、清代樸學與新文化人的治學路徑
二、以「復古解放」為先導的「價值重估」
三、傳統下層文化的興起
四、新文化人實現傳統的創造性轉換中的歷史局限
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以「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儒學關係為中心
一、儒家、儒學、儒教
二、新文化運動反抗重建儒學意識形態─孔教
三、對儒家倫理的吸收與排拒
四、「五四」新文化人對儒學的學術評估
五、餘論:關於傳統與現代性的思考
蔡元培與中國現代教育體制的建立
一、對傳統教育的評估
二、「教育獨立」的理念
三、建立現代大學制...
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傳統起源
一、清代樸學與新文化人的治學路徑
二、以「復古解放」為先導的「價值重估」
三、傳統下層文化的興起
四、新文化人實現傳統的創造性轉換中的歷史局限
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以「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儒學關係為中心
一、儒家、儒學、儒教
二、新文化運動反抗重建儒學意識形態─孔教
三、對儒家倫理的吸收與排拒
四、「五四」新文化人對儒學的學術評估
五、餘論:關於傳統與現代性的思考
蔡元培與中國現代教育體制的建立
一、對傳統教育的評估
二、「教育獨立」的理念
三、建立現代大學制...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歐陽哲生
- 出版社: 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11-10-01 ISBN/ISSN:978986221825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中國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