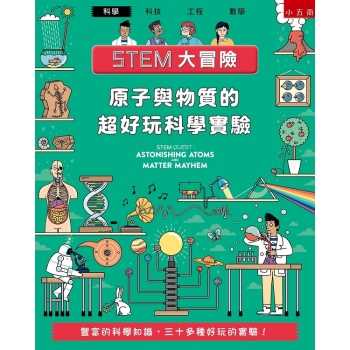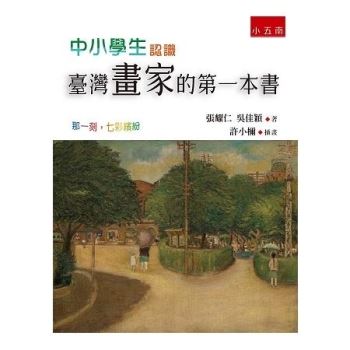文以載道、秀出天南
——悼文史大家金性堯先生
蟄居太湖,遠離申江,訊息不免閉塞。在2007年8月1日《中華讀書報》拜讀了孫仲先生《金性堯病逝,為何媒體反應冷淡》一文,驚悉高齡91歲的性堯先生已「於7月15日因病去世」。我無法回上海和金老「告別」,感到綿綿的惆悵。
性堯生前曾任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第二編輯室副主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審。單位為他舉行隆重的追悼儀式;專家學者發表情文並茂的悼念文章;家鄉定海為表彰他對文化事業的貢獻而建立「金性堯紀念室」。……他一生「秀出天南筆一枝,為人風骨稱其詩。」著作等身,尤以晚年的一本《新注唐詩三百首》紙貴洛陽,暢銷三百萬冊,譽滿海內外。實至名歸,身後並不寂寞。
我與性堯先生的文字因緣,始於「孤島」上海,「人生何所促,忽如朝露凝。」不覺已七十餘年。
他早年《邊鼓》戰上海,《橫眉》斥敵偽,以「文載道」筆名蜚聲海上文壇。他的《新文藝書話》、《期刊過眼錄》和著名的「星屋藏書」,為我從事「魯迅研究」提供了方便。
1957年,當拙著《魯迅研究資料編目》在上海文藝出版社打出清樣、即將出版面世時,他將魯迅先生寫給他的四封親筆信贈給我。學術天下公器,魯迅珍跡豈敢自秘,我特地函告許廣平先生,由許先生編入1959年北京魯迅博物館印行的《魯迅手跡和藏書目錄》第一集。為求永久性保存,我在1964年無償轉贈上海魯迅紀念館(當時由姚慶雄、浦勤修兩同志經手收下),現編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上海魯迅紀念館藏文物珍品集》第28頁。1958年左右,性堯見我對待文物資料熱愛秉公,磊落無私,頗為嘉許。便把1939年他創議並在中共地下黨支持下編輯《魯迅風》的全部文字檔案材料,贈給我供進一步研究。這些材料包括《魯迅風》前後十九期的校樣外,更有許廣平、周建人、陳望道、鄭振鐸、王任叔、孔另境、王統照、魏金枝、柯靈、唐弢、周木齋、石靈、巴金、李健吾、阿英、何家槐、周鋼鳴、蒯斯曛、列車(陸象賢)、金祖同、衛聚賢、趙景深、謝六逸、周黎庵、陶亢德、徐訏、周楞伽、邱韻鐸、錢今昔、吳調公、朱雯、羅洪、黃嘉音、旅岡、白曙、海岑、陳靈犀、陸小洛、胡山源等給性堯的親筆信二百六十多件。當時曾經上海文學研究所副所長葉以群先生和柯靈先生過目,他們要我考證、研究後寫出相應的學術論文。上海《學術月刊》編輯黃迎暑同志專程來舍間商議發表問題。唐弢獲悉後向我借閱這批材料。我在樹民中學求學時,唐弢是樹民中學的國文教員,礙於「師生情面」,我略作摘記後把這些材料全部借給了唐弢。
後來《學術月刊》催稿甚殷,我便向唐弢索討。他一再推諉,只還回半數左右……。
1959年黨內發動「反右傾」運動,由於王任叔在1956年寫過一篇《論人情》,文藝界便把他作為宣揚「人道主義」、「人性論」的「修正主義」典型開展批判。姚文元以巴人為靶子,在上海發表長文《批判文學上的修正主義思潮》,強詞奪理、無限上綱,給巴人以致命的攻擊。同年9月,唐弢調往北京,我去送行,留我便餐。臨別時他對我說:「巴人那些信幫你處理了,否則,你如據以寫文章吹捧他在《魯迅風》的功績,要犯大錯誤了……。」當時,我還對他表示感謝。後來柯慶施提出只准寫「十三年」,「左」風凜冽,我就把自己長期收集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有關圖書和材料轉移到家鄉洞庭東山老屋深藏密鎖起來。家慈病故,長女育群回鄉插隊,為我守護這批深藏的材料。因此,躲過了「文革」浩劫,轉移至家鄉的圖書和資料,幸得無恙。
龔定庵詩「文字緣同骨肉深」,我銘記性堯的深情厚誼,首先是他贈我的這批書信。「補記交情為紀公,厚重虛懷見古風。」我是永難忘懷的。他在「文革」中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家破人亡,慘不忍聞。我去他北京路葆壬裡老家的「斗室」中拜望他,他雙耳失聰,靠了筆述,已經無從暢談往事了。欣逢盛世,將我長期保存的殘簡公諸於眾。惜當年曾窺全豹的以群、柯靈兩位前輩墓木已拱,然即此叢殘亦彌足珍貴,《魯迅風》裡看性堯,足以見他「厚重虛懷」的「古風」於萬一。他在《古今》創刊近一年後是奉袁殊之命投稿的。性堯在1946年曾對我說:「袁殊是三十年代左翼作家。是阿英介紹相識的。上海淪陷後,袁殊主動找到性堯。性堯猜測,他可能姓『共』,也可能姓『國』。無論如何,袁殊在政治背景上總要比周黎庵『吃香』。所以,袁殊一『開口』,性堯就應允了。現在(1946年)國民黨以『漢奸』罪名通緝袁殊,袁殊去了蘇北共產黨的地區,我原來對他『將信將疑』,現在確信他姓『共』無疑了。為了取得朱樸的信任,只能在文章中捧捧朱樸……。」性堯除了向朱樸「投名狀」的兩文外,其他都是談風土、談掌故、談人情、懷舊友……。
1945年10月,連別有用心者在《文化漢奸罪惡史》中,也不得不承認:「幾年以來,文載道雖未喊過什麼『大東亞』與『和平』,可是對周作人卻異常崇拜」,「他並沒有大紅而特紅,也沒有做官,只拿到細微的稿費,在『太平書局』出版了一本文集《風土小記》。」(見該小冊子第33~34頁)——由此可知,這是有人唆使門人對金性堯的「惡搞」(kuso)。可是,從此卻成為性堯的「白壁之玷」。但他既未參加偽組織,更無涉筆「大東亞」……,當年連國民黨政府在「懲治漢奸」時因抓不到他的把柄,未動他的毫髮。建國以後,組織上實事求是地對待他的這段歷史。追悼會上,組織上在《悼詞》中肯定了性堯的一生。如今,建設「和諧」社會之際,在性堯逝世以後,個別人不顧性堯與桂芳夫妻情篤、白頭偕老的事實,捏造謠言,無中生有,污辱亡者夫婦為此而「離婚」云云……,此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死者已焉,生者何堪?!古人云「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個別人的「惡搞」(kuso)是無損於性堯的日月之明的。我作為歷史的見證人,有責任提供事實真相,以見歷史的本來面目。並作為對亡友逝世「周年祭」的一瓣心香。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行雲流水記往(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70 |
中文書 |
$ 284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317 |
史學理論 |
$ 324 |
學者/科學家 |
$ 324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行雲流水記往(下)
本書可謂是沈鵬年先生的回憶錄,記述了沈鵬年的傳奇人生及其年輕時從事現代史和現代文學探索的足跡。本書內容中的大量史料,收集文人著作存稿、手跡、照片、通信等圖文並茂,其中不泛精闢見解,珍貴異常,或可當信史來讀。
作者簡介:
沈鵬年
中國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曾任上海電影集團幹部,研究電影及現代文學史料達二十餘年。
章節試閱
文以載道、秀出天南
——悼文史大家金性堯先生
蟄居太湖,遠離申江,訊息不免閉塞。在2007年8月1日《中華讀書報》拜讀了孫仲先生《金性堯病逝,為何媒體反應冷淡》一文,驚悉高齡91歲的性堯先生已「於7月15日因病去世」。我無法回上海和金老「告別」,感到綿綿的惆悵。
性堯生前曾任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第二編輯室副主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審。單位為他舉行隆重的追悼儀式;專家學者發表情文並茂的悼念文章;家鄉定海為表彰他對文化事業的貢獻而建立「金性堯紀念室」。……他一生「秀出天南筆一枝,為人風骨稱其詩。」著作等身,尤以晚年...
——悼文史大家金性堯先生
蟄居太湖,遠離申江,訊息不免閉塞。在2007年8月1日《中華讀書報》拜讀了孫仲先生《金性堯病逝,為何媒體反應冷淡》一文,驚悉高齡91歲的性堯先生已「於7月15日因病去世」。我無法回上海和金老「告別」,感到綿綿的惆悵。
性堯生前曾任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第二編輯室副主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審。單位為他舉行隆重的追悼儀式;專家學者發表情文並茂的悼念文章;家鄉定海為表彰他對文化事業的貢獻而建立「金性堯紀念室」。……他一生「秀出天南筆一枝,為人風骨稱其詩。」著作等身,尤以晚年...
»看全部
作者序
序
溯自明清之際,正當西洋文藝復興時期,中國傳統文化同時亦發生丕變。由宋明理學而轉為義理、詞章、考證三大流派。降至同(治)光(緒)兩代而至末造,不但對自然科技之學黯然失色,即如清初學風亦淺淡蛻化,唯記聞之學聊備風規。迨至清末民初,即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之間,新聞文藝發展,即如記聞舊學亦形色有異,何況餘者。由此遞變,經民初五四運動逐漸而至於文化大革命期間,惶惶不可終日,有能抱殘守闕,蟄居浩劫之中而依然耽嗜書史,沉潛於記聞者,已無多子。但吳會之間,由來固多埋光抱道之秀士,如古吳東山沈鵬年,即足為例。今...
溯自明清之際,正當西洋文藝復興時期,中國傳統文化同時亦發生丕變。由宋明理學而轉為義理、詞章、考證三大流派。降至同(治)光(緒)兩代而至末造,不但對自然科技之學黯然失色,即如清初學風亦淺淡蛻化,唯記聞之學聊備風規。迨至清末民初,即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之間,新聞文藝發展,即如記聞舊學亦形色有異,何況餘者。由此遞變,經民初五四運動逐漸而至於文化大革命期間,惶惶不可終日,有能抱殘守闕,蟄居浩劫之中而依然耽嗜書史,沉潛於記聞者,已無多子。但吳會之間,由來固多埋光抱道之秀士,如古吳東山沈鵬年,即足為例。今...
»看全部
目錄
目錄
探源篇
文以載道、秀出天南——悼文史大家金性堯
《魯迅風》裡看性堯
從王任叔離滬前的信再看性堯
從投稿《古今》論性堯「白璧之玷」
性堯好友《郭沫若歸國記》作者金祖同
金性堯與阿英:「文字淵源第一人」
——從六封信看他們的深情厚誼
「抗戰時不能忘卻的柯靈」
——柯靈發表性堯四十多篇文章、給他十一封信
性堯「最誠摯坦白的友人」家槐
——《憶家槐》諱言的「不愉快舊事」
金性堯與中華女子職業中學
——蒯斯曛給性堯的四封信
「年青的期待」——劉雪庵的《何日君再來》
——提供一件歷史資料
《十日談》...
探源篇
文以載道、秀出天南——悼文史大家金性堯
《魯迅風》裡看性堯
從王任叔離滬前的信再看性堯
從投稿《古今》論性堯「白璧之玷」
性堯好友《郭沫若歸國記》作者金祖同
金性堯與阿英:「文字淵源第一人」
——從六封信看他們的深情厚誼
「抗戰時不能忘卻的柯靈」
——柯靈發表性堯四十多篇文章、給他十一封信
性堯「最誠摯坦白的友人」家槐
——《憶家槐》諱言的「不愉快舊事」
金性堯與中華女子職業中學
——蒯斯曛給性堯的四封信
「年青的期待」——劉雪庵的《何日君再來》
——提供一件歷史資料
《十日談》...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沈鵬年
- 出版社: 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11-12-01 ISBN/ISSN:978986221838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史學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