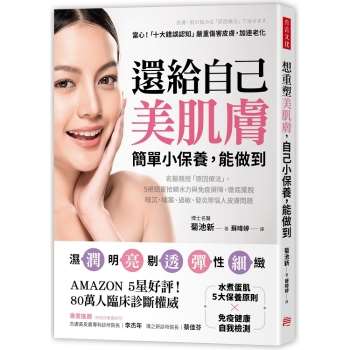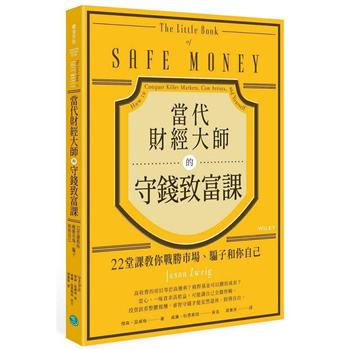序《蛙戲》
在我的劇作中,《蛙戲》也是演出較多的一齣,因為是喜劇,人多,熱鬧。但是喜劇難寫,似乎比悲劇、正劇、通俗劇更難以為工,因為叫人看了好笑而又有意義不是件簡單的事。因此出過莎士比亞的英國,在戲劇獎外特別準備一個喜劇獎,頒給每年出色的新喜劇,以示鼓勵。法國的喜劇作家莫里哀的盛名遠超過其他法國作家,經數百年至今聲譽不墜。其實不但是英、法兩國人偏愛喜劇,其他國家的人,包括中國的觀眾在內,都愛看喜劇。我國傳統戲曲中喜劇的成分就很強,逗笑的丑幾乎穿插在所有的劇作中,而經常都是大團圓的結尾,用在通俗劇,也用在喜劇。但通俗劇不算喜劇,因其強調悲歡離合,先讓觀眾哭,再讓觀眾笑。喜劇不需要悲離的部分,也不需要引出觀眾的悲情,上乘的喜劇使觀者會心一笑即可;如引得觀眾不停地哈哈大笑,那就是鬧劇了。
喜劇與悲劇的區別,如果根據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說法,一是寫市井小民,一是寫達官貴人。所以對悲劇,觀眾是以嚴肅的心情仰望的,對喜劇則可放鬆神經向下俯視。俯視的好處就是覺得劇中的人物不如自己,智慧不如,能力不如,地位不如,運氣也不如,才可盡情地嘲笑他們,覺得自己不像劇中人那麼愚蠢、那麼倒楣,進而獲得某種滿足。此外,喜劇也會給予觀眾某種審美的感受,卻無法像悲劇似地帶給觀眾情緒上的洗滌或昇華,理論上似乎比起悲劇來矮了一截,但是自古喜劇就與悲劇分庭抗禮,因其可以叫觀眾開心,忘掉平時心中的鬱悶或悲戚,那怕是暫時的,也很值的。在現實的社會中,逐日面對貪官污吏、黑心商人、強盜騙徒,流氓神棍,如無喜劇的調侃中和,心肺都會氣炸了,所以人們認為看喜劇有益身心健康,良有以也。而況有意義的喜劇,在觀者的自我滿足外也會連帶學到一些教訓,或獲得某種啟示,使觀眾恍然領悟到一些做人處世的道理。
喜劇一定要大團圓的結尾嗎?傳統的喜劇的確如此,但到了荒謬劇出現,就不盡然了。荒謬劇常為人稱作「悲喜劇」或「喜悲劇」,但它不是通俗劇,它揭示人生的無意義、無道理可言說,叫人看了先是覺得滑稽可笑,骨子裡卻很可悲。人生處境正是如此,熱熱鬧鬧的一輩子,最後總不免悲涼地走入永恆的黑暗中。我寫《蛙戲》時就沒用大團圓式的結尾,而是眾蛙都一個個地死去了;還不是一般的死,而是心甘情願地自我犧牲,包括自命先知的天才的蛙。這種荒謬的結尾,觀眾怎肯接受呢?只有一種情形,觀眾才不會覺得莫名其妙,那就是使他們聯想到我們人間其實也發生過類似的荒謬情境。德國的納粹時代、俄國的史達林時代、中國的毛澤東時代,不都是曾經先宣稱一種崇高的人生理想,鼓動人們奮發追求的情緒,然後再豎立一批假想的敵人,奮勇地向敵人攻擊,最後,把自己也陪進去?在當日那種環境中,其實大家都活得痛苦不堪,沒人真正愉快得起來,但卻沒人敢挺身反抗,就像中了魔咒一般。不同的是,人間鼓吹理想的政黨領袖或革命舵手,外表神聖得像神祇一樣不可侵犯,內在則多的是欺妄懦怯之輩,只鼓勵別人去奉獻犧牲,自己卻隔岸觀火,坐享其成。較之人類,群蛙反倒是更為誠實、悲壯的。
我並不企圖宣揚人間的愛,如果愛存於人的本性中,又何須去宣揚呢?但相信對他人殘酷,最後等於對自己殘酷,這確是經驗證明過的。世間常有眾人敬仰的先知或偉人,用美妙的言詞包裝起殘酷的內涵,就是我們時常聽聞的所謂糖衣毒藥一類,在中毒以前總難辨認出糖衣內部的真實。所以《蛙戲》除了喜鬧之外,是有些含意了,或者說是具有某種諷刺或隱喻,也因此使這齣戲不算是一齣荒謬劇(因為荒謬劇並不屑於去諷刺人間的種種),而只能說是一齣喜悲劇。
有評論者說我喜愛採用寓言的形式,讓動物替代人類搬演人間的故事。不錯,我的戲中出現過獅子、大蟒、蒼蠅、蚊子、野鵓鴿,還有《蛙戲》中的青蛙。不但是劇作,我在《北京的故事》中也寫了不少動物。我喜歡動物,幼年時飼養過很多種動物,貓、狗、雞之類的不用說了,也養過鴿子、黃雀、黃鼠狼。後者因為是野物,給家人偷偷地丟棄了。在寂寞的童年時代,動物曾是我的玩伴。西方文學中的動物多出現在寓言和兒童故事中,以視覺、聽覺為訴求的舞劇、歌劇中也會出現。可是在中國的民間信仰,認為動物,甚至植物、礦物,都可與人性相通,因此自古就有志怪一類的作品,從先秦、六朝、唐、宋,一直到清代蒲松齡的《聊齋誌異》,綿延不絕。動物活在人的世界,人也活在動物的世界;動物有時表現得比人更有人性,人有時表現得比動物更像動物。現代的我們,承續著東西兩方面的傳統,既可以藉助物性相通的信仰,又可採取寓言的形式,使作品增多一份趣味和層次,但並非專寫給兒童看的文學。
這齣戲出版後,最早演出的不在國內,而是在澳洲的坎陪拉大學(University of Canberra)。那時老友李克曼(Pierre Ryckmans, 筆名Simon Leys)教授正在坎陪拉大學教授中文,我寄給他一本剛出版的劇作集,不想他馬上就指導他的學生演出了《蛙戲》。他為什麼選中《蛙戲》而非其他?我沒問過他這個問題,也許因為此戲人物多,可使多數的學生參與演出吧?以後《蛙戲》也成為在台灣學院劇社常演的劇目。
演出《蛙戲》時到底演員應該如何裝扮才更像青蛙?畫臉譜、帶面具,還是素面?我提議畫臉譜或帶面具,但並非硬性規定,素面也可,全看導演處理的方式。提倡「貧窮劇場」的葛羅托夫斯基(Jerzy Grotowski)就主張理想的演員不用化妝,靠演技使觀者認同所扮演的人物的性別、年齡、身態和心理。但這對演員的要求未免過高了,使訓練不足的演員難以企及。至於《蛙戲》中人物的性別,本來八隻蛙中有六隻雄性,只有兩隻雌性,但如今的劇團中時常女多於男,所以聰明的蛙和愚笨的蛙也常改由女性扮演,成為雌雄各半了。
《蛙戲》的舞台設計,一個暮秋時分的大池塘,「敗葉滿地,但天氣晴和,陽光斜斜地穿過樹叢,灑落在地上。」這樣的場景,如果經費充裕,有很大創意的空間,容易產生豐富的美感效果。至於配樂,在話劇版中已有所提示,到了歌舞劇版,那更是譜曲者的責任了。
二○○二年「台南人劇團」想搬演一齣我的戲,因為他們的演員多數是在學的大學生,又想到他們曾經演出過音樂劇,且有多年訓練演員的經驗,我就提議不如演出《蛙戲》,不是話劇的版本,我可以另外新寫一個歌舞劇的版本以供演出。為什麼有此想法?起因於一九八七年我離開英國前,倫敦正在上演歌舞劇《貓》,非常轟動,當時沒買到戲票,所以未及觀賞就離開了,頗引以為憾。心想貓可以熱熱鬧鬧地搬上舞台,青蛙為何不可?為了不致受到《貓》劇的影響,在完成《蛙戲》的歌舞劇版本前故意不看《貓》劇的任何資料,雖然《蛙戲》同用歌舞,結果卻是與《貓》劇有絕不相同的意涵和場面。
現在《蛙戲》有兩個文本,一個是原來的話劇本,另一個是改寫的歌舞劇本,人物和情節大致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劇詞和場面。另外,在歌舞劇版最後加了個後設性的尾巴,減少了可悲的氣氛,把喜悲劇變成純喜劇,算是強調了娛樂的一面。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加以比較。
歌舞劇《蛙戲》首演在成功大學成功廳,繼在台南市文化中心演藝廳,然後又在南台灣的高雄等地巡迴演出多場。經過半年的集訓,年輕演員的歌與舞,居然都有模有樣,雖然比不上百老匯的歌舞明星,但在業餘的劇團中也演出了難能可貴的成績。我覺得這是一齣頗具潛力的戲,如果有職業的歌舞演員擔綱,加上一兩首動聽的歌曲,幾場可觀的舞蹈,會有更好的舞台效果。
現在秀威資訊科技公司正在出版我的文集,包括劇作在內,我特別把《花與劍》和《蛙戲》兩劇從《腳色》中分離出來另外編輯,主要是為了方便對這兩齣戲有興趣的讀者和劇團,可以單獨獲取這兩齣戲比較詳細的資料,這是在《腳色》劇集中無法插入的。
作者序於二○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維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