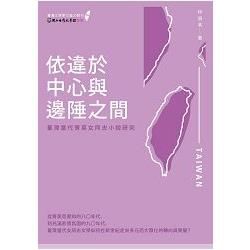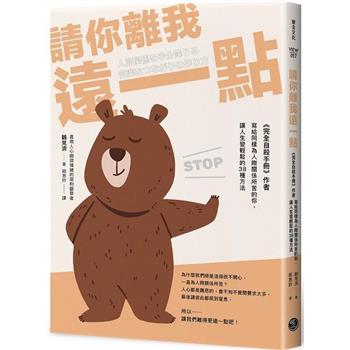從菁英而壓抑的八○年代,
到充滿悲情氛圍的九○年代,
臺灣當代女同志文學如何在新世紀走向多元而大眾化的轉向與質變?
臺灣的同志運動,或是學院裡的同志論述,具有高學歷的菁英族群向來是主要的引導力量;而相較於男同志,女同志顯然更流連徘迴於菁英校園之中。然而,菁英女同志角色雖居於較為優越的文化位階,卻似有其無法跨越的邊緣異境,乃至菁英女同志文本長年以來充滿無所不在的憂鬱氣質與死亡陰影。
本書探討臺灣當代女同志因性別認同與文化階層的差異,所形成的菁英/邊緣位置游移現象。以九○年代劇烈變動的氛圍中,十分具有「典型」菁英女同志意義的已故作家邱妙津的小說為主,並以其他同時期的女同志文本,例如林黛嫚、張亦絢、杜修蘭、曹麗娟等其他作家的作品為輔,論述女同志小說中的菁英氣質,及菁英女同志不同於社會學研究中所關注的T吧階級女同志的既中心又邊緣的性/別位置與文化位階,並思索這種依違於邊緣與中心的文化位階,其中所呈顯出來的菁英認同與邊緣想像,如何延續並深化性/別位階與愛慾身體的複雜糾結。
本書特色
★ 從純情童女到愛欲解放,臺灣女同志文學將何去何從?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依違於中心與邊陲之間:臺灣當代菁英女同志小說研究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194 |
中文書 |
$ 194 |
華文文學研究 |
$ 198 |
文學 |
$ 205 |
同志文學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依違於中心與邊陲之間:臺灣當代菁英女同志小說研究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林佩苓
臺南市人,臺南女中、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畢業,現為臺南一中國文教師。曾獲師大紅樓文學獎、府城文學獎、臺大蘇維熊獎學金,並曾發表單篇論文於《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當代詩學》等期刊。
林佩苓
臺南市人,臺南女中、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畢業,現為臺南一中國文教師。曾獲師大紅樓文學獎、府城文學獎、臺大蘇維熊獎學金,並曾發表單篇論文於《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當代詩學》等期刊。
目錄
館長序/翁誌聰
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圍
二、研究方法
第三節 文獻回顧
一、性/別論述
二、臺灣同志空間論述
三、臺灣當代同志文學與文化研究
第四節 論文架構與章節安排
第二章 純情「童」女:八○年代前後臺灣女性小說中的菁英認同與女女情愛
第一節 婦運中的菁英認同與女性文學場域
一、 婦運中的新女性:以「秀異」的社會位階改寫女性地位
二、文學院式婦運中的女性文學場域
三、女校教育中的菁英認同與性/別意識
第二節 八○年代女校小說中的女女情愛書寫
一、女性意識與菁英認同
二、菁英女校情愛關係中的「婆」敘事主體
三、菁英認同脈絡下的純情「童女」
小 結
第三章 經典「同」女:九○年代女同志小說中的文化菁英位階與性/別邊緣想像
第一節 轉向九○年代:分離主義敘事下的女女愛慾書寫
第二節 經典「同」女:以「拉子」為中心的菁英女同志塑型
一、 菁英「拉子」:九○年代女同志小說中的優秀女同志
二、中心或是邊緣?:菁英女同志迂迴的性/別位階
三、 庸俗群眾或是菁英同志?:游移的性別位階與社會階序
第三節 依違於中心與邊陲之間:菁英女同志的邊緣空間書寫
一、漂移的房間:「拉子」空間書寫
二、性/別「違建」的邊緣空間
三、在「異」鄉與異「國」之外:菁英位置與邊緣想像
第四節 「荒謬的牆」:菁英女同志與親密關係的糾纏
一、「荒謬的牆」:糾結對立的家庭關係
二、「柏拉圖」式的菁英女同志愛慾
小 結
第四章 同女漫遊:兩千年網路世代中女同志文學的愛慾書寫與大眾化轉折
第一節 現身與超越?:菁英女同志文學中的積極現身與運動書寫
一、女校情愛的指認與回返
二、菁英女同志愛慾與女同志圈書寫
第二節 延續或轉向?:網路世代後的新世代女同志文學與文化
一、從刊物集結、社團運動到網路交友
二、 拉子離開以後:飄移網路(網絡)中的憂鬱女同志系譜
三、 告別憂傷:網路世代後女同志文學與文化的大眾化轉向
小 結
第五章 結論
附錄:參考書目
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圍
二、研究方法
第三節 文獻回顧
一、性/別論述
二、臺灣同志空間論述
三、臺灣當代同志文學與文化研究
第四節 論文架構與章節安排
第二章 純情「童」女:八○年代前後臺灣女性小說中的菁英認同與女女情愛
第一節 婦運中的菁英認同與女性文學場域
一、 婦運中的新女性:以「秀異」的社會位階改寫女性地位
二、文學院式婦運中的女性文學場域
三、女校教育中的菁英認同與性/別意識
第二節 八○年代女校小說中的女女情愛書寫
一、女性意識與菁英認同
二、菁英女校情愛關係中的「婆」敘事主體
三、菁英認同脈絡下的純情「童女」
小 結
第三章 經典「同」女:九○年代女同志小說中的文化菁英位階與性/別邊緣想像
第一節 轉向九○年代:分離主義敘事下的女女愛慾書寫
第二節 經典「同」女:以「拉子」為中心的菁英女同志塑型
一、 菁英「拉子」:九○年代女同志小說中的優秀女同志
二、中心或是邊緣?:菁英女同志迂迴的性/別位階
三、 庸俗群眾或是菁英同志?:游移的性別位階與社會階序
第三節 依違於中心與邊陲之間:菁英女同志的邊緣空間書寫
一、漂移的房間:「拉子」空間書寫
二、性/別「違建」的邊緣空間
三、在「異」鄉與異「國」之外:菁英位置與邊緣想像
第四節 「荒謬的牆」:菁英女同志與親密關係的糾纏
一、「荒謬的牆」:糾結對立的家庭關係
二、「柏拉圖」式的菁英女同志愛慾
小 結
第四章 同女漫遊:兩千年網路世代中女同志文學的愛慾書寫與大眾化轉折
第一節 現身與超越?:菁英女同志文學中的積極現身與運動書寫
一、女校情愛的指認與回返
二、菁英女同志愛慾與女同志圈書寫
第二節 延續或轉向?:網路世代後的新世代女同志文學與文化
一、從刊物集結、社團運動到網路交友
二、 拉子離開以後:飄移網路(網絡)中的憂鬱女同志系譜
三、 告別憂傷:網路世代後女同志文學與文化的大眾化轉向
小 結
第五章 結論
附錄:參考書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