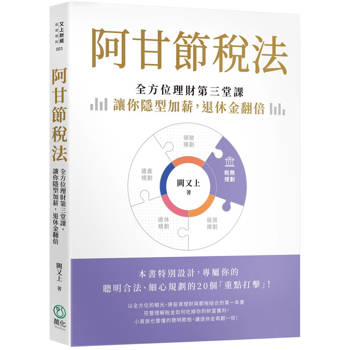此書收錄何與懷博士談論多位華文女作家及其作品的文章。書中提及的作家詩人大多並非文學科班出身,如張鳴真是悉尼大學傳媒學碩士,曾凡是北京清華大學建築系的高材生,胡仄佳年輕時學畫學美術設計;現在她們大多更不專事文學寫作不以此爲生,如梁小萍是著名書法家,郁風生前是著名畫家,劉虹是報紙編輯,孟芳竹從事電臺主持之類的文化工作,而作爲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的中文老師,張典則在大學任教幾十年直到現在退休。其中有幾位也已經享譽中國大陸、臺灣乃至世界華文文壇,如陳若曦、戴厚英、遲子建等。 這些女作家從年齡、國籍、身世背景以及文學成就、知名度都各不相同。然,誠如作者所言:「本書篇什的組成並非預先設計。正因爲不是預先有意而爲,其「隨意性」也許更能說明問題,更能反映出當今世界華文文學五光十色的多元性。當然,這還只是其中極少量女作者的掠影。」
作者簡介:
何與懷 一九四一年出生,廣州市人。畢業於天津南開大學外文系。紐西蘭奧克蘭大學博士。現定居澳大利亞悉尼。除一般寫作外,主要研究興趣是當代中國問題和華文文學。著作多種多樣,例如有涉及英美文學的《英美名詩欣賞》,有用英文寫出的詞典《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文化用語大典》和學術論著《緊縮與放鬆的循環: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九年間中國大陸文學政治事件研究》,有評論、隨筆、報告文學之類的選集《精神難民的掙扎與進取》、《北望長天》、《他還活著》、《海這邊,海那邊》,以及主編《依舊聽風聽雨眠》、《丹心一片付詩聲》和《最後一課》等。各種文章散見世界各地刊物、報紙和網站。 現為澳大利亞悉尼華文作家協會榮譽會長、澳大利亞中華文化促進會副會長、澳大利亞南溟出版基金評審、澳大利亞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校友聯誼會名譽會長、澳大利亞新州華文作家協會顧問、澳大利亞南瀛出版基金顧問、澳洲《酒井園》詩社顧問、悉尼詩詞協會顧問、《澳洲新報‧澳華新文苑》主編、《澳華文學網》榮譽總編輯,以及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召集人。
章節試閱
第一節 李顒悔過自新說
清代學術,導源於宋學。李顒、顏元是清初北方學者的代表。李顒是陝西人,顏元是河北人。李顒倡悔過自新說,實際上就是改進論。改進當然包括改正,只是切實功夫。時人以其卑之無甚高論而輕忽之,李顒提醒說,天地、萬物都是日新的,大哉自新之義。人文能走多遠,就看其改進如何。這一點,已經由過去的歷史顯示、說明瞭。所謂滿街能悔過自新,安見滿街之不可為聖人?虛譚性命,不過是英雄欺人語。關中之儒,橫渠以後,李子而已。「同志
者,雖無過可悔,亦不妨更勉之!」(《悔過自新說》小引)
李顒說:「人也者」,「即得天地之理以為性。此性之量,本與天地同其大。」(《悔過自新說》)但是人不斷被周圍世界剝蝕,「甚至雖具人形,而其所為有不遠於禽獸者。」(《悔過自新說》)所以說君子貴踐形。雖然,人之本性固常在也。人們不能夠改進,停頓甚且倒退,都是因為自棄。「殊不知君子小人、人類禽獸之分,只在一轉念間耳。」(《悔過自新說》)人類是由禽獸不斷改進來的。改進則「一切人服我」,此理常人未之思也。李顒認為,古今大儒,或以主敬窮理、先立乎大、心之精神為聖、自然、復性、致良知、
隨處體認、正修、知止、明德標宗,不一而述;但是,要之都不出「悔過自新」四字。過去只是因為不曾揭出此四字,所以徒費許多辭說。如今不若直提悔過自新四字為說,庶當下便有依據,所謂點鐵成金是也。這是最「直捷簡易」的門路。
在李顒看來,古人留下的經典,都是傳之後人以救萬世之病的。由此亦可見,當明、清之際,所謂天崩地解,士人的思想與理解,往往很自然的容易導入病理學之思維,而不是生理學的。這是由憂患之世促成的,毫不奇怪,悔過自新說正是如此。李顒謂,此說可包舉、統攝萬事。如:
天下─天子能悔過自新,則君極建而天下以之平;
國─諸侯能悔過自新,則侯度貞而國以之治;
家─大夫能悔過自新,則臣道立而家以之齊;
身─士庶人能悔過自新,則德業日隆而身以之修。
所以李顒說,「苟真實有志做人,」須從此(悔過自新)下刀。李顒之所以提出此說,還是為了人們能夠安身立命。「故敢揭之以公同志。」(《悔過自新說》)可不要做那種「惡貧女之布而甘自凍」的事啊!天地最愛修德的人,悔過自新,可以祈天永命。「新與不新,」「全在自己策勵。」性、德,「我固有之也,」(《悔過自新說》)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李顒的改進思想,畢竟是理學時代的痕跡,所以這個改進只是向著「至善」這一上限無限趨近(這使人想到了西學的分析、綜合之辯)。李顒界定說:「新者,復其故之謂也。辟如日之在天,夕而沉,朝而升,光體不增不損,今無異昨,故能常新。若於本體之外,欲有所增加以為新,是喜新好異者之為,而非聖人之所謂新矣。」(《悔過自新說》)
李顒講的悔過自新,具體操作上更像是心理檢查,而且是道德心理檢查,所謂苟有一念未純於理,即是過,即當悔而去之。從這裏來看,說李顒是「格正」思想,也許比說改進思想更貼切、恰當。必先檢身過,次檢心過,念純於理,即是念理合一、道德合一。尤其是在自己一個人的時候,所以說慎獨為難。李顒提出的一個辦法,還是靜坐。因為人不好靜,則不能用心。但是我們說,與其靜坐,還不如練太極拳,當然古人不會太極拳。因為太極拳也屬於心學,是治心性的。這一點人們還沒有認識到。拳學本身即是治理心性之術,有入靜的功效,而且鍛煉身體,綜合比較,遠非靜坐可及。從這裏能夠說明什麼呢?說明古人的修身之具還是非常簡陋的,這才是根本問題。所以千百年來思路打不開,理論之爭總是擠在一個極其狹小的範圍內打轉,原因即在於此,其實說破了非常簡單。李顒說,悔過自新,乃是為了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在宇宙為完人,今日在名教為賢聖,將來在冥漠為神明,」(《悔過自新說》)康熙
皇帝曾想召見李顒,遭拒絕,這表現了他的個人原則。
第二節 戴震字義
北方學者重實行,義理上固不如南方學者為勝。清代理學的代表是戴震,他自道自己的學術思想說,「僕生平論述最大者,為《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與段若膺書)又說:「蓋昔人斥之為意見,今人以不出於私即謂之理。由是以意見殺人,咸自信為理矣!聊舉一字言之,關乎德行、行事匪小。」(與段若膺論理書)這裏講得很清楚,把意見當成理,就會以意見殺人。意見是私、理是公,理與意見,公私之間而已。戴震之學,也就是要辨
明此二者。
他說:「古人曰『理解』者,即尋其腠理而析之也。」「後儒以理、欲相對,寔雜老氏無欲之說。」「不知欲也者,相生養之道也。能視人猶己則忠,以己推之則恕,憂樂於人則仁,出於正、不出於邪則義,恭敬不侮慢則禮,無差謬則智。曰忠恕,曰仁義禮智,豈有他哉?在常人為欲,在君子皆成懿德。」「況欲之失,為私不為蔽。自以為得理,而所執之理寔謬,乃蔽而不明。聖人而下,罕能無蔽─有蔽之深者,有蔽之淺者。自謂蔽而不明者有幾?問其人
曰:聖矣乎?必不敢任;而譏其失理,必怒於心。是盡人不知己蔽也。」(與段若膺論理書)
可見,這個世界上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不明理,反省己蔽是很難的。戴震認為,欲聞道,「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宋儒譏訓詁之學,輕語言文字,是欲渡江而棄舟楫、欲登高而無階梯也。為之卅餘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與段若膺論理書)由文字、語言以通道,也就是由名以通道,這是清學的真精神。老子說可道、可名,道與名的關係,在古代其實是一個常識
第一節 李顒悔過自新說
清代學術,導源於宋學。李顒、顏元是清初北方學者的代表。李顒是陝西人,顏元是河北人。李顒倡悔過自新說,實際上就是改進論。改進當然包括改正,只是切實功夫。時人以其卑之無甚高論而輕忽之,李顒提醒說,天地、萬物都是日新的,大哉自新之義。人文能走多遠,就看其改進如何。這一點,已經由過去的歷史顯示、說明瞭。所謂滿街能悔過自新,安見滿街之不可為聖人?虛譚性命,不過是英雄欺人語。關中之儒,橫渠以後,李子而已。「同志
者,雖無過可悔,亦不妨更勉之!」(《悔過自新說》小引)
李顒說:「人也者」...
作者序
前言
本書篇什的組成並非預先設計。正因爲不是預先有意而爲,其「隨意性」也許更能說明問題,更能反映出當今世界華文文學五光十色的多元性。當然,這還只是其中女作者的掠影。
非常明顯,這些女作家女詩人無論從年齡、國籍、身世背景以及文學成就、知名度都各不相同,甚至差別很大。例如,以九十一歲高齡於2007年謝世的郁風對於現在只有二十多歲的張鳴真來說就完全是不同世紀的人。至於國籍,他們有中國大陸的有臺灣的,有些已經移民加入別的國籍的,如澳大利亞、新西蘭或加拿大。陳若曦是一個很有趣的例子。她在台灣出生,在美國留學,文化大革命時回中國大陸工作,1973年離開大陸到香港,次年到加拿大,取得加拿大國籍,又在美國定居,現在又回歸台灣。她在香港發表成名作小説〈尹縣長〉和其他關於文革題材的作品,被稱爲中國大陸傷痕文學的先行者。臺灣文壇當然把她定位爲臺灣作家,但她又和美國、加拿大以及香港文壇扯上關係;美國華人會把她看作美華作家;中國大陸文史家寫文學史也可能乾脆把她寫成中國作家。
書中十多位作家詩人,大多並非文學科班出身,如張鳴真是悉尼大學傳媒學碩士,曾凡是北京清華大學建築系的高材生,胡仄佳年輕時學畫學美術設計;現在她們大多更不專事文學寫作不以此爲生,如梁小萍是著名書法家,郁風生前是著名畫家,劉虹是報紙編輯,孟芳竹從事電臺主持之類的文化工作,張翎是聽力康復師,而作爲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的中文老師,張典姊則在大學任教幾十年直到現在退休。
梁小萍是一個奇特的個案。有人說,談梁小萍的人生,沒有書法便顯得蒼白。但更應該說,談梁小萍書法藝術,不可不談她的詩詞。書藝之於她的詩詞,是養料、色彩、天空,以滿足她詩詞方面的超人的想像力和創作力。而詩藝,則使她的書法藝術更具個性和靈性,使其洋溢著一種古典式的凝重莊嚴卻又變幻新奇的浪漫情調。可以說,是詩詞賦予梁小萍書法藝術的獨特和高雅,進而構成她藝術意義的全部。而梁小萍的詩藝,尤以她的回文詩聯堪稱一絕。
這些女性有些已經享譽中國大陸、臺灣乃至世界華文文學,如陳若曦、戴厚英、遲子建、張翎等人。其中,在這一年多來,張翎的名字在中國大陸和世界華文文學圈子裏,可能是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個了。但這卻是一個不幸的事件—她因獲獎的長篇小説《金山》而受到誣衊和攻擊。幸好出版《金山》英文版的「企鵝」出版社已經爲張翎洗刷了冤名。
她們都是女作家女詩人,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識是自然不過的。例如中國大陸深圳女詩人劉虹,一貫重視作品的人文關懷,歷來還特別反感從太生物學的角度談兩性寫作的差異。她說,無論是他人評判還是女詩人的自我觀照,都應該首先把自己當作一個「人」,然後才能做女人。要跳出「小女人」的圈子,首先追求活成一個大寫的人,寫出真正的人話,以促進社會的更加人化。她還反復強調:一生反抗「被看」意識,是成為真正的現代女詩人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劉虹看來佔據了一個詩寫理論—或者擴大一點說—文學理論的高地,但這個高地在當今中國社會的經濟大潮的包圍、沖擊下,周邊已出現許多流失;而站在這個高地上的劉虹不免顯得煢煢孑立,形單影隻。
這些女作家女詩人中一些同時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識,很爲文壇矚目。戴厚英在長篇小說《人啊人!》她這部代表作品中,以「人」爲主題,寫人的血跡和淚痕,寫被扭曲了的靈魂的痛苦的呻吟,寫在黑暗中爆出的心靈的火花。今天的文學史家一般都把《人啊人!》看作是中國大陸「新時期文學」的經典作品之一。大多論者都同意,戴厚英在剛剛結束「文革」噩夢的初期,以自身的血淚經歷,對人道主義的高聲呼喚,不啻為當時整個中國大陸文壇的晴空霹靂,可謂振聾發聵!按與時俱進的說法,她的作品可稱為「以人為本」在「新時期文學」中最早的先聲。
陳若曦的《尹縣長》和《慧心蓮》前後獲中山文藝獎,她成了該獎唯一的兩次獲獎者,恰巧她自己也偏愛這兩部作品。筆者認爲,《尹縣長》和《慧心蓮》分別是陳若曦强烈的政治意識與强烈的女性意識的代表作,共同參與構建她的文學世界。陳若曦當年和夫婿毅然投身到「文革」惡浪滔天的中國大陸,後又以親身經歷寫出《尹縣長》《老人》等「文革」系列小說,顯示出她和政治的不解之緣。陳若曦也自認是「政治動物」。她爲「美麗島事件」領頭簽名致函時爲臺灣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並親自從美國返台求見蔣先生陳述臺灣旅美知識份子的共同政見,就是其中一次了不起的行動。她這大半生就是稟著知識份子良知良能行事。她發揚中國文人的傳統,不是只能坐而言,應該起而行。她指出,而且以自己的大半生證明:知識份子就是天生可以關心時事,批評政治,擁抱社會;知識份子沒有退休的權力,永遠關懷這個社會愛自己生長的土地。這是她恒久不變的精神。她堅持理想,一生無悔。陳若曦老師在本書交付出版社之際榮獲「民國一百年國家文藝獎」,實在當之無愧,可喜可賀!
本書中最後一篇是關於中國大陸著名女作家遲子建的雜談。評論界普遍認爲,遲子建是當代中國文壇爲數不多的卓具民間色彩特色的作家之一。她生於上世紀60年代,開始發表作品於上世紀80年代,此後在短短十餘年的時間裏,在當代中國文壇迅速崛起,長驅直入,完成了從一名文壇新秀到小說名家的身份轉換。這可稱之爲「遲子建現象」,特別是比照與她同時成名的一些作家目前創作的「漸成頹勢」;事實上這個現象已經爲當代中國文壇的女性寫作提供了一個不容或缺的注解並引起了超越國界的注意。遲子建多次榮獲中國大陸最重要的文學獎項。但她說她不要把一次次的獲獎當成樓梯,假若順著這些樓梯走上去,就會束之高閣成為空中樓閣。她特別深有哲理地這樣比喻:「世上的路有兩種,一種有形地橫著供人前行、徘徊或者倒退;一種無形地豎著,供靈魂入天堂或者下地獄。在橫著的路上踏遍荊棘而無怨無悔,才能在豎著的路上與雲霞為伍。」
今年十一月,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將在臺灣高雄市舉行第八屆會員代表大會,而且又與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在廣州共同舉辦全球華文作家研討會,兩個機構各自出席一百五十名代表,一起商議如何建構華文文學世界應有地位。這肯定將在世界華文文學歷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頁。筆者將出席這兩個會議,並代表澳洲華文作家向大會提交論文:〈從「世界華文文學」到「華文世界文學」——關於建構華文文學世界應有地位之拙見〉。此文作爲附錄收進本書。而本書亦算是筆者對大會的一個獻禮。
何與懷2011年6月26日於澳洲悉尼
前言
本書篇什的組成並非預先設計。正因爲不是預先有意而爲,其「隨意性」也許更能說明問題,更能反映出當今世界華文文學五光十色的多元性。當然,這還只是其中女作者的掠影。
非常明顯,這些女作家女詩人無論從年齡、國籍、身世背景以及文學成就、知名度都各不相同,甚至差別很大。例如,以九十一歲高齡於2007年謝世的郁風對於現在只有二十多歲的張鳴真來說就完全是不同世紀的人。至於國籍,他們有中國大陸的有臺灣的,有些已經移民加入別的國籍的,如澳大利亞、新西蘭或加拿大。陳若曦是一個很有趣的例子。她在台灣出生,在美國留學,文...
目錄
第一章 理學
第一節 李顒悔過自新說
第二節 戴震字義
第二章 樸學
第一節 章學誠
第二節 阮元
第三章 實學
第一節 存治
第二節 海國
第三節 邪教
第四節 共和
第五節 新民
第六節 天演
第七節 危言
第八節 留學教育
附錄:元代實學─扎撒
附:《成吉思汗法典》殘片
第一章 理學
第一節 李顒悔過自新說
第二節 戴震字義
第二章 樸學
第一節 章學誠
第二節 阮元
第三章 實學
第一節 存治
第二節 海國
第三節 邪教
第四節 共和
第五節 新民
第六節 天演
第七節 危言
第八節 留學教育
附錄:元代實學─扎撒
附:《成吉思汗法典》殘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