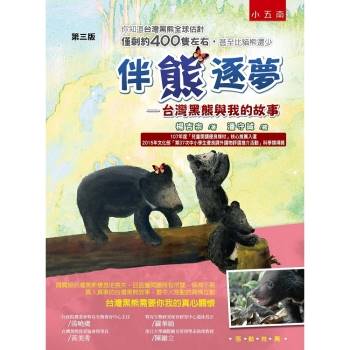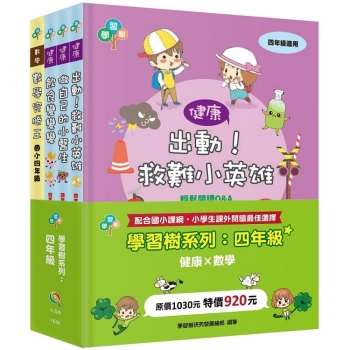序
「重寫歷史」是80年代典型的文化景觀,不僅有「重新文學史」、「20世紀文學史」,而且中國古代史、近現代歷史以及世界史都發生了重要的改寫。在某種意義上,80年代關於中國的自我想像和定位正是通過「重寫歷史」的工作來完成的。如果放在20世紀中國學術史和文化史的背景中,80年代並非唯一「重寫歷史」的時代,可以說「重寫歷史」是中國20世紀現代性的基本特徵,對於「歷史」尤其是線性歷史的認知也正是中國被動或主動捲入現代性的表徵。與西方現代性內部的古今之爭不同的是,古代(傳統、過去)/現代的時間意識只是中國現代性的一個維度,同時產生的另一個維度就是中國/西方的空間區隔,這種「古/今、中/外」的時空意識成為20世紀中國在不同時代確認自身位置的重要座標。在這種彼此交錯的時空平面圖中,中國並非始終像五四或80年代那樣處在「傳統」/「非西方」的位置上(暫且不討論這種五四與80年代的歷史對接來自於80年代特定的歷史隱喻),在傳統/現代與中國/西方的二元座標中還有第三個維度,就是在共產國際影響下的中國革命(某種程度上說,這個維度自五四作為中國現代原點的敘述起就已經存在,並延續至今)。正是這第三個維度,使得中國在二三十年代中國社會性質大討論之後,處在反封建主義(反傳統)、反帝國主義(反現代)的悖反空間中,這種混雜的空間位置(在反現代中追求現代性,在反傳統中重建傳統,恰如作為現代核心空間隱喻的城市/鄉村在中國革命敘述中處在混雜的狀態,也正如來自外部的革命者既是反封建的啟蒙者,也對現代主義激烈批判的反啟蒙者)成為中國現代性的基本經驗(這種空間位置也體現在毛澤東關於「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辯證論述中)。
中國革命的展開始終伴隨著對中國古代史、近現代歷史以及世界史的討論,從二三十年代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大討論嘗試用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來書寫中國歷史,到建國後對於古代史、近現代歷史分期的討論,以及「文化大革命」也涉及到如何把中國歷史書寫為階級鬥爭的過程。與從現代性的時空角度來重寫中國歷史不同(如五四時期關於現代的肯定與對「傳統的發明」同時出現),中國革命尤為需要不斷地「重寫歷史」,因為現實的革命行動與實踐正是建立對特定歷史的認識和把握之上。這些對於中國歷史及社會的認識,也始終伴隨著重建、重構歷史主體的工作,如果說20年代末期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討論涉及到中國革命的任務與方向,那麼對於工人階級、農民的不同理解則決定著中國革命的根本性質(是社會主義革命,還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而50-70年代社會主義歷史實踐的任務則在於確立以工農兵為代表的人民作為歷史動力的主體位置(暫且不討論這種實踐是否成功)。如果把這種「重寫歷史」及其確立人民主體的書寫方式作為中國革命的基本表徵,那麼80年代所展開的「重寫歷史」則是把三元或立體維度中的中國歷史重新放置在現代性時空座標的二元平面的過程,中國彷彿又回到那樣一個現代性重新開啟的時段,中國被還原為一處傳統的、非現代的「黃土地」空間,處在這個前現代空間中的主體則由曾經被革命動員的人民重新變成了需要被改造和啟蒙的前現代主體(進而文革之亂也被解釋為一種「烏合之眾」的愚昧)。
80年代在現代性視野下的「重寫歷史」基本上呈現的是一個斷裂的歷史,傳統/現代、中國/西方、革命/現代、50-70年代/80年代等處在內在衝突的狀態,這種狀態導致中國主體處在一種懸浮(如先鋒派文學所提供的是一種「沒有地點和空間」的世界主義想像)和悖論狀態(如尋根文學處在「尋根」與「掘根」之間) 。那個曾經在50-70年代文本成為敘述及情節動力的革命者以及被革命者所喚醒的、抵抗的人民在80年代的諸多作品中處在遊離和缺席的狀態,這就造成在八九十年代的歷史敘述中,佔據主體位置的是愚昧而狡黠的農民或原民,一群類似於早期魯迅筆下的「庸眾」和被砍頭者(如電影《紅高粱》、《老少爺們上法場》、《鬼子來了》等主角最終走向了刑場,而在革命敘述中,這些被砍頭的人民同時也是反抗的主體)。而更具症候的是在90年代關於中國歷史尤其是革命歷史的敘述往往使用西方人/他者的敘述角度,中國在他者的目光中呈現為一個女人(如電影《紅河谷》、《黃河絕戀》、《紅色戀人》等)。可以說,這種被砍頭和被觀看的位置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主體位置的基本特徵,在這種「被動」的主體位置中,一種「中國人」或「中華民族」的主體位置開始若隱若現。
這種曖昧的主體位置在新世紀以來的歷史敘述中獲得了改變,在「中國崛起」、「大國崛起」、「復興之路」等新一輪關於中國/世界近現代史的重寫中,中國開始呈現為一種作為民族國家的「現代主體」的位置,一個擁有悠久歷史和傳統、並在近代遭遇現代化的歷史中逐漸實現了現代化的新主體(如新革命歷史劇中的「泥腿子將軍」、《南京!南京!》中的角川視角等)。在這個意義上,80年代並沒有在八九十年代之交落幕,彷彿直到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終結之處,那份籠罩在80年代的現代化/新啟蒙論述才「開花結果」。如果說80年代是一個強調歷史斷裂的時代,那麼新世紀以來「重寫歷史」則是把斷裂的歷史重新縫合起來,把曾經激烈對立的傳統/現代、革命/現代、中國/西方等彌合起來,恰如80年代的文化參與者甘陽在2005年提出「孔夫子的傳統,毛澤東的傳統,鄧小平的傳統,是同一個中國歷史文明連續統」的說法(即新時代的「通三統」) ,這種論述如果放置在80年代的語境是很難想像的。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些「歷史重寫」中,一種新的歷史主體開始浮現出來。
自80年代改革開放、尤其90年代急速推進的市場化進程,中國社會迅速進入階級分化的時期,借用社會學家孫立平的表述就是社會結構及階層之間的「斷裂」。為了彌合階層之間的斷裂,新一屆領導人提出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等一系列論述,一種在80年代末期被熱情呼喚、在90年代被想像為社會穩定和民主化力量的中間階層開始佔據社會主體的位置(中產階級的保守性和激進性同時存在),這就是市場經濟內部的消費者──小資、白領及中產階級,與此同時則是底層、弱勢群體的被命名,或者說中產階級與弱勢群體同時成為新世紀之交的社會命名方式,來指稱經歷90年代市場化的雙重主體。中產階級/白領的出現被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看來是「一群新型的表演者,他們上演的是20世紀我們這個社會的常規劇目」、「白領的存在已經推翻了19世紀關於社會應該劃分為企業主和雇傭勞動者兩大部分的預測」 ,也就是說是中產階級打破了19世紀一分為二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二元世界,其「進步」意義在於更多的藍領工人白領化、知識精英成為職業經理人──不再是「白手起家」的美國夢、而是成為中產階級上層,而「反動」意義在於世界被一分為三,底層世界在晉升為白領的美夢中若隱若現 。
新世紀以來,在這種中產階級作為社會中間/中堅的主體想像中,公民社會、公民權利被作為「和諧社會」的「和諧」話語,成為某種社會共識,在這種共識下,救助弱勢群體、志願者精神成為新的道德自律。底層、弱勢群體雖然被區隔在消費主義的都市景觀之外,但他們也分享中產階級話語。在這個意義上,都市白領/中產階級成為或者被建構為「和諧社會」的「和諧」主體 。但是中產階級的主體位置與執政黨的官方說法處在微妙的遊離和分裂狀態,這種分裂產生於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建立在對50-70年代革命歷史的批判之上,因此,反官方/反革命/反主流一直是中產階級的底色。而有趣的是,新世紀以來,無論是2002年出現的「新革命歷史劇」,還是2007年以來的「主流電影」或「新主旋律大片」,都獲得了以中產階級為消費群體的認可,這些文本也成為流行的大眾文化文本。尤其是在2008年經歷一系列西藏騷亂、海外青年護衛奧運聖火以及「汶川大地震」「震」出一個「新中國」等事件中,中產階級與主流價值觀達成和解,或者引用《十月圍城》網友的說法,這部電影讓他「終於和『革命』這個詞握手言和」 ,中產階級被詢喚為新的歷史主體。
本書就以新世紀以來所開啟的新一輪「重寫歷史」為研究對象,主要呈現相關電影、電視劇等大眾文化文本以及《大國崛起》、《復興之路》系列、奧運會開幕式等國家文化工程的意識形態功能。特別關注兩個方面的內容,一個就是這些文本自身的文化脈絡或者說重寫策略,尤其是不同文本序列之間的差異。比如在新革命歷史劇中無往不勝的「泥腿子將軍」、諜戰劇中有勇有謀的「無名英雄」以及馮小剛的新主流電影中遭受委屈的英雄(《集結號》)和苦情母親(《唐山大地震》)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因此,也承擔著不同的文化功能;另一個就是這些「重寫歷史」的文化表述與中產階級主體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如何與反體制/反官方/反主流的中產階級達成想像性的和解,或者引用《十月圍城》的另一位觀眾在博客上的感言,這部電影使得曾經「蒼白」的主流意識形態「不再空洞,變得那麼真實!」 。
簡單地說,本書試圖處理以下幾個問題。一是,新世紀以來在電視螢幕上先後出現的新革命歷史劇和諜戰劇及其所呈現的「泥腿子將軍」與「無名英雄」的文化症候;二是,除了新革命歷史劇把革命故事講述為「激情燃燒的歲月」和「夫唱妻隨」的家庭倫理劇(電視劇《金婚》、《光榮歲月》、《王貴與安娜》等)外,50-70年代的歷史在中產階級的視野中被呈現為純潔、無害的童年歲月(電影《求求你,表揚我》、《鐵人》等);三是,近期主旋律大片屢創票房奇跡,中產階級從2002年中國電影票房回升之時就是主力軍,但《英雄》以來的古裝大片卻陷入「叫座不叫好」的怪圈,自2007年歲末上映的《集結號》始,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主旋律商業大片(如《建國大業》、《十月圍城》、《唐山大地震》等)。在此,我想以三部電影為例,《南京!南京!》、《十月圍城》和《唐山大地震》來呈現「主流電影」是如何實現反體制/反官方/反革命/反主流的中產階級與革命等主旋律論述達成和解的;四是,新世紀以來關於《大國崛起》、「復興之路」等文本,試圖完成中國從「落後就要挨打」的現代化悲情轉變為走向「復興」的現代民族國家(一種現代民族國家的主體需要放置在「復興」的文化表述中來完成),「中華民族」某種程度上被作為歷史敘述的主體,從而實現擁有燦爛文明的上下五千年歷史、悲壯的近現代歷史和50-70年代的革命歷史之間的「無縫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