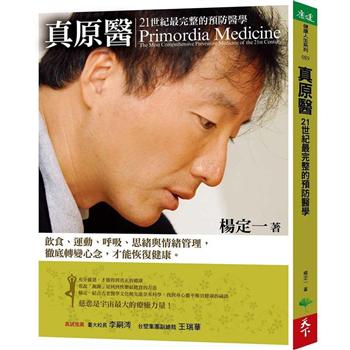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烏托邦幻滅王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189 |
散文 |
$ 202 |
中文書 |
$ 213 |
中文現代文學 |
$ 238 |
現代散文 |
$ 243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270 |
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烏托邦幻滅王國
約略在四十年前或更早,美羅中華中學的一些班上,有一群學生努力在課餘辦壁報,編期刊,寫文章。辦壁報,編期刊,寫文章,原本稀鬆平常,但姻緣巧合之下,文學活動開始穿梭於山城,慢慢翻掘和延伸到全馬各地,復又萌長於臺灣寶島的沃土。
這些文學活動如詩歌的清脆悅耳,散文的幽谷情歌以及小說的章回餘韻,日夜在不同場景出現,引來了同好者的赴約,星空下、山水間,聚會時感到溫暖,散席後行影孤單。過了一些時日,當中有些人處處展露才情,也有些人卻因理念相脖而跌宕失落,更有風光跋扈於現世,或隱居於都會鄉土者,交錯渡過其斤斤計算或與世無爭的生活。
現在,班上的這些青少年華,好像瞬間全都步入不惑之年,一晃,歲月無須交待,也無從細說,光陰的美目如何塗改他們精緻的一生,甚或是寥落的一世,都交由歷史的列車輾過,當有斑斑痕跡可以追溯。
這就是作者想出版第一本散文集的此刻,最想敘述的重要話題,書寫的故事從美羅開始翻山越嶺,轉程到了臺北後流連忘返,最後是過客般又回到大馬雪蘭莪州首府,那陪伴作者虛渡廿多載的莎阿蘭胡姬花城,生根後始終要作個了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