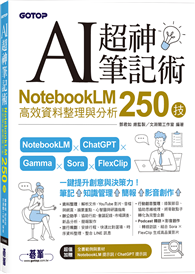序
補一堂中國搖滾的課
2008年五月我在北京。
五月十二號,發生汶川大地震;幾天後,在北京的星光現場舉辦一場搖滾義演包括眾多歌手如汪峰、艾敬,壓軸的是崔健。
那是我第一次看崔健演出。開場前的興奮與期待,不下於我去聽滾石或者狄倫;不只是因為他是一則華語搖滾的傳奇,不只是因為崔健在我二十歲的炙熱的青春是重要的聲音,也在於此前中國於我們來說根本是一個遙遠而陌生的存在:我們跟北京崔健的距離真的跟紐約狄倫阿伯差不多。
那晚演唱會結束後,在樂評人張曉舟的引介下,我們三人去吃宵夜,在北京的台菜店「鹿港小鎮」。我們談著音樂與政治,於我是一個如此的魔幻之夜。次年又在台北Legacy、在北京展覽館看了兩次崔健專場,依然震撼。
在那個五月的北京,我也和朋友受北京樂隊幸福大街女主唱吳虹飛之邀去她家喝酒。「在北京搖滾樂隊女主唱家喝酒」這件事,當時讓我感到莫名興奮,那畢竟是我和北京搖滾的初次邂逅。
那一回,我也認識了北京著名的自由薩克斯風手李鐵橋、當時還沒有如此大名的周雲蓬,和樂評人張曉舟。
那是一次開啟我的中國搖滾之旅的五月大門。
我們的確就是聽崔健、唐朝、魔岩三傑的一代。他們爆發的九零年代初,正好是我的大學時期,我的啟蒙時光。那也是新台語歌的時代:在聽了一個青春期的西洋搖滾後,我們終於有了華語的搖滾,終於可以跟著強烈的節奏高唱《夢回唐朝》、《一無所有》,或者《愛上別人是快樂的事》。
九零年代中期後,因為魔岩離開中國,我們幾乎斷絕了與中國搖滾的聯繫,只能偶爾買到台灣引進的蒼蠅樂隊,或者左小祖咒的《在地安門》台版等中國搖滾。
十年以後的2007年,我在北京鼓樓旁的一個小酒吧疆進酒,第一次看了中國音樂人的演出,那是一個許多人說好的盲人民謠歌手:周雲蓬。當時我們當然並不認識。我也在北京西邊的一個小的獨立白糖罐買了許多中國搖滾CD。然後是08年五月我在北京出版《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簡體版,開始重新認識並且連結起當代的中國搖滾。
我開始逐漸進入中國搖滾的場景,去看演出、音樂節,並且認真地補課,買中國樂評人的書、狂買當下或之前重要的搖滾專輯──只是,有些已然不存在的樂隊、有些傳奇的演出,是當時不在場的我得永遠錯過的,例如當年強悍瘋狂的舌頭、盤古、木推瓜,或者河酒吧時期的野孩子、周雲蓬,或者剛開始的迷笛音樂節。
我也和左小祖咒、周雲蓬、李鐵橋、小河、張瑋瑋、郭龍(以上四人曾同屬於一個樂隊叫美好藥店)、張佺(以上三人同屬「野孩子」)、萬曉利、吳虹飛、上海頂樓馬戲團的成員、廣州民謠樂隊五條人乃至萬能青年旅店成員,在深夜北京的胡同,在通縣、廣州、上海的小飯館中、在台北的快炒店或者「操場」喝酒,並和許多人成為感情深厚的哥們。我喜愛他們的熱情豪爽,喜歡聽他們談起那個在盛世之前、依然地下邊緣的北京,或者那些那個生活困頓但生猛無比的波希米亞時光。
至於少年時影響甚深的魔岩三傑,我也終於在摩登天空音樂節聽到如今有點臃腫的何勇嘶吼《垃圾場》、看張楚和一支金屬嘻哈樂隊合唱《姐姐》。(而後在我最愛的北京小酒館「江湖」見到張楚,並且有次在後海的胡同中與竇唯擦肩而過。)
少年時期深受中國搖滾影響的我,絕對不會想到我會帶著我的搖滾文字「反攻大陸」,聽到崔健親口說、看到何勇在微博上說喜歡我的書,並且有機會在中國擔任一些音樂獎項的評審。
這幾年,兩岸的搖滾交流也越來越多,重要的中國樂隊幾乎都一一來台,但我們對中國搖滾的歷史及其對中國青年文化的意義,了解依然相當單薄。這本帶點學術味的《搖滾中國》有系統地分析了中國搖滾的發展、社會意涵,以及後魔岩時期的轉型,為我們好好補了一門重要的課。
不過,本書仍然集中於兩千年前的歷史,而沒有針對當下。過去十年,搖滾樂越來越進入中國的青年文化,與此同時也更加地商業化、體制化,並且相比於九零年代後期,更失去想像力和爆發力。這個現象最明顯的就是過去兩三年搖滾音樂節在各地如蛋塔般湧現,其中許多都是地方政府和地產商支持的,其結果大多音樂節越來卻貧乏無趣。
但另一方面,雖然書中提到九零年代後期的搖滾如麥田守望者拒絕反思歷史與現實,而只是追求快樂,但也正是在這兩三年,由於中國社會矛盾加劇,中國搖滾也有重新「政治化」的趨勢,不論現在最有代表性的兩個主要音樂人左小祖咒和周雲蓬,或者這兩年最火的樂隊「萬能青年旅店」,都用音樂狠狠地撕裂社會的醜陋瘡疤,帶我們進入那個時代的黑暗迷宮。
這個主流化、商業化但也同時政治化的複雜現象,是當前中國搖滾最奇異的風景,並且正是中國的縮影:一方面我們看到中國崛起的光亮盛世,另一方面卻是社會矛盾的陰影不斷累積擴張。
最後,對我們台灣人來說,這本書除了為我們補一門中國搖滾課,更大的刺激可能在於,我們是不是也該有這麼一本記錄與分析台灣搖滾史的書呢?
來動手吧……
音樂與文化評論人,著有《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時代的噪音:從Dylan到U2的抗議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