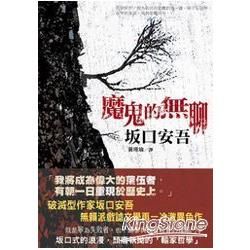譯 序
困惑的時代
一
翻譯這本書的時候,從第一個段落開始,我就感到困惑,就開始擔心,如果這本書要我來寫一篇導讀或譯後序時,我該怎麼寫?我有什麼可以說的?因為抱著這樣的心情,為了準備可能動筆的導讀,我開始一邊翻譯,一邊作書摘,一邊思索著:如果我是(土反)口安吾,我是以什麼樣的心情、什麼樣的思維寫下這一篇篇的故事?
我以為我做了萬全準備,書摘也存進了硬碟裡,甚至還備份在另一個隨插即用的大硬碟中。就在把翻譯稿傳給出版社,並接到編輯要我寫導讀的電話之際,打開電腦想開始動筆的那一剎那,竟然發現電腦整個死掉,檔案完全無法存取,甚至連電腦都打不開了。緊急之刻,臨時借了台電腦過來,想著我還有一個備用硬碟,卻沒想到插上電腦,竟然連這個備用硬碟也壞了。
於是,硬碟拿去送修,壞掉的電腦依然沉默地躺在我的房間,借來的電腦又原班人馬地搬回去了。有時候,人是這樣的,那鼓想努力去做的心情,一旦洩了氣,就很難回復了。
這段期間,出國了幾趟,忙了一段時間。雖然回來之後,經常接到編輯催稿的電話,可是,總是拿沒錢買電腦給自己當藉口,一直把這件事情擱著。拖到實在不能再拖,終於上網買下電腦。感覺就好像是為了寫這篇文章才買了電腦,似乎寫完這段文字,電腦就沒有用處了一般。這篇文章掛在心口,總想著會有比我更適合寫這個序的人,於是,似乎可寫可不寫,但是,答應了又必須完成,為了逃避內咎,只好真的動筆寫這篇序文。
動筆的這一刻,才想起這種心情,似乎在書裡某處看到過:
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雖然,我還是寫了劇本,但是,這是因為這不是正常的工作,這只是份為了逃避沉重苦悶的災難,而完全不需要本著良心去做的工作。畢竟,我這一條在戰爭裡荒廢了的靈魂,根本是不能工作的。
因為不斷出現意外狀況,使我在心情上,不斷想拖延這篇稿子,這才讓我理解到作者那份在廢墟中完全提不起勁、卻又不得不為了逃避內咎的災難而動筆的心情。於是,我覺得我真的可以開始提筆了。
二
(土反)口安吾,出生於明治三十九年(西元一九○六年),死於昭和三十年(西元一九五五年)。他一生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人生觀與小說觀,都深受戰爭的影響。在其短短五十年的生命中,創作豐富,涉足的領域廣泛,不只創作純文學,也寫歷史小說、推理小說、散文,甚至也寫文藝評論。
其中較為重要的作品有〈墮落論〉,描述戰爭中所有道德倫理的瓦解,「墮落」之當然,引起許多讀者的迴響。另外其《白痴》(新雨出版)一作,也給社會帶來很大的影響。(土反)口安吾與織田作之助、太宰治等人,共同被歸類為「新戲作派」、「無賴派」作家。他們以頹廢、自虐的風格,創作出諷刺性意味濃厚的作品。
三
在(土反)口安吾的那個時代,大戰期間,許多作家被徵召到軍隊裡面,成為隨軍記者。但是,當時的隨軍記者必須寫出歌頌軍隊的文章,若涉及真實的人性,或戰爭中的非人性部分,忠實寫出作家敏銳感受到的戰爭殘酷的文字,就會遭禁,甚至遭起訴被判有罪,就如日本作家石川達三所經歷過的一樣。
我想,或許這就是〈魔鬼的無聊〉產生的背景,唯有當一個不成才的作家,唯有毫不在乎生命、毫不在乎人性、毫不在乎死活,才能自在地活著。但是,當這一切都不在乎的時候,活著也變得可有可無,變得像惡魔的無聊遊戲,在虛空中,無所謂地擺盪,不知不覺就存活下來了,活下來了,卻也沒有多大的喜悅,一切都只是無聊而已。
在那個時代背景下,課本裡奮發有為的青年,反而顯得可笑了。因為他們會咬牙切齒地說「我要活下去」、「我要盡一切努力」之類的話,我們現在教育孩子,也總是要孩子們盡力,要孩子們珍惜生命,好好活著。但是,在那個戰亂的時代,昨天還在的高樓大廈,也許一顆子彈落下,明天就成廢墟。剛才還跟你說笑的女子,幾個小時後就成為燒焦的灰炭。一切是如此無常,所有的堅定信念,都變成一場笑話,甚至反而是超現實的。於是,作者消遣著這些有為青年:
我覺得荒君、平野君很像小說中的人物。他們本來就是讀小說讀過頭的人,那種思考方式或說話方式,與其說是現實,倒不如說是充滿小說風格。他們的腳會不會其實並非踩在土地上,而是踩在托爾斯泰或杜司妥也夫斯基上頭呢?他們跟老婆都如何交談?我是知道他們會對老婆說的話啦,但是他們的老婆又是怎麼回應的呢?
在這個時代,生命是無常的,無法靠著人的努力去掌握。明明你無法確定下一秒炸彈會不會落在你頭上,你怎麼還能信誓旦旦地說「我會用盡一切手段活下去」呢?這樣的說辭,反而像是小說中的對話,而不是現實的對話了。
四
那似乎是一個所有事物都反過來的年代,這讓我想起我剛開始翻譯這本書時,總會有一些些不自在,因為(土反)口安吾描述的世界,似乎顛覆了一個循規蹈矩,按照社會現存價值觀在努力打拼的人的想法。尤其是在(土反)口安吾的筆下,認真奮鬥、努力誠懇的人,總是會有悲傷的結局,就像〈肝臟醫生〉的故事。
這是個讓人笑不出來的悲劇,可是,赤城風雨醫生的一生,就是一部讓人笑不出來的悲劇。
赤城醫生若生在現代,或許會被認為是一個誠實認真的好醫生,但是,在那個價值觀錯置的年代,赤城醫生卻像是不斷推石頭上山的尤里西斯,總是徒勞無功。
「赤城醫生有很多這種患者,也就是說,信仰者。全都是因為他的人格。有些信仰他的人會說,他的診斷不行,但是,他的人格卻讓人難忘。醫生聽到這種說法,是高興不起來的。一名醫生,受到尊敬是因為對他人格的崇敬,而不是醫學上的見識,醫生自己是不會滿意的。赤城醫生就是這樣,除了當個醫生,他沒有任何野心,因此,像我們這樣的信仰者,反而讓他感到困擾。」
這段話,不,應該說是赤城醫生的整個故事,都讓我的腦海裡不斷出現幾個人:契坷夫、周星馳。反諷的筆調,帶著一點悲憫,特別趨近於周星馳電影中描寫的小人物。這一個小人物,即使握有數千個病例,還不敢直接對病人說出真正的病症,要用夾帶的方式說明,當書裡描述到赤城醫生的心境時,身為讀者,有一種想笑的心情,卻又哀傷得不知道怎麼笑起:
他很想裝作行若無事的樣子,但是,就是很在意那個「也」字,說到那個字,就會很奇怪地特別用力。後來,先生每次看診,都會與那個「也」字奮戰著,他必須與自責的痛苦奮戰。所有的患者都是肝臟炎,面對此不動的事實,為什麼會畏縮呢?先生對自己的窩囊感到懊惱。
〈肝臟醫生〉曾被電影導演今村昌平改編成電影,根據電影的簡介,導演似乎加入了很多小說中沒有的角色與情節,拍成了比較勵志性的影片,減少了若干帶著淡淡悲傷的反諷。
五
(土反)口安吾的書寫裡,另一個不可或缺的主題,就是女人。
有時會望著一個女人漫不經心的微笑,玩弄著一具只是快樂而放蕩的肉體,如此而已。
「女人等於肉體」這個主題,不斷出現在(土反)口安吾的文字之中。女人是不思考的肉體,會思考的是男人。他期待中的女人是僅具形體與功用的器皿,更接近於人偶:
我心想,女人若是個不說話的人偶就好了。眼睛看不見,也聽不見聲音,我希望她是個回應我孤獨肉欲的無限剪影。
他藉著安子的口,也說出了他心中對女人與男人差異的定義:
我不會輕視肉體或這種肉體遊戲,我也不怕玩弄肉體或拋棄肉體,只是我要求代價。相對地,我想要某種其他可以提高我的東西。女人的心只能靠男人的心來提高,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只要是可以提高我的心的男子,不管是誰,我以身相許都不後悔。
這個世界是以男人的心智創造而成的,女人是依附在男人的世界中成長的肉體,這具肉體深深耽溺於肉欲之中,不可自拔。
女人肉體的弱點,就是即使心裡懷有如此極端的厭惡或輕蔑,依舊深陷孽緣的泥沼之中,無法脫身,這就是女人肉體的悲哀。
即使如此,男人卻矛盾地羨慕女人的單純,單純地擁有肉體與享受肉體。
男人確實只是群凡夫俗子,根本比不上園子屁股的行雲流水境界。水不會停留,也沒有陰影,她的屁股純粹就只是屁股,所謂明鏡止水,就是如此。
只是所謂的肉欲,所謂的愛情,都是虛無而空泛,好像隨時都可以放棄,因為不管是肉體或愛情,都填不滿內心某處的空洞。
我的心只是個貪心鬼,它總是這樣喃喃自語著,為什麼一切都是如此無聊啊!都是如此無止無盡的虛無!
六 尾聲
閱讀每一個故事時,自然而然地會期待一個結局,然後,我們會把故事歸類為悲劇或喜劇,有圓滿結局的或是悲慘結局的,即使故事的主角遭遇悲慘,從頭到尾都讓人掉淚,即使最後是悽慘無比的完結,我們也總期待有一個結局。
王子與公主結婚了,是一個美麗的結尾。賣火柴的女孩凍死了,是一個令人唏噓不已的結尾。大團圓是一個結尾,世界末日大毀滅,也是一個結尾。縱使是有史以來最悲慘的約伯的故事,也依然謹守本分地有開頭、有高潮、有尾聲。
約伯是《聖經》裡其中一卷書〈約伯記〉的主角。神跟他開了一個大玩笑,在某個風和日麗、一點都不像會有遽變的日子,他突然失去了每一個家人,失去田產、房屋。在他失去一切之後,痛不欲生,披頭散髮責問神。
約伯的故事,在《聖經》裡面只有幾十頁的長度,我們可以輕易地翻到最後一頁,看到約伯又重新獲得妻子,重新把孩子都生回來,重新拿回每一分家產。讀到這裡,讀者們就鬆了一口氣,知道無論如何,到最後都會得到一個句點。但是,把十幾頁的故事,放進人生的量尺上,那幾十頁的悲慘,卻如同十輩子一樣地漫長。人很難去想像,要如何走過這十幾頁,總以為這一生都要沉落在這樣的悲慘中,無止無盡,永遠找不到句點。
看(土反)口安吾的這本短篇小說集,就有一種被擺放在人生的中途的感受,回首一片茫然,前路又不知道在哪裡,路旁一片廢墟,生命、愛情,都被擺在可有可無的位置上。每一個故事,都在嘲諷之後,留下一絲絲悲傷,一點點不滿足,一點點不知所措,以及尋找一個句點的渴望。
這是一篇篇寫在困惑的時代的故事。
黃瑾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