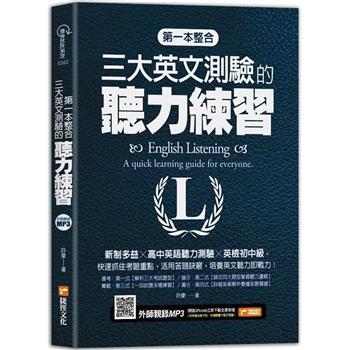山田風太郎賞受賞
週刊朝日「年度最佳歷史小說」Best 1
本屋大賞第一名《天地明察》系列二部曲
週刊朝日「年度最佳歷史小說」Best 1
本屋大賞第一名《天地明察》系列二部曲
風靡台灣日本觀眾心中,他是歷久不衰、有如常青樹般不老的正義化身;
在真實世界中,他是文武雙全、興農勸學的一代英傑——
以正道為心、以蒼生為念;
奔馳於太平盛世的熱血之虎——水戶光圀
本屋大賞得主 冲方丁
以非比尋常的熾熱之筆,深刻勾勒鮮明強烈的人生
顛覆所有傳統視野、最震撼靈魂的「水戶黃門」故事!
在日本的電視上、商店裡,甚至是小鋼珠店的機台,
隨處可見一位拄著拐杖、相貌和藹,留著白鬍子和白眉毛的老先生;
這位看起來很親切的老先生就叫做「水戶黃門」,
是位熱愛微服出巡,體察民情的天下副將軍
每當貪官污吏欺負人民的時候,他就會適時現身,
保護人民、懲罰惡人,為窮苦百姓伸張正義……
只是,眾人眼中威風凜凜的他,在成為「水戶黃門」之前,
也曾經度過無數磨難、挫折,以及自我質疑的掙扎。
背負著「篡位者」之名,苦苦追尋正道卻屢求不得的年少歲月;
縱馬輕狂,恣意狂暴,將滿腔熱血發洩在奇言異行之上的青年時代;
與摯友愛妻相遇,終於得到心靈依託,卻又在轉瞬間失去一切的空虛中年,
最後是與學者朱舜水相遇,潛心於史學之中的學術人生——
坐在梅花盛開的草廬間,兩鬢霜白、銀髮如絲的水戶黃門——德川光圀提起筆,
將埋藏在自己心底深處、從未告知任何人的過往種種,一點一滴紀錄下來……
與《天地明察》相互爭輝,波瀾壯闊的大河小說!
名人推薦
一部嶄新面貌的「水戶黃門」故事;
閱讀此書,必會為了這個男人的「義」而感到熱血沸騰吧!—演員‧中江有里
如果說天地明察是為了實現夢想而奮鬥的「勇氣之書」的話,
那麼光國傳就是一本貫徹自己生命意念的「勇氣之書」。
無論身處再怎樣的困難與束縛,又為了達成目標而焦燥不安、苦苦掙扎,
光國仍然以全心全意,努力地活著;
這樣的他,讓我打從心底最深處,洋溢起難以磨滅的熱情。—三省堂書店大阪店店員.中澤惠
不管生命有多麼充滿悲傷,我們都應對「活著」這件事抱持著喜悅。
這是人的義務,也是人的本質。
光國將這樣的真義,傳遞給所有的人們,同時也跨越時空,教會了我這件事。—冲方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