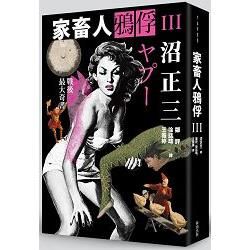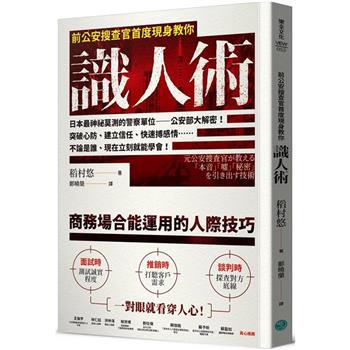你無處可逃,也無路可躲;
因為,你所認知的這一切,全都是我所創造之物—
西王母、赫拉、天照大神、武則天……竟然全是某位邑司人的化身!?
一切古史傳說,現在全都要被癲覆
徹底解構道德威權 最燦爛奪目的倒錯萬花鏡
第三冊全球中文版 首次發行
特別訪談 康芳夫X高取英 專文導讀 巽孝之
調教,就是要鞭子與糖果並用。
身為一位熟練調教狗和馬的女性,克拉拉雖然不曾調教過人類,但調教起麟一郎,卻是自然而然、駕輕就熟;在她恩威並施的調教下,麟一郎慢慢脫去了「人」的尊嚴,往忠犬的方向一步步邁進。
這一人一狗來到了位在地球上空的天空之城「高天原」,在那裡,她們遇到了一位神祕美豔的女性安娜‧泰勒斯。這位安娜號稱是前史英國首相鐵娘子的後人,然而不只如此,她還是日本的創世祖「天照大神」、希臘神話的天后「赫拉」、遠古傳說中的「西王母」,以及中國史上最有權勢的則天武后,而她一夜風流的對象,居然還有漢武帝劉徹……!?
作者簡介:
沼正三
(一九XX年生,二○XX年卒);
XX縣出身,XX大學法學部畢業,曾任職於XX機構。
自稱在二戰末期曾經遭到白人女軍官的俘虜與性虐待,從此養成了被虐狂的癖好;一九五六年起在雜誌《奇譚俱樂部》連載〈家畜人鴉俘〉,甫一推出便以奇想天外的構思、充滿專業的炫學,以及驚世駭俗的價值觀震撼文壇,一時蔚為話題。一九五八年連載至二十八章時一度中斷,此後直至一九七○年才得以出版,但仍舊是未完成的版本。(當時由於文中描述「天照大神乃是邑司白人」一事,引發了右翼團體的抗議乃至暴力行為。)之後又歷經數度刪補增削,終於在一九九二年以四十九章、全五冊的完整版問世。
除了《家畜人鴉俘》以外,沼正三還著有《某夢想家的手冊》、《被虐待狂M的遺言》等作品。關於其身分,至今仍有諸多揣測,有人猜測是法官倉田卓次,也有人認為是故事後段,自稱「沼正三唯一代理人」的小說家天野哲夫;但是隨著倉田、天野兩氏的陸續逝世,此事或許也將成為永遠的謎。
譯者簡介:
鄒評
台大日文所畢業。譯有坂口安吾選集《盛開的櫻花林下》。啃書咬文嚼字的譯者生活中。
徐廷瑋
台大日文所畢業。喜歡摸索文字排列組合的各種可能性,熱愛雙關語。
王薇婷
台大日文所畢業,生性愛書、嗜字、好吃。目前過著教師與譯者的雙重人生。
各界推薦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二○一六年二月,《家畜人鴉俘》,復活——
《家畜人鴉俘》,一部宛若鳳凰涅槃的作品。
日本,一九七○年,《家畜人鴉俘》第一冊初版。不過,直到一九九二年,這部五冊巨著才終於得以完整問世。
台灣,二○○二年,《家畜人鴉俘》出版了第一、二冊,獲得許多讀者的驚歎與對後續故事的期盼──然而,縱使我們耗費了許多時間,不斷地透過版權代理向日本出版社溝通、協調,傳達我們希望能在台灣出齊《家畜人鴉俘》的決心,卻始終無功而返。
這是一部有太多謎團的書。作者是誰?他還活著嗎?權利人又是誰……種種問題,使得在台出版的難度大大增加。
直到二○一五年,一月。這是個奇蹟般的日子。我們接到目前居於日本的漫畫編輯──吳塵罡先生來電,他代表日本最早發行《家畜人鴉俘》、有「世界十大奇人」之稱的康芳夫先生致意在台出版《家畜人鴉俘》的新雨──我們立刻把握了這個機會,多次表達我們「在台出齊《家畜人鴉俘》」的盼望與誠意。之後,感謝康先生的慨然大度,以及吳先生熱切奔走、協助,跨越十年光陰,我們終於能夠將「鴉俘」世界的全貌,呈現在台灣讀者面前──
僅向十年來翹首盼望的讀者,致上最誠摯的歉意與謝意。
—新雨出版社編輯部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二○一六年二月,《家畜人鴉俘》,復活——
《家畜人鴉俘》,一部宛若鳳凰涅槃的作品。
日本,一九七○年,《家畜人鴉俘》第一冊初版。不過,直到一九九二年,這部五冊巨著才終於得以完整問世。
台灣,二○○二年,《家畜人鴉俘》出版了第一、二冊,獲得許多讀者的驚歎與對後續故事的期盼──然而,縱使我們耗費了許多時間,不斷地透過版權代理向日本出版社溝通、協調,傳達我們希望能在台灣出齊《家畜人鴉俘》的決心,卻始終無功而返。
這是一部有太多謎團的書。作者是誰?他還活著嗎?權利人又是誰……種種問題...
章節試閱
安娜・泰勒斯的慈畜主義(註:原文作チャリテイズム。爲「慈善」(チャリティー、charity)與「思想、主張」(イズム、-ism)的合併語,為沼正三所原創。)
四肢伏地、蜷縮著手足趴在寶琳旁邊,身下有著紫色滑雪板的雪上畜突然開始顫抖了起來。
「看來是想要早點讓我搭上去呢?」寶琳一口喝乾杯子裡的靈液,將杯子交給飄在一旁的畜童之後,叼起一根煙草:「看牠都興奮得發抖了。」
另外一隻畜童從上方飛近,頭下腳上地幫這位女貴客叼著的菸草點火——摩擦手指就能點火,這裡面到底有怎樣的機關啊?
「這也是沒辦法的嘛。」愛喝蘇摩到了一種接近中毒狀態的美青年威廉暢飲著第三杯,說道:「牠們可是等了整整十八年呢。」
「而這也是科特維古小姐第一次踏乘雪上畜呢。」安娜朝克拉拉說:「既然這樣的話,就還請您愛護——或者該說好好『疼愛』牠喲,『要有慈愛之心』(Be in charity)!」
「還真像是慈畜主義者(charitist)會說的話呢。」威廉饒富興味地說著。
「唉,以前的口頭禪順口就出來啦。」姿色依然青春,完全看不出來是位老婦人的安娜,此刻也露出了一陣苦笑,讓人可以一瞬間體會到她的歲月陰翳:「不過,你都提到了,這就讓人懷念起以前的時光啊。你大概是讀了我的書,所以才知道的吧?真沒想到會從你這樣的年輕人口中聽到這個字……」
克拉拉喝到第二杯,終於可以理解蘇摩這種風靡邑司帝國的飲料美味之處。她邊飲下第二杯最後的一點美汁,將目光移向腳邊那隻趴在桃色滑雪板上的雪上畜。
從還不懂事開始就被以「讓人類踩踏」為最高唯一生命目標訓練而來的這隻動物,牠那肌肉十分精實的黃色肌膚上所烙下的三十二個鍵點,還有象徵牠在「雪上畜評鑑會」中得到最優等的金色項圈,以及那足以記住深難的雪質學知識,應該具備具備極高IQ的腦髓……牠數年來的辛苦,全都奉獻給身為一種運動道具,身為「雪上畜」的人生——而對克拉拉她們而言,那些不過是娛樂的一環罷了。身為具備知性的動物,牠難道沒有懷疑過自己生命的意義嗎?
——雪上畜啊,你希望我踩在你身上嗎?這樣你就滿足了嗎?
好,那麼我就好好疼愛你吧。
克拉拉低下身子,伸出手去撫摸了雪上畜的頭髮。或許是因為憐憫吧!但我們實在無法保證這並不是因為那一頭黑髮讓克拉拉聯想起麟一郎。
「克拉拉?」威廉用低沈的語音,帶著一點斥責的口氣道:「又不是寵物,摸頭很奇怪耶!」
克拉拉慌張地將手移開,而安娜為之緩頰:
「哎呀,得萊帕少爺,你都知道慈畜主義這個詞現在已經不通用了,不是嗎?科特維古小姐這麼年輕,誤解了我說的『慈愛』的意義也是很正常的啦。」說罷,安娜轉向克拉拉,說:「我說的『疼愛』跟『愛撫』是不一樣的。雪上畜就是鞋類啊,你要疼愛一雙鞋子,當然就是把它們穿在腳上就是最大的疼愛了,不是嗎?」
「這還真是失禮了……」
克拉拉滿臉通紅地道了歉,但是總覺得心底有點不太適應:為什麼「穿一雙鞋子就是對鞋子最大的疼愛」?
「我啊,」寶琳拿著煙,邊開始吞雲吐霧邊說:「常常聽家慈說,拜您的慈畜主義所賜,鴉俘們的工作效率獲得了提升,這點我自認還算了解,可是看到克拉拉小姐的誤會,就突然覺得……」似乎是在替克拉拉說話,又不想損及眼前這位老婦人的興致,她稍微沉默了一陣子,才繼續開口說:「慈畜這個字總覺得不太對勁啊。要鴉俘們把痛苦當作快樂,這真的能叫做慈愛嗎?這要是在人類的話,就是個『調教被虐者』*的遊戲啊。這種虛偽的好意,離真正的慈悲和愛情,難道不是很遠的嗎……?」
*調教被虐者(被虐馴致),是一種邑司的貴婦們所熱衷的「愛情狩獵遊戲」,比試的是自己的能力,目標是將平民男性變成自己的「崇拜者」(fan),同時調教成完完全全的被虐狂。規則不太一定,有比賽誰先成功攻下指定男性的心的,也有個別去找男人,然後比賽在一定的時間內誰能夠將自己的「崇拜者」洗腦得更嗜被虐。使用暴力,或是先告訴那個男性自己的企圖都以違規論,所以比拚的就是貴婦們自己的手腕了。卡路星雖然說是「樂園」(白人居住星)的代表,但居住於此的平民也有可能遇上這種「狩獵」,而變成身體不自由的「天狗」(第二九章)。
(J・西蒙斯《風俗談義》)
「可是牠們是動物啊……」威廉接下了話頭。用靴子的底磨蹭了下腳邊那隻趴在茶色滑雪板上的雪上畜的頭後,寶琳繼續開了口。
「是的,牠們是家畜,所以要怎麼『教育』牠們都沒關係。當然我不是說這不好,但是這些『教育』說穿了也不是為了鴉俘們,而是為了我們人類啊。這真的能說是慈畜心的表現嗎?不是應該要為了對方著想,才能稱作是慈愛嗎……?」
這時,有隻鴉俘不聲不響地出現了。牠從頸部以上是黃色,但以下全身都是綠色的……刺青。牠的全身被刺上了無數的綠葉,而那推得過高的額頭以及整個臉上刺的,則是花瓣重重綻放的黃菊花。若不看刺青的話,這隻鴉俘看起來就跟原生鴉俘沒兩樣,完全沒有標準型廁畜的奇形怪狀。只見牠走到安娜的身後仰躺在地上,接著將腰部以下往自己的頭部彎起,同時抬起上半身,讓頭探出自己的兩腳之間。那張出現在臀部和兩腳間的黃色臉孔,正像是一朵被背部、胸口和腹部的草葉所映襯的大菊花。而安娜此刻離開肉椅子,悠悠哉哉地在那朵大菊花上坐了下來——那朵菊花正中央的「大口」,一顆牙齒都沒有。
克拉拉突然意識到這東西就是一個廁畜。大概是具備讀心功能的單能具吧!但,要宛如雜技表演選手般將身體彎曲成這個樣子,顯然經過長期的訓練。
麟雖然在彎曲實驗(第二十章之4)中得到了滿分,但是能做到這個地步嗎?真是太厲害了……
「是在為對方著想啊。」安娜自信滿滿地說著。「所謂的白神信仰教育雖然就結論而言是在方便我們人類,但是歸根究柢還是為了鴉俘們啊。至少,我推廣主神崇拜的新福音,就是基於這種心情……我們人類的生活需要鴉俘,而我們無視著他們的意志,命令他們坐著被命定的工作,就像這樣……」
安娜像是在對臀下的肉便器示意似地,低下頭看了看,然後繼續說:
「每天我們都會用很多次廁畜,但是大部份的人完全沒有考慮過廁畜的心情。而就算真的去考慮了也啥都不做——『把我們賞賜給牠們的東西吃下去,這就是鴉俘的存在意義』,大部份的人都這樣把這個問題給『解決』了;因為我們的生活沒有鴉俘過不下去,所以這就是鴉俘存在的理由,這樣就滿足了。但是,具備慈畜心的人們可不這麼想——雖然有點自賣自誇,但有句話叫『德及於禽獸』,那麼廁畜到底有什麼感覺,也是令人很在意的啊。標準型肉便器打從出生以來就在白神信仰中長大就算了,但妳可曾試著自己將土著鴉俘調教成肉便器過?」
現在在安娜身下的,並不是打從一出生就被教育為廁畜,而是將土著鴉俘進行肉便器化而成為廁畜的,所以牠的體型也不像一般標準型的便器。貴族用的單能具有不少都是後天「打造」的,不知道這點的克拉拉,此刻驚異非常。
「有啊,還蠻多次的。」寶琳淡然地回答。「我常調教的也是這種威靈頓型鴉俘,尼爾森型偶爾。廁畜既然是貼身家具,基本上都是用旋繩、口球和鞭子來調教。」
「我跟你們不一樣,大部份都是調教尼爾森型呢,威靈頓型反而不太常弄。愉悅度不同。」威廉又插了一句進來。
克拉拉此刻想起昨天到達水晶宮後威廉說鴉俘是「為了揮鞭而養的家畜」,又說將牠們做成便器可以「得到極大的悅樂」(第十二章之5)。
「那我想你們也知道,在調教剛開始的『神嘗之儀』(發誓自己將成為品嚐神賜之物的存在、對液體固體各嚐一口的儀式。附帶一提,調教結束之後,身為新的廁畜,第一次品嚐主人賜物的儀式,則稱為「新嘗之儀」。)中(註:神嘗(かんなめ)和新嘗(にいなめ)都是跟日本皇室有直接相關的祭儀。原本是指秋收後獻穀物與祭品給諸神(新嘗祭時,天皇也會「新嘗」當年的新米)的祭典。特別是後者衍伸出「大嘗祭」(だいじょうさい)這個每當天皇即位時都要辦一次的大儀式。這兩者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第一次吃到我們排泄物的鴉俘那臉上的表情到底有多扭曲了。從那些表情就可以知道,我們每天毫不在意塞給廁畜們的那些東西原來的味道……一定,非常難吃的啊。(先不論美味與否(第六章之2),邑司人其實不是很清楚自己的糞便的營養價值。)仔細想想也是理所當然的事,那東西可是我們的身體吸收過後的殘渣,又怎麼可能好吃呢?但無論鴉俘們怎麼想,還是得吃下那些東西,難道妳們不覺得這很可憐嗎?」
安娜這次轉向克拉拉發話,而克拉拉雖然取出了諮詢器,卻在安娜的長篇大論之間來不及使用。「嗯,是啊。」宛如自己也成了和御魂的主人般,克拉拉點了點頭。
「有句話說,『惻隱之心為仁之端』(Pity is akin to love)。沒錯,憐憫正是慈畜心的第一步喔。」
「那位《家畜人解放論》(第四章之3)的作者也……」
寶琳本想插話,卻被安娜輕易接走了話頭。
「凱勒妻君是吧?雖然看似很像,可是根本上有著完全不同的差異。他覺得鴉俘也是人,而我從沒這麼想過—這簡直蠢極啦。據說他因為這樣,再也沒辦法使用肉便器,而我完全沒有這個問題。我想在不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下讓鴉俘幸福,想要拯救牠們,每天讓牠們吃好吃的……這種心情,就是慈畜心—」
「跟赤Y字思想也有點共通之處呢。」威廉說。
「在不把鴉俘看做人類的這點上確實如此,但是南丁伯壹勳爵的思想原本有就被凱勒影響的危險一面。因為我和赤Y字也有關連,所以可以暢所直言—以慈畜主義運動為分水嶺,他們在愛護動物和防止虐待家畜的內容完全是相反的啊;唯一能算是貫徹始終的,也就只有在治療病畜這點上了。以前啊,他們可是揭著『反對虐待』的標語,主張要求限制揮在鴉俘身上的鞭數,或是禁止使用珍棒呢。為了鴉俘,他們要我們改變自己的生活呢!雖然有點太過跳躍,不過你們能想像,沒辦法用鞭子快樂調教土著鴉俘的人生嗎?」
所有人都無言了。
「主神崇拜這種信仰教育,就是為了讓原本不過就是虐待的東西成為愛護啊。方法上,不改變我們的生活,而改變鴉俘的想法。現在赤Y字的愛護動物也是這種感覺啊。」
「您之所以被稱贊為『赤Y字運動的中興者』,原來是因為這樣啊。」
「這個廁畜剛享用完我給牠的大餐。」安娜無視威廉的插嘴,繼續說了下去。
「『真是太難得了、給我真是太可惜了、我拜領了!』牠們就是這樣子在感謝我的,而那也是因為我是牠們的神明啊。在毫無信仰時這些工作不過是痛楚,但有了信仰後,這些事就成了悅樂,虐待也成了愛護了啊!」邊說著,安娜回到了她的肉椅子前,而那奉仕完自己主神的廁畜——直到他變成廁畜為止,大概都在邪蠻國裡當一個人當得好好的土著鴉俘——做完了感謝禮拜後,便回到了牆中去。今天的牠會寫出怎樣的報告呢?
「把明明很難吃的東西,用信仰讓對方錯覺般地吃起來像頓佳餚,這難道不是人們的狡猾與欺詐嗎?」寶琳提出了她的疑問。
「不,味覺沒有真假;只要有了愈深的信仰,在沒信仰時愈是難吃的東西就愈美味。剛剛那個廁畜也是這樣,從一開始的神嘗之儀後,我就一直命令牠寫報告,而牠的報告裡也透露出漸漸覺得那東西很好吃呢。這就是信仰的力量啊。而這張肉椅子也是—」
安娜掃視了一下大家坐著的那些椅子:「在肉體上,牠們應該覺得這我們很重吧。可是,牠們在精神上卻因支撐神體的榮耀,而感到生命充滿了意義呢。調查牠們的腦波就會發現,當我們坐在牠們身上,幾乎要壓斷牠們的手骨時,幸福感的曲線反而飆高。肉體的苦痛正比於牠們所得到的精神幸福感……只要知道了這點,相信大家的慈畜心都能得到滿足吧?慈畜主義運動正是用信仰去拯救鴉俘,讓牠們能夠樂於侍奉人類;鴉俘們的工作效率上升,只是單純的正面副作用啊。」
安娜・泰勒斯的慈畜主義(註:原文作チャリテイズム。爲「慈善」(チャリティー、charity)與「思想、主張」(イズム、-ism)的合併語,為沼正三所原創。)
四肢伏地、蜷縮著手足趴在寶琳旁邊,身下有著紫色滑雪板的雪上畜突然開始顫抖了起來。
「看來是想要早點讓我搭上去呢?」寶琳一口喝乾杯子裡的靈液,將杯子交給飄在一旁的畜童之後,叼起一根煙草:「看牠都興奮得發抖了。」
另外一隻畜童從上方飛近,頭下腳上地幫這位女貴客叼著的菸草點火——摩擦手指就能點火,這裡面到底有怎樣的機關啊?
「這也是沒辦法的嘛。」愛喝蘇摩到了一...
推薦序
畜權神授說~沼正三《家畜人鴉俘》與日本神話的解構(節錄)
隱姓埋名,筆耕不輟的作家們。
為什麼要隱遁、又為什麼不現身,這並沒有一定的答案;這些匿名作家的意識形態隨著時代而不同,可想而知,自我認同和匿蹤的理由也千差萬別。例如十九世紀中葉,美國便有一位隱遁詩人埃米莉・狄更生,而在現代,則有例如J‧D‧沙林傑與湯瑪斯‧品瓊。而在這當中,也有諸如後品瓊的代表性作家—約翰‧加爾文‧巴切拉(John calvin Batchelor)之類,曾經高聲主張「品瓊就是沙林傑的別名」般,這種身分隱匿,往往會直接導致身分的混亂。
不過,也並不是所有的匿名作家都樂於見到這種混亂。
例如小詹姆斯‧提普奇這個筆名,便是一名女性匿名作家藉由男性筆名的這個「身分」來得到寫作的自由;匿名作家正是因為「不存在」這個修辭,才能寫出品質極高且極富想像力與批判性的作品,並將它們呈現在大眾眼前。
而當考慮到這裡時,我不由得想起兩段內容,而這似乎顯示了身為匿名作家總有一種文化上的暗合。第一個是一九九○年,美國後設小說的巨匠品瓊所發表的第四個長篇《葡萄園》:在該故事中,美國有一個以白人女性為主要成員的女性主義部隊「九之一集團」,使用像是在《北斗神拳》中的必殺技,先讓一名日本男性陷入了假死狀態,之後再將藉由她們的東洋針灸機械「判灸機」,把這名叫做Takeshi Fumimota的日本人洗腦成女性主義者。借品瓊自己的說法來看,這是對他之前所寫作的、有關陰莖象徵的人造人小說《萬有引力之虹》以現在的視點進行補完,也是一種具備去勢主義的女性主義生化實驗。不過這種劇情上的構圖,或者該說其文脈非常地日本,給人一種相當濃厚的既視感。這段劇情的主要成分,看起來只像是在描寫六○年代後期被女性虐待的男性,但是只要稍微把角度偏移,我們就會看到被美國人所欺侮的日本人—換個說法,這段劇情直接反映了一九八○年代的美國的人種政治學。
是的,這個橋段確實可以看做是「重擊日本」(Japan Bashing)的一環。而當我想到這裡時,我腦海中浮現了另外一與之跨海互相默默呼應的作品—那是一部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前,並不出現在盎格魯美洲,而是出現在我國的作品,其內容同樣徹徹底底地描寫了白人女性對於日本男性的洗腦、飼育、家畜化—那就是另外一位隱匿作家‧沼正三的長篇小說,《家畜人鴉俘》(於《奇譚俱樂部》1956年12月號開始連載,1970年由都市出版社出版,1972年收入角川文庫版。)
《家畜人》筆下的世界是位於四十世紀的未來世界。在那裡,白人女性握有霸權,黑人被當作奴隸,至於日本人,則是家畜和家具的活體材料。這篇小說自出現以來,各界便以「SM小說」或「變態性欲小說」的身分來加以評斷。此一看法並不一定失準,但從現代的視角來看,相反地,它是一部實驗性質的小說,一方面解構《古事記》為首的日本神話,另一方面也同時以其文本的前提,反轉人種、性別與階級,是篇足以提出新的歷史觀的文本。而此文本出現當時,以三島由紀夫和澀澤龍彥為首的少數讀書家便已經對其本質有相當深刻的了解,這點也不容忽視。
例如在一九七○年代《家畜人》初版出版的時候,石川喬司便已對其壓倒性的衝擊做出了以下的敘述:「當要選出SF的前十名作時,這本夢幻的名作總會被提起,總是被說『你們沒有忘了更厲害的作品嗎?』……(中略)……作為一本SF、也是黑色幽默的傑作,它可以得到相當高的評價;在這之前,有任何人的SF作品描繪出更加獵奇且又具有魅力的未來社會嗎?」(《SF的時代》,三三七~三三八頁)。
而奧野健男於初版的解說以外,又在自由國民社的《世界科幻文學總解說》初版,《家畜人鴉俘》的項目中給出了以下的評語:「作者將他真正的目標用科幻小說這個框架隱藏起來,在以那自由自在的訊息來給予一個毫無方法預測的逸脫和放浪。作者將那人性中不可解的倒錯如萬花筒般散射,並將其內心那翻騰不止的反現實主義、反烏托邦的焰火噴吐而出……這本書確實值得稱為『奇書』、『怪作』。」(一二〇頁)
在那之後,過了三十多年。
《家畜人鴉俘》做為文本,看起來已經被埋入了非主流文學史的深淵。但,無巧不成書地,恰似在反映八零年代的「重擊日本」潮流般,品瓊發表了《葡萄園》;同時,沼正三也正在振筆疾書《家畜人鴉俘》的最終篇,而它同樣也是一篇浸淫於八○年代的意識形態的作品。
也因此,再次讀完了《家畜人鴉俘》的我,還沒來得及喘口氣,就跟《家畜人鴉俘》的完結篇撞上了。
Ⅰ 匿名作家的行為表述(performative)
如果要討論《家畜人鴉俘》的話,顯然我們不能避開「匿名作家」這個「醜聞」。
論其主因,或許可以從跟美國比起來,日本的「匿名作家」這種「不存之存」,可說極端地往「不存」偏近這個現狀有關。前述的品瓊的「真實身分」是麻省理工的學者啦、或是J‧D‧沙林傑啦這類的「騷動」,說穿了就只是他的作品的狂熱讀者間的笑話—但沼正三的狀況,就與作品的本質差不多無關了。三島由紀夫與伊薩亞‧弁德桑(Isaiah Ben-Dasan)探索真相,而最後就成了媒體主導的一曲瘋狂的狂想曲。而就在這差不多等於〈竹林中〉(yabu-nonaka),不,我們可以說,在〈鴉俘中〉(yapoo-nonaka)撲朔迷離的劇情中,大家開始強烈推測東京最高法院的法官K先生(譯註:即倉田卓次,東京高等裁判所的法官。(1922-2011))。才是沼正三;而與之相對地,沼正三的代理人天野哲夫則出來宣稱「我才是沼正三」,並表示自己跟K先生間的關係是「大人間的遊戲」。當然,這個聲明並沒有辦法為這個「活動」一錘定音──相反地,正因為沒有人能夠斷言,所以天野哲夫將這件事直接用一句「大人間的遊戲」收場的行動,其本身才是「大人間的遊戲」。說得簡單一點,「我才是沼正三」這個聲明,就跟福樓拜說「我才是包法利夫人」一樣—沒人能夠證明這句話不是一個誇飾法。(引自森下小太郎刊登於《諸君》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二月號的短文,還有天野哲夫於《潮》一九八三年一月號的短文)。
當然,筆者對於這件事並沒有比媒體更加熱中於追尋真相;畢竟看到沼正三指出:「後記亦是小說的一部分,也是其延長」(角川書店刊限定愛藏版,一九八四年)的時候,我開始思考,這種「隱遁」是否也是沼正三的修辭的一部分、或是在其延長線上呢?繼續引用《葡萄園》中的例子,裡面提到了「西新宿的希爾頓國際會館」,其實這也是一種只有當作者是匿名作家時才能使用的修辭法—我們雖然已經對各種東方主義式的描寫見怪不怪,但在這個新都廳還在建設的時間點,從外國人筆下出現「西新宿」這個字眼,自然會開始推測,或者該說夢想諸如品瓊是不是其實來過日本,或是其實他搞不好根本就住在日本。而另外一位匿名作家沼正三也是把這種「不存之存、存而不存」的事實構織進他的作品裡;這是個讓作者和讀者的想像力都能無盡翱翔的巨大機關。
—巽孝之
畜權神授說~沼正三《家畜人鴉俘》與日本神話的解構(節錄)
隱姓埋名,筆耕不輟的作家們。
為什麼要隱遁、又為什麼不現身,這並沒有一定的答案;這些匿名作家的意識形態隨著時代而不同,可想而知,自我認同和匿蹤的理由也千差萬別。例如十九世紀中葉,美國便有一位隱遁詩人埃米莉・狄更生,而在現代,則有例如J‧D‧沙林傑與湯瑪斯‧品瓊。而在這當中,也有諸如後品瓊的代表性作家—約翰‧加爾文‧巴切拉(John calvin Batchelor)之類,曾經高聲主張「品瓊就是沙林傑的別名」般,這種身分隱匿,往往會直接導致身分的混亂。
不過,也並不是...
目錄
第一章 於遊仙窟
第二章 往狩獵場
第三章 矮人之死、黑奴之死
第四章 等待降臨的人們
第五章 降臨富士山
第六章 子宮畜選拔
第七章 瑤臺之宴
第八章 瑤池湖畔
第九章 兩個小盒
第十章 黑奴酒酒吧
第一章 於遊仙窟
第二章 往狩獵場
第三章 矮人之死、黑奴之死
第四章 等待降臨的人們
第五章 降臨富士山
第六章 子宮畜選拔
第七章 瑤臺之宴
第八章 瑤池湖畔
第九章 兩個小盒
第十章 黑奴酒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