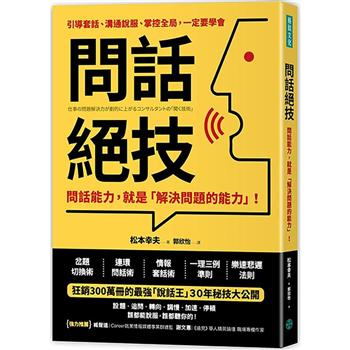系列總導讀
劃破黑霧的筆鋒─松本清張
排版印刷室充滿著油墨味,那是一種陳腐、悶鼻的味道。許多撿字工人、排版工人,雙手、圍兜上都是油墨,他們動作熟練,從一個個檜木做的,已經被油墨染成黑鴉鴉木頭格子裡快速辨認各種大小不同的字,一個接著一個快速挑出來,疊放在另一個平放的框框裡組成一篇篇文章。他們沒有人說話,時間很趕,動作敏捷,面無表情地持續做著這個沉悶、無趣、機械式的動作。 在排版室裡,有一位四十歲的資深員工,名叫松本清張,他從撿字工作幹起,通過多年的考驗,現在已經是位可靠的排版美編兼廣告業務,白天他偶爾還要出去拉廣告,賺點傭金。
松本清張好不容易找到這份工作,這份穩定的收入對他養家活口太重要了,他認份盡職的在排版室,一待多年,安份守己,就如同多年前他賣掃把時一樣,兢兢業業。只是在這樣傭碌的排版室,沒人會注意這個中年人的世故老成,也不會有人注意到這個下層社會的人,有一雙比一般人更為犀利的眼神。
一九五二年的某一天,在日本以挖掘純文學新人著名的芥川賞獲獎名單上,赫然出現松本清張的名字。當編輯部的編輯記者們知道,這位松本清張就是在他們樓底下排版室工作的傢伙時,大家驚呆了。但真的就是樓下那個傢伙。
得獎後數年,就在大家幾乎要把松本清張四個字忘記時,他突然背著一種很奇怪的小說文體再現文壇,驚人的是他的寫作像小說工廠一樣頻頻在各種雜誌上連載,一年出版好幾部小說,從印刷廠送上書店,一上架就銷售完畢,再上架又銷完。他的寫作像火山爆發一樣,熱岩漿不免燙傷了一些人,社會震撼。
在昭和前期,軍閥控制日本,社會氣氛肅穆,大家有話不敢講,有權有勢的人為非做歹老百姓不敢批評,不敢講良心話。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美軍的促進下,推動了日本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的各種改革。
戰後的世界對日本平民是天翻地覆的變化:日本新憲法保障國民基本的人權,美軍下令讓那些軍國主義思想的人從言論陣地的位置下台,給予社會更多的言論自由。 美軍還破除了原來的金權結構,解散舊財閥,進行土地改革,解散國家主義團體,恢復工會,恢復政黨活動自由,設立勞動法,保障工人,一夕之間好像人人都有更公平的機會了。舊秩序崩塌,新秩序在混亂中逐漸成形,但原來舊權勢的人物只是不在台面上,他們下了台,仍然佔據社會的金字塔頂端,與國家機器的運作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處在這種時代變局下的松本清張,獲得全新的機會。他蟄伏四年後,找到一種新的語言新的題材來表達他對社會的看法……幾乎是每年最少一到二部的速度在創作,他為各家報紙、雜誌所寫的稿也不盡其數,他像這個時期的其他作家一樣,是把當下社會的矛盾關係拉進小說裡,反映其扭曲邪惡的關係,藉而批評社會的不公不義。在松本清張描述中,社會上的邪惡,大多是有權有勢的人心生歹念,不仁不義;或者向社會更高階梯上攀爬的人為求成功不惜為惡,但罪魁禍首是社會制度,是社會制度喚醒了人們沉睡中的惡念,孕育了人間的不幸。
二戰結束後,許多日本作家投身反省日本社會的文學創作活動。後來得到諾貝爾文學獎,與他們同時代的純文學作家大江健三郞這樣描述戰後作家群:
「在近代日本文學的歷史中,最富赤忱和使命感的就是那群戰後作家,他們在戰爭一結束後就立刻嶄露頭角,雖然背負戰敗的創傷但仍渴望新生。他們力圖為日本軍隊在其他亞洲國家所犯下的殘忍暴行贖罪,並努力消弭日本與西方國家間,甚是與非洲、拉丁美洲間的鴻溝。他們認為只有這麼做才能謙卑地與其他國家和解。而堅守這些作家們流傳下來的傳統文學精神,是我寫作生涯裡不戀的志向。」
大學念到二年級就被戰爭中斷學業的山崎豐子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她說:「身為作家,我若失去勇氣不寫出應該寫的故事,那麼就等於我已死去。」她寫下對映大學醫學問題的《白色巨塔》、反映了金融問題的《華麗一族》,後來為了掙脫戰爭陰影追尋靈魂自由,又寫了三部曲:講述流放西伯利亞日本戰俘的《不毛地帶》、講述日裔美國人的《兩個祖國》、以及講述東北日本遺留兒的《大地之子》。對她來說這都是不能不說的作家使命。
山崎豐子寫了司馬遼太郎不敢觸碰的時期。司馬遼太郎關注的是幕府末期和明治維新,新舊時代交替,在新潮與守舊觀念強烈碰撞下人物的掙扎與抉擇。他感受到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人的欣興氣象,但他走到了日俄戰爭,就走不下去了。在一八九四年日本打敗中國成為「第二流的文明國」,一九○四年打敗了哥蕯克騎兵和俄羅斯艦隊成為「第一流的文明國」,之後日本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司馬遼太郎著迷日俄戰爭之前的明治維新時代給日本帶來的新氣象。
不同於司馬史觀,松本清張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審美趣味是另一種樣貌。他讓日本讀者讀到的故事,不總是那樣令人愉悅、充滿積極向上的氣質。也不特別覺得明治時代好,昭和時代壞。相反的,由於松本清張幾乎打從一生下來,就處於為生存而戰的境況下,統治者和努力向社會階層更高處爬的人並不總是那麼美好,競爭讓每個人都可能在一個壞的時代壞的制度下成為陰暗的壞蛋。松本清張進了新聞界,但不能如願當記者,因此他的許多小說具有調查報導的氣質,好像他在對記者生涯遺憾的一償宿願。在壞傢伙們裡,他揭露醫院高層的惡行,在《日本之黑霧》中,他又像調查記者一樣揭發駐日盟軍總部掩蓋事件的方式。
山崎豐子說,筆是作家的配劍。松本清張用這枝筆當作武器去挑戰國家與社會的謊言。以前他不能以記者的身份秉春秋之筆去揭露時弊。現在松本清張成了小說家,發現自己小說家的筆更強大。小說家可以隱身在虛構的背後去挑戰和顛覆真實。小說可以說是用許多真實建立的謊言,但這個謊言可能影射真實,而且比不完整的真相更有力道。作家生涯他一路秉持這個信念寫下去,陸陸續續寫七百五十多本著作,署名文章九百八十篇,加上推薦序則破千篇,稿紙用去十二萬張,他把手都寫受傷了。據聞到最後十年,他的創作甚至是口述讓人抄錄(國學大師錢穆也是如此)。他寫當代社會,寫非小說類的紀實文學、寫報導文學、對昭和史的挖掘也有超過小說家的水平。
他用一枝筆追尋真相的興趣漫延到歷史領域。不同於司馬遼太郎專注在幕末和明治時期,松本清張對大正末到昭和十一年以及古代史的歷史挖掘投入相當的心力。文春文庫二○○五年出版了他昭和史挖掘的著作多達九卷,其中包括了陸軍機密費問題、滿洲事變、陸軍士官學校事件、和最重要的少壯派軍官向特權階級發起軍事政變的二二六事件,這些都是昭和前期一般民眾無法知道的國家密秘。除了昭和史外,他還以業餘史家的身份對日本古代史進行研究,使日本皇室的身世遭到質疑。天皇與日本社會的血統聯繫是明治以來,日本建構國族神化,征韓、抗俄,戰爭動員的重要倫理。松本清張意圖從根本上顛覆這個國家機器的運作邏輯,可見其視野、雄心、與膽識。松本的史觀是一種日本平民史觀,他用三十多的寫作生涯,展現了平民去建構歷史挖掘真相的勇氣,對抗可疑的國家建構的歷史。這過程當中,人們可以見到他的一股怨氣,對特權、對貧困、對充斥虛假人格的上流社會的韃伐。
從更大的視野來看松本清張,推理小說不過是他建構歷史的一種方法,是他一生追求平民視角的公理和真相的一種工具。他太過龐大,以推理小說定位他可能是出版社和他之間的一種商業考量,正如同今日我們定位某某人為青春玉女或是豪放女一樣,是為了銷售。而松本清張本身並不反對商業手法,相反的他熟諳商業邏輯,不要忘了,他的前半生都在商業世界中打滾掙扎,在追求正義與真相的另一面,他沒有侷限造作的文人氣。他的寫作兼顧了為求生存的原始根性,就像平凡的日本民眾那樣充滿驚人的勤奮勞作。
有人就問,為什麼一個平凡的人可以寫出這麼多的不同知識和題材的文章?松本清張可能是以寫作團隊形式出版的創始人吧。據一位當年出版社的編輯回憶,松本清張的寫作不全是孤獨的創作,他會與編輯討論適合市場的題材,甚至到內容的蒐集,都有專業知識者的合作,提供編輯資源和協助,可以說是一個完全產業式的俱有工廠生產力的創作方式。這種生產模式也見到了作用: 松本清張的寫作甚至帶動了娛樂產業,大眾媒體的市場,他的作品不斷被改編成電視、電影、戲劇。直到今天,松本清張逝世二十多年,每一年都還有他的作品持續被改編。這個作家的許多面都超越我們的想像。
◎譚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