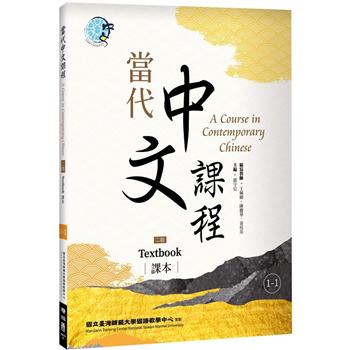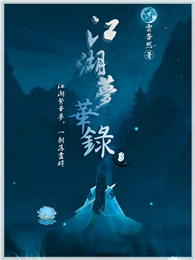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石黑一雄揚名文壇的出道之作
榮獲英國皇家協會霍爾比紀念獎(Winifred Holtby Memorial Prize)
「日本記憶」名作
全新譯本
時空跨越二十年,一對飽經磨難而渴慕安穩與重生的母女──在闇昧的記憶與敘事中,如一抹淡影朦朧掩映。
理想的嚮往與追求無非是一場渺茫的夢;舊價值終將迎來無情的挑戰;自欺徒然招致內心最深沉的疚痛。那些男女,不分老少,都懸浮在真空的表面,像一群跳著凌波舞的迷失靈魂。
生意盎然的英國田園,戰後殘垣斷壁的長崎街道;安逸與毀壞的鮮明對比,正是寡婦悅子的現在與過去。
悅子與久未見面的女兒妮姬,因長女惠子的自盡而重聚。在閃爍模糊的對話中,悅子逐漸憶起二戰後在長崎的往事;謎樣女人幸子和她女兒真理子,與她們謎一般的街屋住處;前夫次郎和公公緒方,既不切中核心又無法交集的對話。像一盤勝負未決而一方卻已棄守的棋局。
作者簡介: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日裔英籍小說家。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八日生於日本長崎市,一九六○年,父親赴英國國家海洋學院從事研究,舉家遷居英國。大學時代,石黑一雄進入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就讀,主修英文和哲學,畢業後赴東英吉利大學(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攻讀創意寫作學位,當時即練就細膩優雅的獨特文風。年輕時,尚未以作家為業的石黑一雄曾短暫投入社福工作,小說作品如今已被翻譯超過三十種語言,他以「國際主義作家」自居,由於移民作家的特殊身分,並與另兩位印度裔小說家維迪亞德哈爾.奈波爾(V. S. Naipaul)、薩魯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稱「英國文壇移民三雄」。論者以為石黑一雄是亞裔作家中,少數不以移民背景或文化差異作為主要創作題材的作者,「移民身分」正是石黑一雄作品最隱晦且不被置諸題旨的「反高潮」,其作品不刻意操作亞裔的族群認同,往往關懷普遍的人情、感性經驗與個體的孤獨景況,深沉的特質使他被英國《衛報》評論為「最近乎卡夫卡小說世界」的當代作家。一九九五年,因為對文學的卓越貢獻,獲英國皇室頒發文學騎士勛章(官佐勛章,簡稱OBE);一九九八年獲授法國藝術暨文學騎士勛章(Ordre des Arts et des Lettres),現為英國皇家文學會研究員,與其妻女定居於倫敦。迄今石黑一雄有七部長篇小說:一九八二年《群山淡景》獲「英國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溫尼弗雷德.霍爾比獎(Winifred Holtby Prize);一九八六年《浮世畫家》獲英國曁愛爾蘭圖書協會(Booksellers Association of the UK and Ireland)頒發「惠特布萊德」年度最佳小說獎(Whitbread Book of the Year Award),並獲英國布克獎(Booker Prize)提名;一九八九年《長日將盡》獲英國布克獎,並登上《出版家週刊》年度暢銷榜書單;一九九五年《無可撫慰》贏得「契爾特納姆」文學藝術獎(Cheltenham Prize);二○○○年《我輩孤雛》入圍布克獎提名;二○○五年《別讓我走》入圍曼布克獎(Man Booker Prize)最後決選名單,並獲「歐洲小說獎」(European Novel Award)。二○○五年出版睽違十年的長篇新作《被掩埋的巨人》。
譯者簡介:
林為正
中山大學外文所碩士,英國華威大學翻譯研究博士,曾事師余光中教授及蘇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教授,現任教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學術興趣在於詩歌、詩歌翻譯、翻譯理論,教授課程包括大學及研究所之各類翻譯實務及理論、中西詩歌、西洋文學概論、英文作文、英語聽講實習等等;曾為梁實秋譯詩獎、譯文獎及散文創作獎得主,《聯合晚報》副刊之每日一譯專欄譯者及影評、雜文之邀稿作家,譯作三十餘種含文學、大眾文化作品,含路益師(C. S. Lewis)之《四種愛》、希美內思(J.R. Jimenez)之《小毛驢與我》、石黑一雄之《我輩孤雛》、《群山淡影》、西斯奈洛斯(S. Cisneros)之《家住芒果街》以及陳克華詩集之英譯等等近三十種。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他把故事說得這樣動聽,這樣貼近個人的私密世界,同時又具有西方小說少見的情感昇華、尋求和解的善良,和慈悲。從《群山淡影》出發,以至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石黑一雄無疑為文學找到了至高的淑世使命和恢宏視野。」——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副教授 蘇榕
「《群山淡影》這個作品有種豁達,有種思念,有種執著,有種深陷黑暗深淵的恐懼,有種對社會對歷史心懷關注,還有種種身不由己既殘酷又時而暖入人心的萬般滋味。」—— 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蕭幸君
「悚然而佈局完美的謎團。」——《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
「原創且非凡的天才。」——《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精美,諷刺,晦澀的小說……它的人物非常生動而具說服力……但我們會記得的是它在哀歌和諷諭之間的微妙平衡。」——《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名人推薦:「他把故事說得這樣動聽,這樣貼近個人的私密世界,同時又具有西方小說少見的情感昇華、尋求和解的善良,和慈悲。從《群山淡影》出發,以至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石黑一雄無疑為文學找到了至高的淑世使命和恢宏視野。」——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副教授 蘇榕
「《群山淡影》這個作品有種豁達,有種思念,有種執著,有種深陷黑暗深淵的恐懼,有種對社會對歷史心懷關注,還有種種身不由己既殘酷又時而暖入人心的萬般滋味。」—— 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蕭幸君
「悚然而佈局完美的謎團。」——《英國星期日泰晤士...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妮姬是我跟丈夫最後給女兒取的名字,那可不是哪個名字的簡稱;是我跟她父親各讓一步的結果。這事說來弔詭,她父親想給她取日文名字,而想給她取個英文名字的人,反而是我—也許是出自私心吧,不希望過去老是被勾起。最後他接受妮姬,覺得其中隱約有東方色彩。
今年她的訪期提早了些,在四月,天氣依然寒冷而陰雨綿綿。也許她原本打算待得更久,我不敢說。但是我的鄉居與其寂靜的環境讓她悶得慌,沒多久我就看出她急著想返回她倫敦的生活。她不耐煩地聽我的古典唱片,雜誌一本本翻翻就放下。打給她的電話不曾停過,她大步走過地毯,削瘦的身形包裹著緊身裝扮,還留心把門關上,好讓我聽不到談話內容。五天後她就回去了。
她到的第二天才提起惠子。那是個陰天多風的早晨,我們把扶手椅挪近窗戶,好欣賞我花園的雨中景緻。
「上次妳有沒有期待我會來?」她問,「我是指來葬禮。」
「恐怕沒有。我並不認為妳會來。」
「聽到她的事,讓我好難過。我幾乎要動身。」
「我根本沒期望妳來。」
「別人不明白我有什麼問題,」她說,「我也沒跟誰提起。我想我是怕尷尬。他們不會了解的,真的,他們不會了解我對這件事的感受。姊妹本該關係親密,不是嗎?你未必很喜歡她們,但是親還是親。不過實情就不是這個樣子。現在我連她的長相都想不起來了。」
「也是,妳上次與她見面,已經有一段日子了。」
「我只記得她就是讓我日子難過的人。我就記得她這點。不過聽到她出事,我當下還是傷心難過。」
也許讓我女兒受不了而返回倫敦的,不是寂靜。因為儘管我們談到惠子的死,都點到為止,該事卻不曾遠離,每次聊天都徘徊在話題左右。
惠子不像妮姬,惠子是純日本人,不只一家報紙立刻逮住這點來作文章。英國人的腦子裡,喜歡把我們日本人想成有自殺本能的民族,彷彿沒必要再深入探究;他們就只報導這點,她是日本人,所以她會在自己房間裡上吊自殺。
那一天晚上,我站在窗前,向外望著夜色,我聽到妮姬在我身後對我說,「母親,妳現在在想什麼?」她坐在沙發另一頭,膝上有本平裝書。
「我在想我以前認識的一個人。我曾認識的一位女士。」
「妳認識她的時候,妳……還沒來英格蘭?」
「我住長崎的時候認識她,妳問的是這個罷?」她還是望著我看,所以我補充一點:「好久好久以前囉。遠早於遇到妳父親。」
她似乎明白了,咕噥兩句回應就繼續看她的書。妮姬在好多方面,是個貼心的女兒。她來探望我,不只是關心我聽到惠子的死訊能不能承受;她來探望我也是出自一種使命感。因為近年來,她決定她有義務欣賞我過去的某些層面,她來訪正是有心要告訴我,無論過去種種如何,都會走到今天這個局面,我對我當年做的那些抉擇應該完全不必後悔。簡言之,就是要跟我保證,惠子尋短,不是我的錯。
現在我也不太想老是談惠子,再談也幾無慰藉。我在這裡提到她,只因為那剛好是妮姬四月來訪那陣子時的事情,也是因為就在她來訪期間,多年不曾想起的幸子,又浮上心頭。我跟幸子根本不曾熟識。老實說,我們結識為友的時間,只有許多年前某個夏天的幾週而已。
當時最慘澹日子已經過了。美國軍人卻還是跟以前一樣多—因為韓國有戰事—但是在長崎,經歷了之前的戰禍,那段日子算是平靜、自在。世界有種思變的氣氛。
我丈夫與我住在城市東邊的區域,搭一段電車就可以到市中心。我家附近有條河,我聽說在戰前,河邊曾經窩著一座小村落。不過原子彈投擲後,一切只剩焦墟。重建早已開始,到那時,四棟水泥建築已拔地而起,每棟約有四十戶獨立公寓。四者之中我們那棟最晚建,也成為重建計劃的終止點;我們與河流間有一大片荒地,好幾畝的乾泥巴地與溝渠。許多人抱怨那是衞生災難,而其排水的確大有問題。一年到頭,總有積了死水的坑坑洞洞,在夏季月份裡,蚊子簡直教人吃不消。每隔一段時間,總會有政府官員在那裡走動,丈量地形或記錄什麼,不過月復一月,什麼行動也沒有。
住宅大樓的住戶與我們大同小異—年輕夫妻,而丈夫受聘於擴張中的公司。許多戶也被這些公司買下,再以優惠的房租租給員工。每戶格局都相同;地板是榻榻米,浴室廚房則是西式設計。房子不大,溫暖的季節也不易保持涼爽,不過住戶大體都還算滿意。然而我記得那裡的氣氛,讓人清清楚楚感覺那並非久留之地,彷彿我們都等待有一天能搬到更好的地方。
有棟木造村屋逃過戰爭與政府推土機的摧殘,我從我家窗戶就能看到,孤伶伶站在那一大片荒地的另一邊,直逼河畔。是鄉下常見的那種村屋,斜式瓦片屋頂直接垂到接近地面。在我空閒時,我會到窗邊加以端詳。
從幸子搬進去所引起的騷動來看,顯然不止我在盯那棟村屋。許多人說有兩個男人某天在那裡整理什麼—也許是政府人員。後來有人說,有個女人帶著一個小女孩住在那裡,而我自己也好幾次看到她們找路通過那片坑坑洞洞的荒原。
我第一次看到那輛美國大車是初夏時節,當時我懷孕約三四個月,一輛破舊的白車,蹣跚開過那片荒原前往河邊。當時已近入夜,屋後落日在金屬車體上的餘暉僅留片刻。
後來有個下午,我在電車亭聽到兩個婦人聊天,談那個搬進河邊棄屋的女人。一個對她的同伴解釋,她某天早上想跟那個女人搭訕卻明顯換來白眼。她的同伴附和說,這個新居民的確不友善—也許是自大吧。她至少也有三十了,而那孩子十歲。先開口的那個說這個陌生人操東京的方言,顯然不是長崎人。她們八卦了一會兒那個「美國朋友」,接著她又再提起這個陌生人那天早上對她有多麼不友善。
如今我清楚了解當時左鄰右舍的婦女中,有些身受苦難,有些心裡藏著悲傷慘痛的回憶。但日日觀察她們忙碌於照料丈夫子女,我覺得這點難以相信—我是指她們的人生曾經歷戰爭的悲劇與惡夢。我絕沒有意思要給她們冷漠臉色看,但實情是,我恐怕也沒有特別花力氣去迎合她們。因為在我人生的那個階段,我仍寧可獨處。
因此側聽那些婦女聊幸子,我是有幾分好奇。我能清楚想起在電車亭的那天下午。那是六月雨季後再度放晴裡的某一天,我們四周的磚塊水泥,原先濕透的表面,都漸漸乾了。我們站在鐵道橋上,在鐵軌一側的山腳下,可見一片屋頂聚集,彷彿房子滾下山坡了。往那些房屋望去,不遠處便是我們家公寓所在的幾棟大樓,矗立如四根水泥柱。我當時有點同情幸子,我曾在遠處看過她的樣子,注意到那種岸然冷漠的神情,我覺得自己多少理解。
那年夏天我們成為朋友,而且至少有一段短暫的時日,她對我推心置腹。如今我不太清楚我們最初是怎麼開始的。我記得有天下午,我在通往我們住宅那區的路上,看到她的身影走在我前方。我急著趕路,幸子則步伐平穩。到那個時候,我們一定早已知道對方的名字,因為我記得靠近她時叫住了她。
幸子轉身等我趕上。「一切還好嗎?」
「還好我找到您,」我說,有點喘不過氣。「令嬡,我出門時看到她跟人打架。就在那邊,靠近坑坑洞洞那區。」
「她,打架?」
「跟另外兩個小孩。其中一個是男孩。看起來打得很兇。」
「明白了。」幸子又開始前行。我隨行其側。
「我不想讓您擔心,」我說,「不過看起來打得有點太兇。還有,我看到令嬡臉頰上有個傷口。」
「明白了。」
「就在那邊,那片荒地的邊上。」
「您覺得,他們現在還在打嗎?」她腳步不停往丘頂走去。
「呃,是停了。我看見令嬡跑開了。」
幸子看著我,面露微笑。「妳不常看到小孩子打架吧?」
「這個嘛,我猜孩子們難免會打架。只不過我覺得我該告訴您一聲。更何況她並沒有往學校的方向走去。其他兩個繼續走上學的路,但令嬡回頭往河邊走。」
幸子沒有回答,腳步不停往丘頂走去。
「老實說,」我繼續說,「我先前就想跟您提這一件事。是這樣子,最近我有好幾次看到令嬡。我擔心,她也許偶而也會逃學。」
路在丘頂分道揚鑣。幸子停下來,我們轉向彼此。
「您這麼關心,真是好心腸,悅子。」她說,「真是好心腸。我相信您會是一個出色的好母親。」
在此之前—就像電車亭那些三姑六婆一樣—也猜想幸子應該是三十上下。不過她年輕的身材會讓人錯估,因為她的容貌看來不止這個歲數。她帶著淺笑盯著我看,似乎認為我少見多怪,我自覺唐突,只好笑一笑解圍。
「您這樣專程來通知我,真是感激不盡,」她繼續說。「不過也請包涵,我現在有急事在身。必須進長崎去。」
「了解。我不過是覺得還是跟您說一聲才好,如此而已。」
有那麼一會兒,她只是以那種笑容對我著看。接著她說,「承蒙關照了。恕我失禮,我得馬上進城。」她鞠躬,轉身踏上通往電車亭的路。
「只不過她臉上有道傷口,」我略微提高音量。「而河邊有些地方相當危險。我覺得我最好還是來告訴您一下。」
她轉身,再度望著我看。「假如您沒有什麼別的事要忙的話,悅子,」她說,「也許您不介意今天幫我照顧一下我女兒。我下午就回來。我相信您跟她會很投緣的。」
「假如這是您的意思,我也不反對。容我指出,令嬡似乎相當年幼,不該整天獨處。」
「您真是好心,」幸子又說了。接著她又微笑。「沒錯,我確定妳會是個好母親。」
與幸子分開後,我往下坡走回頭路,穿過住宅區。不一會我就到了自己的公寓大樓外,面對著那一大片荒地。我沒看到小女孩的蹤影,打算上樓去,就在那時我瞥見河堤上有動靜。真理子原先一定是蹲著,現在我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她嬌小的身形,就在那片泥濘空地的另一邊。起先我有點衝動想忘了這整件事,回家處理家務。然而我終究開始找路走向她,小心躲開溝渠。 就我記憶所及,這是我第一次與真理子說話。她的行為八成也沒什麼不尋常的地方,因為我對這個孩子而言畢竟是陌生人,她絕對有權懷疑我。即使我當時心頭確實感到不安,但也說不出所以然,可能只是單純回應真理子的舉止而已。
那天早上河水水位依然高漲,從幾週前的雨季以來水就流得湍急。地面近河就陡降,直到水邊,而坡底小女孩所站立的泥巴明顯更加潮濕。真理子身著簡單棉布及膝連身裝,而她的整齊短髮讓她容貌有男孩子氣。她抬頭望著站在泥巴坡頂的我,沒有笑容。
「嗨,」我說,「我剛與您母親說話。您一定是真理子小姐。」 小女孩依然盯著我,一言不發。我原先以為她臉上有個傷口,如今再看應是一抹泥痕。 「您怎麼沒上學去呢?」我問。
她有一會兒閉口不言。接著她說,「我沒上學。」
「可是所有小朋友都應該上學,難道您不喜歡?」
「我沒上學。」
「難到令堂沒有把您轉進本地的學校?」
真理子並未回答。她反而退一步遠離我。
「小心,」我說,「會跌到河裡。那裡很滑。」
她依然留在坡底,抬頭盯著我。我看到她的小鞋子丟在她身邊的泥地上。她裸露的腳和鞋子,都沾滿泥巴。
第一章
妮姬是我跟丈夫最後給女兒取的名字,那可不是哪個名字的簡稱;是我跟她父親各讓一步的結果。這事說來弔詭,她父親想給她取日文名字,而想給她取個英文名字的人,反而是我—也許是出自私心吧,不希望過去老是被勾起。最後他接受妮姬,覺得其中隱約有東方色彩。
今年她的訪期提早了些,在四月,天氣依然寒冷而陰雨綿綿。也許她原本打算待得更久,我不敢說。但是我的鄉居與其寂靜的環境讓她悶得慌,沒多久我就看出她急著想返回她倫敦的生活。她不耐煩地聽我的古典唱片,雜誌一本本翻翻就放下。打給她的電話不曾停過,她大步走過地毯...
推薦序
《群山淡影》——石黑一雄的微觀歷史和宏觀視野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副教授 蘇榕
石黑一雄是英國文壇難得一見的作家。較諸其他移民作家,石黑一雄的背景、身份、風格可謂獨樹一幟。他的文筆優雅,視野遼闊,既能深入小人物的私歷史,又能見微知著,以個人故事直指歷史問題的核心,兼以幽默口吻反諷當代政治,這樣的寫作風格幾乎貫串了他的所有作品。雖然他從不重複書寫相同的主題,但自從一九八二年出版的《群山淡影》開始,以至於二○一五年出版的《被埋葬的記憶》,他的作品大致都沿著這個脈絡逐步演化,圍繞著記憶、創傷、悲天憫人的人文情懷、人類命運的倫理抉擇等重大議題,娓娓述說個人的傷痛回憶,隱藏在這些個人私密世界背後的往往是人類歷史面臨的重大轉折或危機。這就是石黑一雄的寫作策略和格局:以微觀歷史展現宏觀視野。
石黑一雄出生於長崎—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投下原子彈的兩個日本城市之一。長崎和廣島在原爆中夷為平地,第二次世界大戰於是落幕,留下滿目瘡痍的斷壁殘垣,也在歷經二戰那個世代的日本人心中留下深刻創傷;同時,在歐洲戰場,英國也遭受納粹德軍轟炸,戰後首都放眼望去盡是瓦礫廢墟。其實,在飽受戰爭蹂躪的交戰國中,歷經峰火的整個世代哪個人能倖免於難?石黑一雄在五歲時隨父母從長崎移居到倫敦南方近三十英哩外的薩里郡居爾福德鎮。他的母親生長於長崎,父親和祖父曾在上海工作;石黑一雄本人在一九五四年出生於長崎,那時戰爭雖然已經結束九年,但父母和親人對戰爭的談論和記憶,使他對二次世界大戰留下的陰影難以忘懷。一九六○年他因父親加入英國政府北海研究計畫移居英國,這時英國逐漸從大戰後復甦,嬉皮、反戰、性解放、搖滾樂、學生運動正要興起。石黑一家由軸心國/侵略者/戰敗國,移居到同盟國/抵禦者/戰勝國,處境難免尷尬難堪。但是他在二○一七年十二月七日的諾貝爾文學獎演講辭中提到:當時他們是全鎮唯一非英國白人的家庭,面對來自曾是敵國的外國居民,鎮上社區的平凡居民表現的開放心胸和出自直覺的寬宏大量,使他對歷經二戰那一代的英國人充滿愛、敬意,和好奇。戰爭與和平,始終是隱藏在石黑一雄諸多作品背後的重要主題。人類如何面對邪惡勢力的挑戰,如何發揮人性光輝中的至善,如何在諸多回憶中擇取值得記住的,如何向那些處在邊緣的陌生文化或新文學形式展現開放的胸襟,是石黑一雄在諾貝爾獎演講中反覆申述的呼籲。
這樣的宏大視野早從《群山淡影》就可約略窺見。石黑一雄選擇長崎作為小說的故事背景,一方面除了如他自己所解釋的,為了繪出心中那個「不存在於現實的日本」;另一方面,也透露了他想用隱而不彰的方式,表達對於戰爭的反省。《群山淡影》表面講的是日本寡婦悅子的故事,但是故事的時空背景和人物之間的關係始終和戰爭留下的陰影緊密纏繞。悅子的回憶間接呈現了原子彈爆炸重創長崎對居民身心留下的後遺症。小說人物的對話,更反映了戰爭對人民生活態度和價值觀造成的改變。藤源太太寧可向前看,務實經營她的小麵攤,悅子和幸子則無法滿足現狀,選擇遠走他鄉。緒方先生堅持舊的價值觀,卻被松田重夫的新價值觀所挑戰。這樣以小人物的故事多方表現戰爭造成的世代轉變和價值衝突,以及質疑大眾視為理所當然的觀念,同樣出現在《浮世畫家》、《長日將盡》等作品,直至最新的長篇小說《被埋葬的記憶》。細心的讀者應當可以看到清晰的發展軌跡。《浮世畫家》中的浮世繪畫家小野鱒二在二戰中為軍國主義背書,晚年卻被門生鄙視,他不斷捫心自問:畢生的信仰錯了嗎?《長日將盡》中的管家史蒂文斯為親納粹的達靈頓公爵服務,戰後被眾人唾棄,開始反省何謂「偉大」?畢生奉獻服務業而犧牲愛情錯了嗎?《我輩孤雛》中在中國上海長大的英國偵探克里斯多福反問自己:怎樣才算是個道地的英國人?《別讓我走》中的複製人湯米和凱西向那位神秘的女士追問:我們究竟有沒有權利追求愛情?《被埋葬的記憶》藉古老的魔幻傳奇質問何謂正義?哪些記憶需要保留?被保留的記憶價值何在?衝突的記憶和世仇有無和解的可能?這些大哉問都在他的諾貝爾演說中被反覆強調。然而正如其小說總以開放結局收尾—石黑一雄並未提供明確的答案。或許因為他跨越了立場衝突的兩方,採取迂迴溫和的態度總能避免尷尬尖銳的衝撞。
《群山淡影》標示了石黑一雄寫作生涯的成功起點,儘管起初有些評家認為擇取日本作為寫作題材佔了些異國情調的便宜,隨著他極力追求作品主題的千變萬化,這種論調已成昨日黃花。但是二次大戰對人類命運和價值觀所造成的衝擊和轉變依舊深刻影響了石黑一雄,《群山淡影》預示了他對普世價值被挑戰的省思和憂慮,這包括了《被埋葬的記憶》影射的種種當代病徵,例如他所憂慮的極右保守勢力的抬頭、西方民主制度的民粹化、種族主義的舊瓶新裝、恐怖主義的崛起、意識形態的極端對立等新興現象。石黑一雄在諾貝爾宴演說中特別提到了一個小故事,或許可以作為《群山淡影》以長崎為背景的註腳。他說在五歲時,曾經趴在長崎老家的榻榻米上看一本書,當時母親指著書上的外國人給他看,告訴他,這個人叫做諾貝爾,發明了炸藥,為了紀念和平(heiwa),創立了「諾貝爾賞」(TheNobelSho)。石黑接著又說,這時是長崎被轟炸後的第十四年,他不曾受領過戰火,卻從此知道了和平的重要,也就是在這樣的精神之下,他藉著長崎掌握到和平的重要意義。
在這層意義上,《群山淡影》標示了以個人的私歷史反省戰爭與和平的象徵寓意。表面上看來,整部小說似乎都在訴說悅子個人的悲哀故事,然而,總有那麼一瞬間,石黑一雄忍不住讓他的歷史宏觀、人性關懷,以及對戰爭的批判浮出水面。在小說的第八章,悅子聽從公公緒方先生的建議,搭電車到長崎的和平公園逛逛。在公園裡,她注意到一尊巨大的白色紀念雕像—用來紀念原子彈的罹難者。雕像右手指向天空,左手向左側伸展,暗示擋住邪惡的勢力。石黑一雄這樣描述悅子的觀感:我一直覺得那尊雕像看起來很笨重累贅,我更無法將它和那天發生的事以及之後的可怕日子連結起來。遠看近乎可笑,像警察在指揮交通。我一直覺得它只是尊雕像,雖然多數的長崎人似乎將它視為某種象徵,我懷疑一般人的感覺就和我一樣。透過悅子的感受,石黑一雄表達了對戰爭的嘲諷和大論述的懷疑。閱讀石黑一雄,不妨將《群山淡影》視作他對生命中嚴肅議題一連串詰問的起點。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在一貫而不重複的主題中投注對人類命運和視野的關注。難得的是他把故事說得這樣動聽,這樣貼近個人的私密世界,同時又具有西方小說少見的情感昇華、尋求和解的善良,和慈悲。從《群山淡影》出發,以至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石黑一雄無疑為文學找到了至高的淑世使命和恢宏視野。
遺忘,或者面對:看石黑一雄如何點描封存的「日本」記憶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蕭幸君 ⋯⋯我們該選擇什麼去記憶?什麼時候選擇遺忘並前進才是最好的? —《特急二十世紀之夜與一些小突破》頁六二至六四二○一八年二月十五日,石黑一雄的諾貝爾文學獎演講全文內容以英日對照的方式在日本出版。無論是這份講稿或是NHK獲獎專訪—面對全球廣大的讀者、諾貝爾文學獎相關者乃至針對日本國內的群眾—石黑一雄不忘強調的,就是這份「記憶」的傳承。從他回顧執筆書寫《群山淡影》的長崎開始,這份「記憶」猶如突然襲擊而來的洪水,讓當時年紀尚輕才剛要步入文壇的石黑,甚或有些措手不及因這股不明由來的動力而振筆疾書,書寫的幾個月裡久久斷絕與周遭人們的接觸。他說,在「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年的冬天至緊接而來的春天,除了班上的五位同學、村裡食品雜貨店的老闆跟隔週週末來訪的女友外,我幾乎跟誰都不說一句話。這不算均衡的四、五個月的日子裡,我首部長篇小說《群山淡影》已然完成了一半」。這段時間,除了有關日本的題材以外,他手上仍有幾個短篇的構想卻無論如何都令他提不起興致來寫。那時那個異乎尋常的寫作衝動到底是什麼?「如今回想起來,我所得到的答案是,在我人生中這是一段我急於也必須存留記憶的時期」,石黑如是說。
演講中這長長串聯的寫作記憶,在在點出《群山淡影》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它是石黑崛起文壇的首部長篇小說,更重要的是,它啟動了石黑一雄身為作家的訴求與覺醒,為何而寫?所為何求?痕跡歷歷都盡在這部長篇裡。
而究竟,石黑所要存留的日本「記憶」是什麼?作家交代了,那麼去尋求答案就是讀者們的範疇了。石黑對日本的記憶,在許多評論報導或是導讀裡都曾被提及,五歲之後的離鄉背井,讓石黑必須在自己心靈角落點滴堆砌那個遙遠故國的想像。然而即使在他被自己的念想,推擠催促、心無旁騖專注寫作的當下,即使在他提筆起稿的那段時日裡,不與人語,像是深怕自己小心堆砌的記憶,會消失潰決在不同時空下日常的噓寒問暖裡,石黑明白,他所寫的「日本」早非現實存在的那個,而是想像中的虛構產物,宛如大難不死的恍若隔世或是死者重生後的前世記憶。是的,石黑一雄《群山淡影》中的「日本」,正如大難不死的恍若隔世或是死者重生後的前世記憶。之所以虛實交錯,之所以錯綜複雜,或恬淡或幽玄,風雨過後魂牽夢縈所窺見的景象,即便是破碎斷片堆砌得模糊不清,卻永不失真。為什麼?因為記憶的「真實」,就是那個自己時時惦記著,不肯遺忘,難以遺忘,揮之不去的。因為人們最善於在錯誤百出中的記憶裡保存的,就是那份絕不會失落的「真實」。
然而這聽似簡單的道理,就算身為讀者的我們也多少經歷過這種模糊記憶的體驗,但要寫得不露痕跡又要讓人體會深刻,這是談何容易?要依靠五歲前的記憶以及移居英國之後建構出來的日本想像來摹寫,作家依循的,還是借鏡前輩作家的創作。在朝日新聞書評網站上刊登的書訊〈石黑一雄談「福爾摩斯、谷崎、普魯斯特」〉裡,石黑提到,為他打開日本想像的那扇門的,就是谷崎潤一郎。他看到了谷崎作品中那個獨特的「谷崎的日本」,讓石黑確信他也能寫出屬於自己的日本。細想下來,撰寫《陰翳禮讚》,用光影細膩詮釋日本文化的谷崎潤一郎,不管是在他問鼎文壇的處女作《刺青》,還是寫作風格已臻純熟的《細雪》,他寫的日本都是在面對西洋文化虎視眈眈下逐漸藏蹤匿跡的那一面。更不用說谷崎那些膾炙人口,被稱為「日本回歸」的作品群能如此引人入勝,決不是憑藉引經據典依靠史料文獻的寫實,而是他能化虛為實的無限想像。我私心想,谷崎文學中的這些日本想像,不但激發了石黑日本書寫的信心,也成就了石黑《群山淡影》中這似是而非的「日本」。對日本的讀者來說,這似是而非的「日本」反而令人產生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對台灣的讀者來說,閱讀《群山淡影》的樂趣,自是少不了要來尋尋石黑的「日本」想像,相較之下,也可看看自己對日本又是持有何種想像。
例如《群山淡影》中的人物對話,據說是揣摩日文的感覺之後用英文書寫下來的。負責日文版的翻譯家小野寺就曾回想,原作的英文對話之所以會令人感到十分拗口,就是因為石黑希望讀者能透過文體感受到日本女性對話的感覺。在翻譯人物名字的時候,甚至一度決定不使用漢字,而要直接用英文來呈現。作為台灣的讀者,《群山淡影》暗藏玄機的女性敘事自然是不可錯過的精彩層面,而從中文人名的字面意義來感受人物,不消說這又是別有一番滋味的。對於作家的創作手法持有獨到見解的讀者,相信決不願錯過這可一窺究竟的機會,畢竟小說閱讀的醍醐味都盡在其中。
有人說《群山淡影》通篇瀰漫著薄霧的氛圍,看不清作品中描寫的人事物。的確,那種陷入五里霧中的感覺,雖然不像卻幾次都令我想起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那個同樣活在死者的世界裡糾纏不清的作品。只是這種迷霧滿佈模糊不清的光景,一如小說書名所提示的襯著微光映入眼簾的群山淡影,群山背後透亮的那道光,究竟是象徵希望的光芒,或是核爆閃光之後從佈滿長崎的煙塵瞭望遠山的淡景,這已不得而知。對我這個讀者來說,《群山淡影》這個作品有種豁達、有種思念、有種執著、有種深陷黑暗深淵的恐懼;有種對社會對歷史心懷關注,還有種種身不由己既殘酷又時而暖入人心的萬般滋味。但不可諱言,石黑要寫的「日本」縮影或許就盡在Ogata與其學生的一番對話當中。如果我們延續閱讀石黑其他有關日本書寫的作品,相信讀者一定有機會在這些作品裡發現《群山淡影》Ogata的身影,即便他已經改名換姓,看來面目全非。這種一貫出現在石黑作品中的人物寫照,或許也隱藏著石黑難以放下的執著。
石黑文學的真髓在於它不管描寫的是個人還是家國、科幻或是懸疑虛構的場景,它瞄準的紅心往往就是普世通達的那個一點都不容許妥協的、面對歷史記憶的真誠與正義。他在獲獎感言裡說:……這記憶的重擔是否會落在我們這個世代身上?我們沒有那些戰爭經驗,但我們至少是在這些經歷過這無法抹滅的戰爭經驗的父母親身邊長大的。現今我已成為一個公眾的說故事的人,是否仍有個義務是我不曾察覺的?那個該盡我所能將父母親這一代的記憶與教訓傳達給我們的下一代的,一個傳承的義務?(《特急二十世紀之夜與一些小突破》,頁六四)
這段話聽在台灣讀者耳裡,勾起的肯定是暗地洶湧澎湃不已的萬丈波瀾。小說中那個嚴肅深沉,痛擊長者的口吻,不再是那個針對Ogata所說的,甚或不再是針對日本所說的,也是針對每個生活在歷史延長線上的我們每一個人所說的。到底什麼時候我們可以遺忘?又或者什麼時候我們才能放下?記憶,該遺忘或者面對,石黑似乎已經下定了決心。
石黑一雄在《群山淡影》所佈下的迷霧陷阱裡,我確信已經找到我心中的答案,大家是否也已經找到你/妳的了呢?
無論從哪個觀點來看,《群山淡影》,我都大力推薦。
《群山淡影》——石黑一雄的微觀歷史和宏觀視野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副教授 蘇榕
石黑一雄是英國文壇難得一見的作家。較諸其他移民作家,石黑一雄的背景、身份、風格可謂獨樹一幟。他的文筆優雅,視野遼闊,既能深入小人物的私歷史,又能見微知著,以個人故事直指歷史問題的核心,兼以幽默口吻反諷當代政治,這樣的寫作風格幾乎貫串了他的所有作品。雖然他從不重複書寫相同的主題,但自從一九八二年出版的《群山淡影》開始,以至於二○一五年出版的《被埋葬的記憶》,他的作品大致都沿著這個脈絡逐步演化,圍繞著記憶、創...
目錄
推薦文
《群山淡影》——石黑一雄的微觀歷史和宏觀視野
遺忘,或者面對:看石黑一雄如何點描封存的「日本」記憶
群山淡影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二部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推薦文
《群山淡影》——石黑一雄的微觀歷史和宏觀視野
遺忘,或者面對:看石黑一雄如何點描封存的「日本」記憶
群山淡影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二部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2021/08/29
2021/08/29 2021/08/04
2021/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