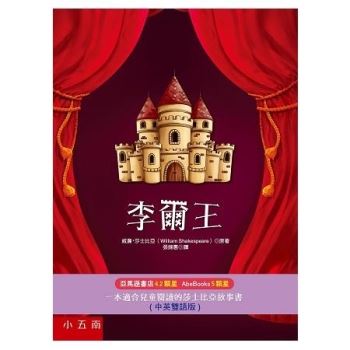圖書名稱:異鄉人
我以為他們是想治我的罪,但他們只是想審判我的人格。
他說,他曾探索我的靈魂,但卻一無所獲。
我必須承認,這、根、本、一點也不重要。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李茂生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黃雅嫺
──專文剖析
燠熱的烈陽下,槍鳴彈落,直到面前的阿拉伯人再也無法動彈。
這天的陽光和母親下葬那天一樣,刺痛著我的額葉。
莫梭原本樸實無華到不值一提的人生,
卻在母親逝世後,每一件事都突然失速偏離軌道。
那個不願見母親遺容的事、那個在守靈夜喝了咖啡牛奶的事,那個在葬禮上不落淚的事、那個喪禮隔天看了喜劇片的事……那些根本毫無關聯的瑣事,居然在未來通通變成了莫梭人格的量尺,一步一步被解讀為定罪的證據。
「正在接受審判的究竟是誰?」
莫梭知道是自己,但有好幾個瞬間,他又不是很確定。
在檢察官與律師每一次的相互詰問中,他感覺自己的靈魂都在不斷地被抽離出去,被排除於事件之外,被排除於法庭之外,被排除於現場所有人的心靈之外。
在莫梭想出答案之前,社會的模板還在無情的輾壓,將人們型塑成同一種樣貌,用世界的法則將每個人都寫成標準答案。
而你,想成為的是世界裡的一般人,還是世界外的異鄉人?
作者簡介
卡繆(Albert Camus,1913-1960)
一九一三年出生於北非法屬阿爾及利亞,父親在他未滿周歲時,就不幸葬身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而幼小的卡繆和哥哥便隨著文盲且近乎全聾的母親搬回外婆家居住。儘管生活環境十分艱難,但卡繆因其小學及中學的老師慧眼識英雄,而扭轉了他看似昏昧無光的命運。在他往後的人生中,阿爾及利亞的陽光、沙灘和地中海風光,皆轉化為卡繆思想與精神上的奠基,也變成他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
十七歲那年,卡繆由於感染上肺結核的緣故,好幾次的發病都讓他不得不提心吊膽死亡的突然來襲。面對這麼一個隨時可能結束的生命,也造就他在作品中不斷提及「死亡」的命題。
一九三三年起,卡繆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在阿爾及利亞大學攻讀哲學,而後加入了法國共產黨。畢業後,卡繆以記者的身分,報導了許多中下勞動階層與穆斯林的生活疾苦,同時也積極參加政治活動並創立劇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曾任《共和晚報》及《巴黎晚報》編輯,德軍侵法後則領導地下反抗運動報紙《戰鬥報》,成為法國最重要的意見領袖。最終卻在一九六○年一月四日,因車禍而不幸去世,享年僅四十七歲。
「荒謬」與「反抗」一直是卡繆思想的核心,他也是第一個讓「荒謬」成為存在主義重要概念的人物,並與沙特並列為法國文壇的兩大思想巨擘。
譯者簡介
韓書妍
法國蒙貝里耶第三大學(Université Paul Valéry)造型藝術系畢。旅居法國九年。目前定居台灣,為專職英法譯者。
聯絡信箱:shurealisme@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