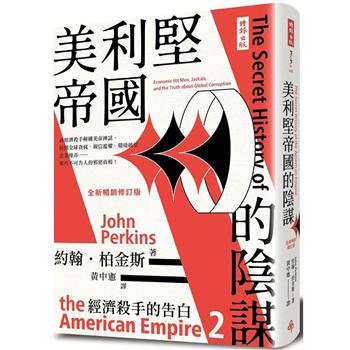甦醒,是為了宿命的相遇。
當愛情跟著背脊上的花朵一起出現,
還有一個男孩,
也像隱藏在她肌膚下的花苞那樣,
躲在她如魔法般的過去……
《暮光之城》作者大力推薦
甫出版即空降《紐約時報》排行榜第6名
迪士尼已買下電影拍攝權:《暮光之城》的Temple Hill將參與製作,
且邀請《孟漢娜》人氣女星麥莉.賽勒斯(Miley Cyrus)主演。
售出22國版權,包括日本
總覺得自己與世界格格不入的少女羅芮兒,為了背上離奇出現的巨大花朵,求助於對生物學充滿狂熱的足球隊員大衛;當兩人像CSI探員那樣分析她身上美麗的植物時,羅芮兒卻在即將售出的老家森林裡遇見了綠色眼睛、綠色髮根,神祕的年輕男子塔馬米,而他竟然告訴羅芮兒——她一直是一株開花植物!
充滿不祥預感的房地產經紀人、突然重病瀕死的父親、塔馬米強人所難的要求……為了拯救故居與父親的羅芮兒,只能拖著大衛和塔馬米、抵抗想要致她於死的邪惡陰謀……
作者簡介
艾玻妮.派克 Aprilynne Pike
從小就喜歡發揮想像力編造關於精靈的故事。20歲時取得文學士學位。寫作餘暇喜歡健身、唱歌、表演、閱讀,她同時也是協助準媽媽學習分娩的老師。最近與她的丈夫及三個孩子回到亞利桑那定居,享受陽光。
譯者簡介
綵憶
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畢業。喜歡閱讀各類翻譯書籍,因為希望能從不同文化背景中,觀賞大千 世界多采多姿的風景。對於自然界的奧祕有濃厚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