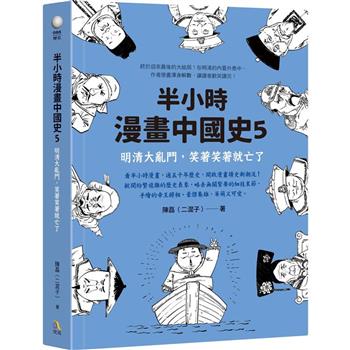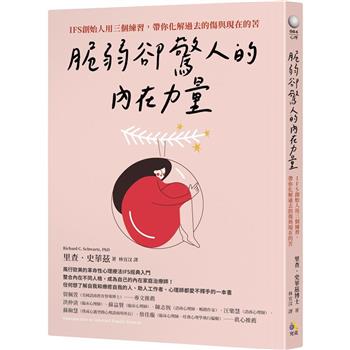楔子
恩美提著水桶與掃把,步履艱難的走向連接主堂與客樓的走廊。
雖說這裡名義上僅是一座王府,但是主堂與各個客樓、廂房,都建造得如宮殿般宏偉浩大、美輪美奐。
瞧這條廊道,站在起頭上,竟看不到盡頭,寬度也可以站上十個人。
此時正值深秋,周邊滿植的銀杏,葉子都成了明黃色,把這廊道的周圍,裝飾得金黃亮麗,乍看之下,好像不是個俗人可待的世界……
但缺點就是,隨風飄落到廊道上的落葉,怎麼也掃不盡。
而負責清掃這條廊道的,只有她一個人而已。
這裡是肅能親王府,她新主人的家。
恩美放下水桶,看了看它,不禁低呼——連水桶都是白銀打造的。
這位肅能親王雖是她侍奉的主人,但對初來乍到的她來說,他就像個傳說中的人物一樣,很遙遠,她只能用這王府上下的物品,去揣想他的面貌。
她想,這個好大喜功的人物,可能是個挺著大肚腩、掛著一對順風耳,還留得一嘴自以為飄逸、實則猥褻的鬍子的中年男人吧!
將民脂民膏花費在自己的享受上,這種人,死不足惜。
恩美緊緊握著拳頭,臉色沉了下來。
不過她馬上振作起來,看了看這條浩蕩得彷彿可以駛上一輛馬車的廊道,深深呼了口氣。
家宰說,她今天一定要把這條廊道清掃完畢,因為親王今日下午時分,定會走經此路;若讓他大爺看到一丁點不順眼的小東西沾在上面,連他家宰都有得瞧了。
「因為啊……」家宰說:「爺是個潔癖很重的人呢!」
她連忙將這條路上的落葉給掃去。
當恩美擰乾抹布,打算將廊道上鋪的黑玉磚擦拭乾淨時,忽然一陣大風吹起,竟把大片大片的銀杏葉,又吹上了廊道。
「哇啊啊啊——」恩美慘叫。「為什麼這條走廊旁邊要種樹嘛?!」
她推算了一下時辰,只拿起掃把胡亂掃了一下;畢竟掃得太乾淨,一會兒風起又做白工了。
掃罷,她便跪在地上,好好的擦地,若遇到落葉,再順手撿起。
她就這樣慢慢的打掃了一會兒。
此時,一抹被夕暮拉長的影子,伴著細碎的聲音,靠了過來。
她一愣,抬起頭一瞧……
又愣住了。
她……從沒看過……這麼英俊,英俊到甚至可以稱得上是美的男子。
這男子的五官年輕英挺,細緻飛揚的眉透著貴氣;雙眼的形狀完美得像杏核,甚至帶著些像女子的媚;他緊緊盤高的髮髻一絲不苟,更讓他的臉容爽朗淨白。
他穿著一身淡雅,卻內斂高貴的白色深衣,長長的袖子自然整齊的摺到腕上,露出一雙白皙的手,手上還握著一柄摺扇。
他用手細細的撫著摺扇柄,撫完後,又摸了摸戴在左手拇指上的白玉扳指……這細小的動作,卻可以做得這麼高貴、這麼好看,讓恩美深深被吸引了。
「我沒見過妳。」那男人說,聲音是清悅的和藹。「妳是?」
被這麼一問,恩美趕緊抬頭看他;正要回答,沒想到,卻又被他臉上那若有似無的笑意,給攫住了目光。
她想,那不露齒的笑容真是好看,雖然淡淡的,可是卻會讓人不自覺的放下戒備,直想和他掏心掏肺的談話。
她站起來,然後拍了拍被地板弄髒的裙襬。「大人,小的是乙日卯時入班的婢女……」她又偷看了他一眼,心想這人會不會是親王的小兒子?
若親王的小兒子都生得這副俊樣,那親王大概也長得不差。
「喔,原來如此,是新進的乙卯那班?」他用扇柄輕敲著手掌,狀似在思考著什麼。
這安靜的時刻,恩美也不敢作聲;不知為何,這男人雖然有溫煦的笑容、雍容的舉止,但在無意之中,卻給了人一種無形的壓力,就像此刻。
這是天生的氣質使然嗎?
過了一會兒,男人將手上的摺扇打開;一團色彩素雅,但線條卻繁複華麗的白色牡丹花,便映入了恩美的眼簾。
這男人連開扇的動作,都美得讓人不忍移開目光,也讓人一眼就看清楚扇面的圖案。「來。」他的聲音像哄孩子一樣。
「妳說說看,看得出這是什麼花嗎?」
「咦?」怎麼突然問這個?不過恩美還是回答:「是、是牡丹花,大人。」
「哦?所以妳看得到。」又是一個提高聲音的疑問句。
可這疑問……聽起來,怎麼那麼不對勁?
恩美不解的偷偷覷他;男人抓到她的視線,再度咧出一計足以讓所有女人為之倒地的溫柔微笑。
他合上扇面,扇端往遠處一指,聲音柔和的說:「我以為妳可能是個盲人,看不到這些東西,所以才沒掃起來。」
呃……咦咦咦?!
恩美霎時間說不出話來。
這、這些話……是一個端著這麼好看高雅的笑容的人,說出來的嗎?
此時,後頭傳來慌急的腳步聲,然後她聽到了家宰誠惶誠恐的聲音。
「王、王、王爺啊——小的該死,小的該死!」
「耶?」王、王爺?
家宰跑來,馬上把恩美給按倒在地,要她向男人磕頭。
他罵道:「混帳東西,快跟王爺說對不起啊!」王爺現在站著的這條路上,竟這麼凌亂骯髒,簡直弄髒了王爺的鞋底!
「呃,家、家宰……所、所以他、他、他是……」他就是那個她以為應該有大肚腩、順風耳還有猥褻鬍子的肅能親王?!
家宰對她擠眉眨眼,要她只要說對不起就好,其餘的,閉上嘴。
恩美會意。「嗯……對、對不起,王爺,非常抱歉……」可是她突然覺得很委屈,這麼大一條路,風又一直吹,她一個人,怎麼可能掃得完嘛!
「算了、算了,安爺,這丫頭是新來的,別對人家這麼苛嘛,嗯?」這個年輕的肅能親王,像是在安撫她似的。
恩美心裡叫好。
她就說嘛,這男人看起來這麼和善,家宰為什麼要怕成這個樣子?
但家宰仍是跪趴著身,一點也不敢動彈,她也就不好意思起來。
男人又說:「不過呢,下次再這樣,馬廄的位置就等著你嘍!」
恩美僵住。
「丫頭,妳叫什麼名字?」男人問。
「呃,小的叫相恩美。」恩美戰戰兢兢的回答。
「喔,恩美啊,好名字。」男人笑著說:「不過下次,妳的手要是再跟不上眼睛,我就要幫妳賜個名了。」
恩美說不出話。
「就叫『相盲子』,妳覺得如何?」說完,男人打開扇子,邊搖,邊瀟洒的離開了。
「我不是跟妳說了,今天無論如何都要把這條路給掃乾淨的!」家宰氣急敗壞的罵道:「王爺有潔癖!」
恩美好久都不說話。
當她開口時,卻只是問了這麼一句。「那、那個人,就是肅能親王?」
「沒錯。」
恩美乾笑幾聲,好像聽到了心裡破碎的聲音。
第1章
御醫說,皇帝的身子已經不行了,隨時都有可能……
解英一手搖著扇,一手揣著一桿正燒著煙膏的旱煙管;他臉上沒什麼表情,眼神卻空洞的望著與皇宮遙遙相對的遠山,正思考著什麼。
這陣子,只要他探完皇兄的病,便總是用這副模樣坐在皇帝寢殿的陪殿裡,許久許久。
宮女們都不敢打擾這位身分尊貴的肅能親王,他不但是皇帝最親近的兄弟,更兼任手握全國兵馬軍權的都統領使——即使他看起來這般年輕,只有三十出頭。
他抖抖煙管,又吸了幾口,挪移了姿勢,還是這般寧靜的望著遠方。
佇立一旁的宮女,都忍不住地偷偷覷他,因為這位尊貴的王爺,真的是她們見過最英俊、最挺拔的男人;但他身上逼人的貴氣與氣魄,卻也讓她們只敢遠觀而不敢親近。
沒有人會傻到貿然去接近這個像冰山的男人——即使他的臉上,總是掛著看似平易近人的笑。
偏殿外頭來了人,一名太監進殿,趨近向解英報備。「王爺……」
「嗯?」解英懶懶的看了那太監一眼,然後把桌上的茶碗推給他。「總算想到要替我換茶啦?」
「呃,不是的,爺,娘娘在外頭,等著見您……」太監戰戰兢兢的說。
「先替我換茶吧!不換新茶,我心情好不起來;好不起來,就不見人。」解英正眼也不瞧太監一眼,逕自高傲的吩咐。他一揮扇,有些不耐煩。「去。」
「是。」宮裡的每個人都知道,這王爺比皇上還不好侍候,因此總是低聲下氣的小心順應。
換了新茶,外頭的貴客也被迎了進來;解英抬眼,看到那容貌精緻如繪過的細瓷,身段苗條多姿,同他一樣貴氣得讓人無法逼視的森妃。
她那媚惑的眼睛與自信的嘴唇,因為精心塗了妝彩,更是明顯的突出了她超凡的美。正是因為如此,他的皇兄才會這麼寵幸她,甚至與她生下一子,使她從一個小小的嬪妃,晉升成為當今最尊貴的太子之母。
但他厭惡那眼、那唇,那種媚,不過是俗媚罷了。
不過,解英還是馬上卸下臉上的冷漠,堆上讓人覺得情真意切的微笑,起身向森妃作揖。「愚弟向娘娘請安。」
森妃笑了一聲,擺擺手,不經解英同意,就逕自坐在他對面。
解英皺了眉,他吃飯喝茶,一向最忌諱他人靠近他的桌,更厭惡一個生得俗麗面容的人坐在他對面,那會讓他倒胃口的。
可此時森妃的身價不同以往,他也不好發作。
「王爺難得進宮,怎麼不多陪陪皇上呢?老是坐在這兒,實在太悶了。」森妃說。
解英老覺得她說話時故作嬌媚,卻反倒更惹人生厭。
「皇上睡了,我不便打擾。」解英淡淡的敘述。
森妃哼笑。「還是說,因為皇上對繼承者的猶疑不定,讓王爺有氣了?」
解英斜眼看著她。
「朝上兩派大老,老爭論這話題,也惹得妾身不愛上朝旁聽了。」森妃看向修得完美無缺的指甲,笑著說:「否則身為太子的母親,多少也該知道國家大事的,您說是嗎?王爺。」
「娘娘說得是。」解英客氣的點點頭。
「那王爺對朝上兩派的爭論,可有什麼意見?」森妃像是故意要激人,又問。
解英當然知道她的居心。
皇上大限在即,兩派都為繼承者一事吵得如火如荼。有大臣主張一切依照位傳嫡長子的古禮,由年僅五歲的太子繼位,但這麼做,身為外戚的森妃與其親戚,就有當權作亂之慮,因此又生出一派,擁戴肅能親王解英登基。
森妃與解英看似都置身事外,不願參與爭論,然而人心私底下是怎麼想的,外人怎麼會知道?
「愚弟怎敢有意見?」解英笑咪咪的說。「一切以皇上說得是。」
森妃笑著,用團扇遮嘴。「王爺,妾身其實有一個主意,您願意聽聽嗎?」
解英挑眉,不置可否。
森妃揮手,遣退四處的宮女太監,並命人緊閉窗門。
解英冷冷看著她的舉動。
當四周都安靜下來時,森妃突然露出了寂寞的表情。「王爺,您瞧,光是這座小小的偏殿,一遣走人,就這般冷清孤寂……一個女人長年生活在此,您說,多麼教人不忍?」
「是嗎?」解英喝了口茶,悠哉的說:「愚弟倒覺得娘娘如魚得水。」
森妃對這諷刺微皺了眉,但趕緊微笑帶過;她站了起來,慢步到解英身後,纖手細細撫上他寬闊的肩背,力道十足的挑逗。
可解英仍是低垂著眼,沒有任何反應。
「我說……解英啊……」忽然間,森妃口中的語氣全變,變得親暱、溫柔與媚惑。她說:「你不可能不清楚外頭那幫大臣的想法,我呢,也清楚得很。他們就是看不慣女人當權,所以甚至想違背古禮,把景兒從皇位上拉下去。我們這對孤兒寡母的,就這樣任人欺負……」
解英打斷她。「嫂嫂,大哥還沒死啊。」
森妃一愕,但沒理解英,只繼續說:「不過呢,我有兩全其美的方式。解英,你要不要聽聽看?」
「嫂嫂請說。」解英這聲「嫂嫂」,叫得讓人牙癢癢。
但為求目的,森妃只能忍著。她笑道:「不如,咱們聯手?」
「哦?」解英狀似驚訝。
「我答應讓你登基,等景兒長大懂事,能治理國家了,你再退位;既為國家也為侄子的安危,還可在史書留下好名聲,你覺得如何?」
解英站了起來,打開扇子,輕搖著扇,走到窗前,沉思了一會兒。
許久,他才問:「那敢問,愚弟與嫂嫂的關係,會變成什麼?」
「呵呵,解英,你說呢?」森妃的聲音裡,充滿挑逗的意味。
想也知道,妳這膚淺的女人。解英心想。可惜,我的野心不只如此。
解英收起摺扇,回身向森妃作了一揖。「娘娘,愚弟還有政事尚未處理,要先告辭了。」
森妃瞠大眼睛。「什、什麼?」她都挑那麼明了,為什麼這男人竟無動於衷?
轉眼,解英已走到門邊,她趕緊上前拉住他。「解英,你的答案呢?」
解英低下眼,像看到骯髒的東西似的瞅著森妃的手。「請自重,嫂嫂。您今日這番話,愚弟就當作是聽到一則不可信的流,很快就會把它忘掉;倒是您,請記住,您的丈夫,是我那臥病在床的哥哥。」
「你——」森妃惱羞成怒。「就是說你不答應了?!」
「我說過,這是一則流言,不是一個問題。」解英甩開森妃的手,撫平衣角她弄皺的摺痕。
「告辭。」解英瀟洒的離開。
森妃惡毒的看著他挺拔的身影逐漸離開自己。
她喃喃自語。「是你逼我的,肅能親王。」
解英在回府的路途中,並沒有花太多心思在森妃說的那番話上。
就像他說的,他只是把她當成一則流言,聽聽、笑笑,就罷了。
可他的心情還是開朗不起來……只要一想到皇兄即將離世……
他與皇兄,感情雖稱不上好,但至少是至親手足;一旦他離世,那麼他的野心就非得暴露出來,否則他還沒除掉別人,別人就會先除掉他了。
為了生存,他不得不背叛皇兄的遺願,也要爭得這個人上人的位置。
現在的他,已經很難找到自己;一旦捲入這場皇位爭奪的戲碼,他勢必又要在自己臉上敷著厚厚的戲妝,然後陪這群人演一齣戲。
然而戲演完了,他真的就知道自己要什麼了嗎?
他沉著臉,思考著。
馬車回到府上,家宰與奴婢都來恭迎他;可一看到他的臉色不對勁,便都噤聲安靜,不敢多說一句話,就怕擾了親王,會有罪好受。
回到寢殿,女婢正要為他換下朝服,但他卻站定不動。
「爺?」女婢覺得奇怪。
「我說啊……」解英堆起微笑,轉頭問女婢。「今天的薰香是誰準備的?」
解英的表情,看起來像是要誇獎人,讓人瞧得心花怒放。
於是女婢便傻傻的說:「呃,是小的準備的。」
「原來如此。」解英點點頭,然後朝外頭喊:「來人。」
女婢一愣,見到家宰和其他婢女進房。
「王爺有何吩咐?」家宰戰戰兢兢的問。
「換個女婢來。至於她嘛……」解英正眼也不瞧對方,只是指指那女婢站的位置說:「不要讓我再看到她。」
家宰愣愣的看著那名不知所措的婢女。「王爺,是、是出了什麼問題嗎?」
「用用你的鼻子吧,家宰。」解英逕自脫下朝袍,一旁的婢女見狀,趕緊上前幫忙。「這種廉價的過期薰香,為什麼會出現在我房裡?嗯?」
「呃……」
「還有問題嗎?」解英淡淡的一瞥,氣勢卻像千軍萬馬般,輾過在場所有人。「還需要我說第二遍嗎?」
家宰醒神,趕緊揮揮手,教其他人將那犯錯的女婢給押走。
那女婢嚇傻了,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一群人走了,殿內寂靜無聲。
解英漫步至窗邊,坐在窗邊的長椅上,點起添了煙膏的煙管。
他再度獨自的安靜著。或許這樣驅開所有人的寂寥,才是最適合他的人生……
此時,有人拉了門邊的銅鈴。
解英起先沒聽到,那人又拉了拉。
解英一頓,醒了,有些不悅,懶洋洋的問:「誰啊?」
「王爺,小的送點心來了。」
「進來。」
門開了,一個小小的身影,托著比她肩膀還要寬的食案,慢慢的走進來,走到他身邊,再把食案放在他身旁的桌子上。
解英沒看向來人,只看著廚子替他準備的各式點心。
又甜、又油、又膩……他突然厭煩,甩了甩手。「撤下去。」
「咦?」那人發出疑惑的聲音。「可王爺——」
解英不讓那人說話,又說:「我說撤走。」
「不過,王爺,抽煙前,肚子若不墊點東西,會鬧胃疼的喔。」那人說。
解英挑眉。怪了,從來沒人敢在他說一之後,跟他說二的。
這個敢跟他說二的丫頭,長什麼樣子?他抬頭,看了一眼。
「哦。」他笑了一下。「我記得妳。」
「耶?」
「妳就是那個『相盲子』嘛。嗯?」他溫柔的微笑。
「呃……是……」被家宰拉來送點心的,正是恩美。
「主子剛罰完人,就被差來送點心,實在不是個好差事。妳說是嗎?盲子。」
「呃,王爺,小的叫恩美,不是盲子。」恩美很勇敢的反駁。
可解英仍逕自說下去,他很少聽人家的話的。「通常這個時候呢,妳要安安靜靜的,主子說什麼就做什麼。這樣不是比較安全嗎?嗯?」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王爺捧在手心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62 |
小說 |
$ 162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王爺捧在手心上
她一個小小宮女,卻被派去掃一條看到盡頭的走廊;
這時王爺款款踱步走來,溫柔的問她:妳看,這是什麼?
被迷得暈陶陶的她,嬌羞的答:牡~丹~花~
他淺淺一笑:所以妳沒瞎嘛!那這麼大片的落葉,為啥看不見?
咦……咦咦?!王爺真是個表裡不一的壞傢伙!
她只能恨恨的咬被,暗罵教你作威作福、教你作威作福……
這主子,真是討厭到她要去打小人了!
誰知,王爺竟出了一點「小小的」意外,
頓時大變身,淪落成只有她手臂那麼長的真人娃娃……
哈哈!天助她也,現在,輪到她對他頤指氣使啦!
看在自己得靠她過活的分上,王爺肯定得對她低聲下氣一回;
誰知他身材小歸小,但那討人厭的脾氣,卻一點也沒少!
見他這麼不識時務,她忍無可忍,便決定毋須再忍,
於是,巨大宮女對著迷你王爺,爆發啦──
她將他倒提起來,當成竹蜻蜓,在半空中轉了幾圈;
當他差點被搞得吐出來時,她對他狠狠的撂話:
王爺,您是個壞蛋!您最好搞清楚,現在,誰才是「老大」!
章節試閱
楔子
恩美提著水桶與掃把,步履艱難的走向連接主堂與客樓的走廊。
雖說這裡名義上僅是一座王府,但是主堂與各個客樓、廂房,都建造得如宮殿般宏偉浩大、美輪美奐。
瞧這條廊道,站在起頭上,竟看不到盡頭,寬度也可以站上十個人。
此時正值深秋,周邊滿植的銀杏,葉子都成了明黃色,把這廊道的周圍,裝飾得金黃亮麗,乍看之下,好像不是個俗人可待的世界……
但缺點就是,隨風飄落到廊道上的落葉,怎麼也掃不盡。
而負責清掃這條廊道的,只有她一個人而已。
這裡是肅能親王府,她新主人的家。
恩美放下水桶,看了看它,不禁低呼...
恩美提著水桶與掃把,步履艱難的走向連接主堂與客樓的走廊。
雖說這裡名義上僅是一座王府,但是主堂與各個客樓、廂房,都建造得如宮殿般宏偉浩大、美輪美奐。
瞧這條廊道,站在起頭上,竟看不到盡頭,寬度也可以站上十個人。
此時正值深秋,周邊滿植的銀杏,葉子都成了明黃色,把這廊道的周圍,裝飾得金黃亮麗,乍看之下,好像不是個俗人可待的世界……
但缺點就是,隨風飄落到廊道上的落葉,怎麼也掃不盡。
而負責清掃這條廊道的,只有她一個人而已。
這裡是肅能親王府,她新主人的家。
恩美放下水桶,看了看它,不禁低呼...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唐絹
- 出版社: 松果屋.誠果屋 出版日期:2011-02-10 ISBN/ISSN:978986232217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