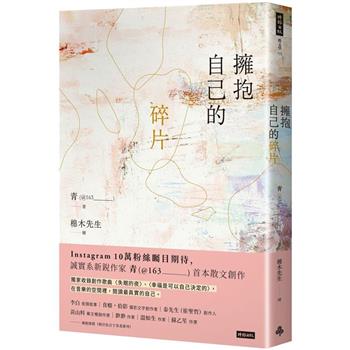◆繼約翰.伯格(John Berger)《觀看的方式》之後精闢而全面的視覺文化論述!
◆給觀看影像、使用影像、理解影像的人的視覺文化經典!
◆政大廣電系副教授 陳儒修 審訂、導讀!
每一天,我們都在「觀看」的實踐中解讀這個世界。
「看」(to see)是觀察和認識周遭世界的一個過程。
「觀看」(to look)則是主動去為這個世界製造意義。
「看」(seeing)是我們每日生活中的某種隨性作為。
「觀看」(looking)則是一種更有目的性與方向性的活動。
「觀看」可以是容易或困難的,有趣或不悅的,無害或危險的。
「觀看」同時存在著潛意識和意識這兩個層次。
我們參與「觀看」的實踐是為了溝通、影響或被影響。
這本無所不包又緊密貼合的視覺文化導論,探討了我們使用影像和理解影像的所有方法。本書檢視繪畫、照片、電影、電視和各種新媒體,涵蓋的領域包括藝術、廣告、新聞、科學及法律。作者介紹了近幾十年來與視覺分析有關的各種研究取向,以清晰易懂、高度可讀的文字,帶領讀者一一破解視覺文化的重要理論。
設計IBM logo的設計大師保羅.蘭德(Paul Rand)曾說道:教學生設計的最大原則就是,解釋每一個名詞,老師都習慣假設學生知道,但其實學生都不知道。本書難得的一大特色便是,以平易的方式,在內文中從頭說明每一個看來難解的名詞和哲學概念。
這是一本貨真價實的跨領域書籍,收錄了一百多張圖片,希望成為所有對影像有興趣者的綜合導論,以及媒體暨電影研究、藝術史、攝影和傳播等學科的最佳參考書籍。
意義並不存在於影像內部,意義是在觀看者消費影像、流通影像的那一刻生產出來的。
【名家推薦】
◎「整體而言,本書有如在進行一場視覺文化普查……本書強調觀看的『實踐』,便是主張唯有真正張開眼睛觀看,影像文本的意義才會揭露出來。因此本書又有如一本導覽手冊,讀者可以依循各章節對不同媒體的分析與論述,安心的走出重重的影像迷宮。」~陳儒修,政大廣電系副教授
◎「《觀看的實踐》以高度流暢而緊密貼合的方式,為讀者說明當代視覺文化的各種理論爭辯。」~海瑟.道金斯(Heather Dawkins),西蒙弗雷澤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藝術和文化研究教授
◎「我們終於有了一本無所不包,既富歷史意識,又具分析力道的視覺文化教科書。生動的實例、豐富的插圖,加上親切易讀的文字。全面、翔實、清晰、縝密,讀來充滿樂趣。」~托比•米勒(Toby Miller),紐約大學電影研究教授
◎「一部全面又令人信服的導論,涵蓋了各領域的批判思想。」~尼古拉斯•米爾佐夫(Nicholas Mirzoeff),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藝術系教授
◎「這是一本立論精闢、組織清晰,非常適合教學的著作――在視覺文化這個領域,像這樣令人信服、條理分明又適合初學入門者的書,實在不多。」~唐納.普瑞茲奧斯(Donald Preziosi),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藝術史教授
◎「作為這個領域的入門書籍,這本書有三大特色強項:一,它的即時性;二,它對從廣告到電視、從電影到電腦等各種影像實踐的嫻熟;以及三,它可以用深入淺出、明白易懂的方式解釋複雜萬端的方法學和影像課題。」~派翠西亞.懷特(Patricia White),斯沃斯摩爾學院(Swarthmore College)英語和電影研究助理教授
作者簡介:
美國羅徹斯特大學英語及視覺文化研究助理教授,蘇珊安東尼性別暨婦女研究中心(Susan B. Anthony Institute for Gender and Women's Studies)主任。
章節試閱
影像產生意義。然而嚴格說起來,一件藝術作品或媒體影像的意義,並不會埋藏在作品當中(那是製造者置放意義的所在)等待觀看者去發覺。意義毋寧是透過複雜的社會關係製造出來的,而這層社會關係除了影像本身和它的製造者外,至少還包括兩個元素:1. 觀看者如何詮釋或體驗影像,2. 影像是在什麼脈絡下被看見的。雖然影像具有我們所謂的優勢意義或共同意義,但它們的詮釋和使用卻不一定要順應這些意義。
我們應該牢記,藝術和媒體作品絕少一體適用地對每個人「說話」。影像通常是對著幾組特定觀看者「說話」,而這些觀看者碰巧面對了該影像的某個面向,諸如風格、內容、它所建構的世界或它所引發的議題等。當我們說:影像在對我們說話時,我們也等於是說:我們認為自己是該影像所想像的文化團體或觀眾中的一員。就像觀看者為影像製造意義,影像也建構它的觀眾。
影像製作者的企圖意義
絕大多數的影像都有其製造者最中意的一個意義。例如,廣告人常做觀眾研究,以確保觀看者會在產品廣告中詮釋出他們想要傳達的意義。藝術家、平面設計者、電影人以及其他影像製作者,他們創造廣告和其他各種影像,並企圖讓我們以特定的方式解讀它們。然而,根據製作者的意圖來分析影像並非完全管用的策略。我們通常沒辦法確知製作者想要他或她的影像意味著什麼。此外,即便找出製作者的意圖,往往也無法告訴我們太多影像的意義,因為製作者的意圖和觀看者真正從影像或文本那裡得到的東西可能是不一致的。人們常帶著經驗與聯想來觀賞特定影像,這是該影像製作者無法預期的,要不就是觀看者所擷取的意義是依據當時的脈絡(或環境)而定,因此,人們觀看影像的角度往往不同於影像製作者原先的企圖。例如,在都會脈絡中許多廣告影像是以下圖這種方式呈現,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這麼說,觀看者可能會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去解讀製作者的原始企圖。除了影像的交錯並置之外,單是混亂的視覺內容就足以影響觀看者對這些影像的詮釋了。許多當代影像,諸如廣告和電視影像,是在五花八門的脈絡中被觀看,而每一個不同的脈絡都會影響到它們的意義。此外,觀看者本身還有自己特定的文化聯想,這點也會影響到個人對影像的詮釋。
這麼說並不表示觀看者錯誤詮釋影像,或影像無法成功說服觀看者。而是說,影像的意義有部分是由「消費影像」的時間、地點和人物創造出來的,而不只和「製造影像」的時間、地點和人物有關。藝術家或製作者也許能夠創造影像和媒體的文本(text),不過他或她卻沒辦法完全掌控接下來觀看者會在他們的作品中看出哪些意義。廣告人之所以投資大量的時間和金錢去研究廣告對觀眾的影響力,正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無法完全控制影像所製造出來的意義。研究不同的觀眾如何詮釋和使用影像,可以提高影像製作者的預測能力,知道怎樣的意義容易被接受;然而即便如此,他們還是無法完全掌控影像在不同脈絡下和不同觀眾中所引發的意義。
讓我們想一想下面這個例子。1976年,一名底特律市郊工人階級的青少年,在家裡地下室的育樂間觀賞紅極一時的電視影集《戰地醫院》(M*A*S*H*),以及十年後,一名巴西亞馬遜河村莊的中年店員,在戶外商店中以電池發電的電視機觀看相同的影集。我們可以說,這兩名觀看者從該節目中取得的意義是不同的。不過,我們卻不能說其中一個觀看者的詮釋要比另一個正確。在這兩個例子裡,意義都是受到觀看者的社會導向以及觀看脈絡所影響。在這兩個例子中,影響影像意義的因素包括個別觀看者的年齡、性別、地域和文化認同;影片播出時他們各自世界所發生的政治和社會事件;還有觀看者各自的地理位置以及觀賞時間距離該節目的製作年代有多久。雖然《戰地醫院》的場景是訂在韓戰時期,但它反映的卻是1970年代的事件,尤其是越戰,所以該節目對在那段時間觀看的美國公民,以及十年後在巴西看同一節目的人來說,他們所產生的共鳴迴響是截然不同的。
就像我們在第一章曾經討論過的,符號學(semiotics)的詮釋工作告訴我們,影像的意義會隨著不同的脈絡、時間和觀看者而改變。於是,我們可以這麼說,《戰地醫院》在符號學上的意義會隨著不同的觀看脈絡而改變,節目元素會因此創造出不同的符號(sign)。一旦焦點轉移之後,我們也同樣看得出來,觀看者所察覺或接收到的意義,要比製作者企圖達到的意義來得重要。影像是在它被觀看者接受並詮釋的當下產生意義。因此我們可以說,意義並不是影像與生俱來的。意義是在影像、觀看者和脈絡三者之間的複雜社會互動中生產出來的。優勢意義,亦即某一文化中趨於主流的意義,就是從這種複雜的社會互動中湧現的。
美學和品味
影像的品質(諸如「美」)和它們對觀看者所產生的衝擊力都得接受評判。用來詮釋影像和賦予影像價值的標準,乃取決於文化符碼(code)或共同觀念,那是影像讓人覺得愉快或不愉快、震驚或瑣碎、有趣或沉悶的原因。就像我們之前解釋過的那樣,這些品質並不是影像與生俱來的,而是取決於它們被觀看的脈絡、該社會所盛行的符碼,以及做出判斷的觀看者。而所有觀看者的詮釋都離不開這兩個基本價值觀念─美學(aesthetics)和品味(taste)。
「美學」通常指的是人們對美醜的哲學感知。這種美學品質到底是存在於物體本身,還是只存在於觀看者腦中呢?哲學家們為了這個問題爭論了好幾個世紀。例如,十八世紀的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就曾經寫道,「美」可被視為獨立於批判或主體性的一個類別。康德相信人們可以在自然界和藝術當中發現純粹的美,這種美是普遍性的,而非專屬於特定的文化符碼或個人符碼。換句話說,他覺得有某些東西具有必然和客觀的美。
然而,今日的美學觀念早已不再相信美麗存在於某特定物體或影像裡面。我們不再認為美是放諸四海皆準的一套品質。當代的美學觀念強調,品味才是評判美或不美的標準,而品味並不是天生的,它是文化養成的。「情人眼裡出西施」這句諺語,不就指出了「美」是取決於個人的詮釋。
可是,品味並不只關乎個人的詮釋。品味的形成和一個人的階級、文化背景、教育程度以及其他認同層面有關。當我們論及品味,或說某個人「有品味」時,我們使用的通常是以階級為基礎的文化特定觀念。當我們稱讚人們具有好品味的時候,我們往往指的是他們分享了中產階級和上流階級的品味觀念或接受過相關教育,不論他們是否屬於這個階層。因此品味可說是教育的標誌,是對菁英文化價值的體察。至於那些忽視了社會公認之「品質」或「品味」的產品,則往往被冠上「壞品味」的名號。在這樣的理解下,品味是一種可藉由接觸文化機制(例如美術館或有「品味」的商店)而加以學習的特質,這些機制告訴我們什麼是好品味,什麼是壞品味。
品味也構成了鑑賞(connoisseurship)概念的基礎。我們大多認為鑑賞家應該是一個「好教養」的人,比較像是一個具有「好品味」,並且能夠判斷藝術作品好壞的「紳士」。鑑賞家被認為是美麗或美學的權威,他比一般人更能夠評斷文化產物的品質。這種基於階級品味的「鑑別」技巧看起來好像是與生俱來的,而不是在特定的社會或教育脈絡下習得的。「天生品味」的想法是一種迷思,遮掩了品味乃學習而來的事實。
1970年代,法國社會學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研究了一系列法國人對於品味問題的反應。他得到一個結論:品味並不是某些特定人士與生俱有的,而是可以透過參與那些推動所謂正確品味的社會和文化機制學習而來。像美術館這樣的機構,它的功用不僅在於教導人們藝術史而已,更重要的是灌輸人們什麼是有品味的,什麼不是,什麼是「真」藝術,什麼不是。透過這些機構,勞工階級和上流階級都可以學習成為「可鑑別」影像與物件的觀看者和消費者。也就是說,不管出身如何,他們都能夠根據一套充滿階級價值觀的品味系統來為影像排名。
根據布迪厄的理論,品味是強化階級界線的守門員。布迪厄在作品裡面指出,生活中的一切都透過社會網絡互相連結成一種習性(habitus,或譯慣習)─我們的藝術品味和我們對音樂、時尚、家具、電影、運動以及休閒活動的品味相連結,同時也和我們的職業、階級身分和教育程度脫不了關係。品味通常是用來傷害較低階級的人,因為它貶低了與他們生活風格有關的物品和觀看方式,認為那些是不值得注意和尊敬的。更過分的是,被判定為有品味的東西,例如藝術作品,通常是大多數消費者無福擁有的。
這些不同文化之間的區分傳統上被理解為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high and low cultural)之別。就像我們在導言中提到的,歷史上對於「文化」的最普遍定義,就是某一文化的最佳部分。這種定義具有高度的階級觀念,統治階級所追求的那些文化被視為高雅文化,而勞工階級的活動則屬於低俗文化。所以,高雅文化就是美術、古典音樂、歌劇和芭蕾舞。低俗文化則是指漫畫、電視以及最早期的電影。然而,近幾十年來,這種高雅低俗之分常被批評成上層階級的勢利作為,而且隨著文化範疇的不斷改變,這種論點也愈來愈站不住腳。在二十世紀末的藝術運動中,不管是普普藝術(Pop Art)或是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精緻藝術和流行文化之間的界線已變得越來越模糊(我們會在第六章和第七章討論到這部分)。此外,諸如媚俗(kitsch)的風行,一度曾被視為「壞」品味的人工製品,也登堂入室成為流行的收藏品,此舉更模糊了高雅低俗文化的分野。更有甚者,對於B級電影和羅曼史小說這類曾經被歸類為低俗文化產品的分析研究,也凸顯出當代流行文化在某些特殊社群和個人身上所造成的衝擊和價值,他們藉由詮釋這些文本來強化社群或挑戰壓迫。如今想要了解一個文化,就必須分析該文化的所有產品和消費形式,從高雅到低俗都不能省略。
影像產生意義。然而嚴格說起來,一件藝術作品或媒體影像的意義,並不會埋藏在作品當中(那是製造者置放意義的所在)等待觀看者去發覺。意義毋寧是透過複雜的社會關係製造出來的,而這層社會關係除了影像本身和它的製造者外,至少還包括兩個元素:1. 觀看者如何詮釋或體驗影像,2. 影像是在什麼脈絡下被看見的。雖然影像具有我們所謂的優勢意義或共同意義,但它們的詮釋和使用卻不一定要順應這些意義。 我們應該牢記,藝術和媒體作品絕少一體適用地對每個人「說話」。影像通常是對著幾組特定觀看者「說話」,而這些觀看者碰巧面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