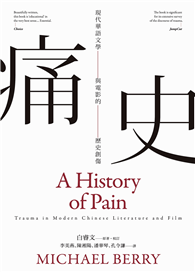推薦序
感恩心接受 智慧心處理
法鼓山有個「四它」觀念,就是在遇到任何狀況時,要「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已成為社會大眾琅琅上口的一句話。但很多人在挨罵時,通常是不舒服、不接受,也不處理,卻讓心裡產生煩惱、罣礙,之後依舊習氣存在、我行我素。
在日本,腦筋動得快的孩子,只要一做錯事被罵,就會立刻說「對不起」,一來可以平息對方的怒氣,二來在父母的眼中,仍是一位懂得「道歉」的懂事孩子。事實上,孩子或許並不了解自己錯在哪裡,只知道說「對不起」,就是避開難關的絕佳護身符。日本真言宗的高幡山金剛寺的貫主川澄祐勝,觀察到日本社會現象,有感而寫了這一本《被罵的幸福》。
佛教講求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強調要「說好話、做好事」,要常用柔軟語、親切語、慈悲語、智慧語,以欣賞的、讚歎的、勸慰的、勉勵的語氣與人廣結善緣。但誠如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也會以金剛怒目現兇猛的明王相,用憤怒威德來降服貪瞋癡特別重、冥頑不靈的人。
古代禪宗祖師大德也常以「棒喝」的方式教育弟子,都是為了杜絕弟子執著虛妄的思惟或考驗其悟境,特別用棒打,或是大喝一聲,以暗示與啟悟對方,這是站在「幫助弟子修行更好」的契機契理態度上。沿用到今日,我們要警醒一個人的執迷不悟,或破除其不當行為,就稱為「當頭棒喝」。
在近代,以嚴厲的方式教導弟子而聞名,就屬我師公東初老和尚。1959年,我的恩師聖嚴師父隨他出家之後,除了為老和尚編輯《人生》月刊,還兼做雜役及秘書。
東初老和尚有時候看到佛教界不平之事,就要聖嚴師父用筆名出面聲討,聖嚴師父很慈悲,覺得那是多管閒事,犯不著與人結惡緣,東初老和尚卻認為:「大家不管閒事的話,佛教豈非黑白不分了嗎?」又如,師父年輕時喜歡念書、寫作,但東初老和尚總是要聖嚴師父多做事,動不動就對他說:「你已三十多歲,正是做事成就人的時代。」又說:「你的智慧已夠應付得過,就是福報差點,要多做事,多培福澤。」即使後來師父在日本攻讀博士學位時,老和尚還特地寫信以「汝當作大宗教家,切勿為宗教學者」,提醒師父除了具備學識,更要滋長悲天憫人的宗教家情操。今天聖嚴師父能成為家喻戶曉的宗教師,而不是宗教學者,東初老和尚的功德非常大。
我在出家生活中,也是在恩師聖嚴師父的教誨中成長。我過去曾經擔任法鼓山護法總會輔導法師,認為出家眾就是要慈悲與人為善,廣結善緣。自從2006年9月,我繼任法鼓山方丈以來,我還是抱持這樣的想法,結果每次遇到重大決策時,為顧慮到整體的圓滿,希望面面俱到,加上承擔起創辦人聖嚴師父及全體法鼓山的託付,因此,總是慎重考量,有時會依賴師父的看法與做法。
這當然逃不過師父的法眼,他多次提醒我,「雖然尊重師父,但要學習承擔,動頭腦思考,想辦法圓滿事情,心胸要廣大,眼光要深遠。」有一次師父更是直接喝斥我說:「這是方丈的事,自己想辦法去處理,不要問師父。」甚至還加一句:「相信你做不到。」後來我自己想辦法去溝通、處理,圓滿了一項能夠利益社會的重大決策,即是有關「環保生命園區」之觀念與做法。事後,師父對其他執事法師說:「我們方丈和尚這一件事情處理得很好。」
當然,人是有情緒的,不管是罵人者還是被罵者,最重要是不起瞋念。佛教稱憤怒、生氣的心為瞋,瞋也是根本煩惱之一,是無明火,說「瞋是心中火,能燒功德林」、「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意思就是瞋火能把自己所修的功德都摧毀了,影響是非常巨大的。
在《被罵的幸福》一書中,就提到父母愈是「恨鐵不成鋼」,責備就愈是容易情緒化,但往往容易流為情緒激動的發脾氣。顯然現金剛怒目罵人是要有智慧的,或者說罵人也是一種慈悲的展現,因為罵人不是謾罵,嚴格要從愛或慈悲出發,罵一個人都是站在關心對方的立場。
同時,被罵的人也要用感恩心來接受。誠如該書中所說,人對於「被罵」這件事是永遠不會習慣的,在被罵的當下,心情一定是沮喪的。不過我們不妨這樣想,「有缺點則改之,無則嘉勉兼修忍辱」,如能以感恩心來接受,則是一生之幸福。
書中有提到一種「自我責備」的情緒管理,這讓我想到佛教是非常重視懺悔,認為人不論在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狀態下,無時無刻都會犯錯,因此必須透過懺悔,來反省自己的身、口、意三種行為,從注意、瞭解自己行為,進而反省、改善修正自己的行為。一個人藉由一次又一次地懺悔,比較容易降伏對自我的執著,讓心更加謙卑、清淨。如果能隨時懺悔自己,生起懺悔心與慚愧心,面對他人的責罵,也比較能夠正面去思考,想一想自己哪裡出錯?為什麼會被罵?
總之,罵人時當存慈悲心,被罵時則要有感恩心,彼此都能以同理心去為對方著想,如此安定和諧,自然營造豐富人生,那要建設一處「安和豐富」幸福的人間淨土,將是指日可待。
果東法師(法鼓山方丈)
作者序
無人責備是一生的不幸
不久之前,社會上似乎很流行「讚美教育」這個名詞,好像不論是家庭、學校或社會都為這個詞所炫惑,盛行一時。
人們認為讚美不可或缺,挖空心思地尋找讚美的方法,但會不會因此對過錯都視而不見呢?吃飯的時候,看到孩子狼吞虎嚥的模樣,便讚美他「生龍活虎」,卻忽略他粗魯的吃相,甚至有些父母連筷子的正確拿法,都不曾好好的教給孩子。
人哇哇墜地時是純潔無暇的,因而即使是細瑣小事,都必須經人指導才能學會。
而且,人不可能一生毫不犯錯,此為人之常情。有時會犯錯,有時有過失,所以我們才需要別人指正、教誨。
得到大人嚴正的斥責,並且認真領受時,就會產生真正的心靈交流。若是認為用空泛的讚美就能建立美好的親子或帥徒關係,是大錯大誤。
只有嚴厲的責備才能心靈相通,正因為做錯的時候受到責罵,得到讚美時,才能感受到打動心靈的喜悅。
我經常被秋山大師責罵,可以說是這輩子過的是被罵的人生。但是,多虧了他的嚴詞責罵,才能造就今天的我。責罵就是教誨。事實上,有很多事沒有師父嚴格的鞭策,自己就忽略了。
而且,正因為一直處在被責罵的狀況,偶爾得到讚美,或是感到責備之必要時,心裡便會湧出無限的喜悅。
炎炎夏日裡燒護摩木(譯注:佛教密宗的儀禮之一,日本真言宗、天台宗也保留這個儀式,即在護摩爐中燃燒薪火,投入種種供物,以佛智慧之火燒去心中的煩惱和業),自然是熱得受不了。但是燒完之後,向大家合掌行禮時,迎面拂來的風卻有著難以言傳的清涼,激起人的感恩之情。
在俳句中,「涼」這個字乃夏天的季語(譯注:日本俳句中必須出現一個關鍵字,也就是所謂的「季語」,這些字象徵時令、季節,除月份、春夏秋冬外,天文地理、祭典活動、動植物、食物都包含在內),取其因暑才知涼的意思。
我聽說最近的孩子們喜愛炫耀手機通訊錄的朋友眾多,想必是來自於「有這麼多朋友」代表自己善於交際的想法吧。
但是,在這麼多朋友當中,有幾個人會指正自己,或是說出與己不同的意見呢?順著自己說話的朋友,並不是真朋友;有錯指正的人,才是真正可以信賴的朋友。
我問過十幾歲的少年們,他們的「好友」有幾人。大多數人都說十個左右。所謂的「好友」,至多只有兩、三個人可以來往一輩子,所以這個數字不太尋常。恐怕是根本沒有了解好友的真諦,只是單純把一起玩樂的朋友稱為好友吧。說不定還誤以為那些會說逆耳之言的人不是好友,最好馬上與他們疏遠。
彼此商量、妥協並不會進步。認真地在意見上交鋒,進而切磋琢磨,彼此提攜,才能嘗到友誼的醍醐味。
在讚美中成長的人不習慣被責罵,所以,受到被罵這個事實本身的衝擊,別說是感謝,甚至會因此惱恨對方。
如此一來,被罵就成了沒有意義的事。從這個層面來看,沒有被罵豈不成了人一生中的不幸呢?
被罵才了解別人的痛
「慈祥而嚴厲!」
每當有當家長為新生兒前來寺裡祈福或慶祝七五三(譯注:按日本習俗,男孩逢三、五歲,女孩逢三歲和七歲要進神社拜拜,祈求他平安長大。)時,我總會送他們這句話。從小開始該罵的時候就要罵,才是真正的父母。
光是慈祥,是不夠格當父母的。父母的義務還必須教導孩子確實了解社會的規則,辨別可做與不可做的事才行。
盡管法律上沒有禁止,但世上還是有很多不可為之事。這些人們心照不宣的事項,我們叫它「不成文的規則」。
被媒體稱為「堀啦A夢」而名噪一時的堀江貴文,和大言不慚說「賺錢有什麼不對?」的村上世彰(譯注:堀江貴文以經營「活力門」網站起家,後因違反證券交易法被起訴,村上世彰則因股市內線交易而遭到逮捕),兩人的出發點似乎都是「只要法律沒有禁止的事,就可以做」。
但他們卻超越了「不可再往前」的線。雖然堂堂東京大學畢業,但從小到大卻沒有機會學習社會的規則,可以說是十分不幸的人。
就算沒有爆發出這麼大的社會事件,「不成文的規則」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俯拾可得。例如,從吃一頓飯當中,就能表現出其人成長的環境和品格。更別說邊走邊吃的習慣了。
從前,女星黑柳徹子曾說:「長輩教過我,與別人吃飯時,要吃得不動聲色。」
同為女星,也是散文作家的澤村貞子女士也曾表示過,吃相不夠優雅是她退隱的理由之一。因為這份職業必須面對公眾,外食的時候眾目睽睽,她無法忍受別人看到她吃相不夠端莊的樣子。
而今,女性在捷運上化妝的光景也已稀鬆平常。然而曾經有段時期,女性絕不在別人面前搽口紅或撲粉。當時的女性總會若無其事地離席,到隱蔽處補妝。
那種生活習慣現在已全然消失了。現代女性應該沒學過不令他人感到不快,乃社會的不成文規則。
很多家長說,他們無法辨別何時該罵,何時不該罵。我認為把「責罵」的中心放在期望孩子成為一個懂得別人之痛的人,應該就不會出錯了。至少,他將不會變成一個隨意傷人的人。
被罵始知人痛。從小在不被責備的環境中長大的人,以為世界是以他為中心旋轉。他只關心自己的傷痛,所以不會留意到別人跟自己同樣是人,也一樣有感情。
例如,與朋友吵架,有些孩子會脫口說出「去死!」兩字。那樣的孩子便是缺乏體會別人傷痛的想像力。
人並非生來就能嫻熟社會規則,被罵之後而能領悟社會機微,體會別人的傷痛。
換言之,受到責罵之後,才能成為堂堂正正的人。也因此,如何虛心領受別人責罵自己的話語,如何反省自己的行為,是十分重要的。
一旦體會到它的重要時,就能由衷地心懷感謝,並且品嘗到幸福的滋味。被罵真的是幸福的事。
接下來,我就以自己被罵的體驗為範例,與大家一起來思考「罵人與被罵」的意義,盼望各位能展卷直到最後。
川澄祐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