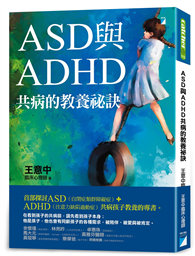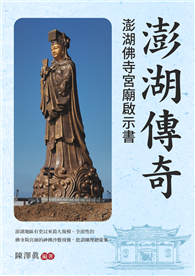第二回 觀方藥測病情絲絲入扣 治疾病如寫真樣樣相似
畫家可以運用色彩為人物畫像,而醫家能夠遣用藥物為疾病畫像,並且畫有畫格,醫有醫風,二者相通。此回中通過畫像與治病相比,說明中醫治病的特色與西醫的區別。欲知中醫如何用處方對疾病畫像,中醫大家治病有何風格,請看此回分解——
今天青禾在研究室整理病例,通過這一段時間的實習,對張老師所說的巧又有所領悟。
「姑娘,張大夫今天上班了嗎?」青禾抬頭,見一個四十多歲的瘦高男人,提黑色大提包,晃著長髮站在門口。
「張老師開會去了,可能一會兒回來。」青禾回答。
「那——」來人猶豫著,「我在這等他會兒?」
「您請進來坐吧。」青禾指指沙發。
他進來坐下,細長的手指不住地敲沙發扶手,節奏雖急促而不紊亂,好像是一首什麼進行曲的旋律。頭也隨著晃動,長髮跟著擺動。
晃了一會兒,他站起身,摸出一張處方遞過來,說:「我是張大夫的朋友,姓胡,在省畫院工作。這是我上月出去寫生前張大夫開的方子,你能不能給我抄一下?」
青禾接過處方:「這麼說您是畫家了,我對畫家素來敬佩。」
胡畫家連擺手道:「我只是胡寫亂畫,不切實際。張大夫治病救人,才值得敬佩。」
青禾將處方看了一遍,說:「我以前也很想當畫家,兼當書法家,一直是學校美術組的成員,也下了不少的功夫,可是沒能如願。現在雖然學了中醫,卻發現也能實現畫家夢。你如果感興趣,我想憑著這張藥方為你的病畫畫像。」
「我不說病情,你也不號脈,只看著藥方說我的病?」胡畫家頗感驚奇。
「也不一定能說對,」青禾微笑,「我試著說,錯了你糾正。」
胡畫家覺得青禾的唇型頗有個性,便說:「好,如果你說得對,我就給你畫張速寫。」
「你主要的病症是腹瀉。精神緊張或受涼時容易發生。腹瀉前腸鳴腹痛,瀉後就不痛了。可能近來早晨一起來就要腹瀉。你有點容易激動,心煩失眠,還有消化不良。可能也化驗過大便,或做過別的檢查,可是都沒有發現問題。」青禾看著藥方,一氣說完。
「喲,你神了呀!姑娘。說得都對!說得都對!」胡畫家聽著,不自覺站了起來,脫口而出。
「什麼都對呀,看你激動的。」隨著話音,張老師進來了。
胡畫家說了剛才的事,末了嘆道:「真是『師高徒不矮』,『強將手下無弱兵』呀。」
青禾微窘,說:「這主要是張老師『畫』病『畫』得像,你這病情和處方上的用藥都對應著呢,我只不過是以方測證,照本宣科。」
「就這也不簡單。」胡畫家說。
「青禾,」張老師指指畫家:「你可以比較詳細地給畫家先生批講批講。他雖然主攻中國畫,對醫道也頗感興趣。另外呢,我也聽聽你是如何以方測證,這算是你實習中的一次隨機小測驗吧。」
「如果這是考試測驗的話,我已經作弊了。」青禾詭祕地一笑。
「作弊?」胡畫家一愣,微晃的頭也戛然而停。
「因為我並沒有老老實實地僅僅從處方來推測。雖然沒有診脈,但咱見面了說話了,這就等於進行了望診和聞診。我是結合由此得到的資訊,與處方互相印證,來勾畫你的病情。」
「既然見了病人,這也勢必難免,」張老師釋然,「不過這也表明你能將學到的東西及時恰當的運用,那你不妨也結合望診和聞診來說。」
「好。」青禾拿出做畢業答辯的勁頭:「老師這個方子是痛瀉要方與四神丸加減化裁。方中加了固腸止瀉的訶子、烏梅,理氣止痛的元胡,所以我推測主要是腹痛泄瀉,兼有五更瀉。西醫與此對應的有腸易激綜合徵,由於本病屬功能性疾病,所以我推測大便化驗正常。雖然這是功能性病變,但久瀉傷正,陽氣漸衰,所以我推測五更瀉是後來出現的。腸易激綜合徵多因精神壓力而發病,常常伴隨失眠、焦慮、抑鬱、易激動等,我注意他時有嘆息噯氣,坐下後手指不停地敲沙發扶手,頭還常不自覺的微微晃動,又看到方中有疏肝的柴胡、佛手,所以推測他屬於敏感、好激動的一類人,藝術家正是本病的高發人群。何況搞藝術的人一般比較敏感,有點神經質。這類人容易肝氣不舒,所以我說他容易激動,心煩失眠,方中的炒棗仁也印證了這一點。方中有焦三仙,結合畫家形體消瘦,所以推測消化不良。」
張老師邊聽邊喝茶。胡畫家邊聽邊晃頭。
「最後我還得補充一點,我的推測過程參考了西醫對此病的認識,也屬於作弊——不過這也正如老師剛才所說:這也勢必難免——因忘東西有時比記東西還難。」
張老師微笑地點點頭:「你給自己打多少分呢?」
「勉強及格。」青禾似乎早有準備。
「姑娘不必對自己這麼苛刻。」胡畫家手指敲敲沙發。
「我必須排除作弊的因素。」青禾堅持。
「好了,好了,青禾,」張老師笑笑:「我看你這是文章的反襯法。不說參考而偏說作弊,潛意識裡是為了要強調你觀察的仔細,和對西醫的瞭解,對吧?」
青禾朦朧的潛意識被張老師點明,粉面泛紅,正如《素問•脈要精微論》所描寫的那樣——「赤欲如白裹朱」。
張老師轉向胡畫家:「寫生收穫不小吧?不過看來你的病情沒有多大變化呀。」
「是呀,」畫家伸出手腕,「在外面熬湯藥太麻煩了,這都有半個多月沒吃藥了。」
張老師詳察了舌、脈,又問了病情,對青禾說:「病不變,方亦不變,原方照抄。」
青禾抄過,張老師簽字,遞給胡畫家。
畫家收起處方,拿過大提包,取出一個墨綠皮面速寫本:「我剛才與姑娘口頭簽約,如果她病說得對,就給她畫張速寫——我這就履行條約。」說著,又揀出一枝炭筆。
他選了一個位置站定,對青禾凝神看了一會兒,開始用炭筆打輪廓。
三人這時都不說話,只聽得炭筆與白紙的摩擦聲忽高忽低,忽疾忽徐,忽停忽作,約半小時,畫家長出一口氣:「好了。」說著將本子靠壁豎在茶几上,後退幾步,將長髮向後一甩,瞇著眼看,忽又上前,改動幾筆。
張老師起身看了看:「行,抓到了青禾機敏的特點,可以套用『某某神情躍然紙上』這句俗話。你對她形象的畫像,和她給你疾病的畫像,可當一齣莎劇之名——《一報還一報》。」
青禾看看這幅速寫,覺得口唇處刻意為之,好像自己家裡那幅塗深色口紅的黑白照片。
「老師,我以前學過國畫,覺得寫真與治病還有幾分相通呢。」青禾邊看邊說。
「這古人早就有言在先,」張老師點點案上的《醫部全錄》,說:「元代的滄州翁,在《諸醫論》中評論宋代名醫許叔微的醫術『如顧愷寫神,神氣有餘,特不出於形似之外。』此言頗有見地。」
胡畫家聽得畫聖之畫藝可比做名醫之醫術,來了興致:「張大夫,我來說寫真,你們說治病,看二者有多少相通之處。」
青禾更是興奮,拿筆的手都有些顫抖:「我得把二位老師今天的妙論記下來,整理成論文。」
張老師對青禾說:「你是醫、畫兩棲人物,而我們是水岸兩隔,有不懂之處,還得請你溝通、『翻譯』。另外,如果說得不對,你可以執中仲裁。」
「老師取笑弟子了。」青禾自謙道:「我醫不足以癒病,畫不能夠賦形,兩樣都鬆,一事無成。」
「好好,但願等會兒你評論我們也像這樣苛刻。」張老師轉向畫家:「請你先說吧。」
「寫真要先觀察對象的輪廓,仔細瞭解五官特點,更要抓到被表現對象的神。抓到神,畫起來就可以一以貫之。」
「中醫診病先要診出患什麼病。」張老師說。
「這相當於看出對象的大致輪廓。」青禾插話。
「對,不僅如此,」張老師接著說:「還要瞭解同一疾病在不同人身上的具體表現,因『邪之陰陽,隨人身之陰陽而變也』,每個人體質、年齡、經歷等等情況不盡相同,症狀病機往往彼此差異,通過望聞問切四診,同中求異,探究病機,辨出屬於什麼證——這證可能相當於你們所說的神。」
「畫家完成觀察後,要根據對象的形神運筆,行筆或鉤或皴,用墨或枯或潤,賦彩或點或染,或濃或淡,不苟減亦不妄添,『應物象形,隨類賦彩』,不但力求外形逼真,更以追求神似做為最高境界,即畫論中說的『氣韻生動』。」胡畫家說起繪畫,有點激動,長髮隨他頭的晃動不停地搖擺。
張老師的風格則與畫家迥異,如《靈樞•陰陽二十五人》所述之陰陽和平之人,雍容謙和,侃侃而談:「中醫開方也如同為疾病畫像。古人言:『方者仿也,仿疾而立方。』與畫論『應物象形,隨類賦彩』,或許屬於不同行業的相同要求,或是同一要求的不同表達方式。所以中醫開方與寫真類似,總是精心選方遣藥,其法或清或下或溫或汗,其藥或峻或緩或輕或重,其方或大或小或奇或偶,力求方藥熨貼,恰合病情。不僅要兼顧各個症狀,更要切合病機。那些不重病機,跟著症狀跑,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子,屬於有藥而無方。」
「這些藥方好比有形無神的畫了?」胡畫家問。
「對。只有那些配伍精當,切合病機的處方,欣賞起來,才會感到奕奕有神,體會到其中的結構美、協調美、韻律美。在這裡,美的尺度對於二者同樣是適用的。」
「聽了你這高論,我似對畫論,對中醫的理解又深了一些。」胡畫家剛說完,好像忽然又想起什麼,接著又說:「那西醫好像不存在這問題吧,開方可沒你們這麼麻煩。我家老太太、老爺子雖然都是高血壓,我都看出來了,一個有痰,一個上火,但是西醫給二人開的都是什麼栗,栗達帕——對,壽比山片,連吃法都一樣。」
「這方面,中醫與西醫迥異其趣。」
青禾剛才一陣狂記,剛要停下卻又聽張老師談到中西醫差異,忙又奮筆疾書。
「西醫常是根據群體統計認識疾病,診療疾病。統計的結果常是去異求同,抹去了特殊與偶然,注重的是共性與常態。所以百人一方,或者萬人一方,對於西醫也是正常的,甚至是必需的。而中醫詳究窮辨各人的特殊反應,並據此處方,結果必然是一人一方,萬人萬方,人與人異,方與方殊。」
「可以不可以這樣說,」胡畫家道:「如果用畫像比,西醫等於統一給一類人畫一個像,千人一面;而中醫是為一個一個人分別畫像,一人一樣。」
「所以從西醫處方上只知道病情的大致輪廓,而從中醫處方中常常可以看出更詳細的資訊。」青禾邊寫邊說。
「所以你就能憑處方勾畫我的病情——儘管難免做了點弊。」胡畫家笑著接言。
「站在個體的立場上看,西醫這個統計學的運用是有弊端的。」張老師說:「儘管能夠從共性上,從總體上把握規律,然而這是以犧牲個性、漠視特徵為代價的。以部分個體的統計平均值,應用於近於無限的、千差萬別的個體,千變萬化的病情,必然有其局限性,而在診斷上難免出現假陰性、假陽性。例如在一些正常與異常的臨界線上,對某個個體可能屬於正常,可在另一個體,卻可能已經病得不輕。這種統計方法,適用於彼此個性差別不大的,勻一性較高的簡單個體,所謂千篇一律者;而不太適用於複雜個體——而人是最複雜的個體,勻一性最低。」
「就是嘛,」青禾也補充:「就說附子的用量吧,如果按照藥典用量,或許對這個人還沒顯示出治療作用,而在另一個人卻早已發生了毒副作用——原因在於這兩個個體的體質有別,前者陰寒偏盛,後者陽熱突出。」
張老師接著青禾的話說:「所以中醫運用附子,既要參考一般用量,更要瞭解病人的體質與疾病性質。於是可見到各家醫案上附子的用量差別極大,少則三克五克,輕輕一撥,即可見效;多則竟達百克,驚心動魄,方能收功。總之,既要從總體上把握規律,又要充分重視個體的差異,才能充分瞭解個體的情況,而有針對性的處理——因你所面對的病人總是具體的。由此意義上說,中醫學與西醫可成互補之勢,共同為人類健康造福。」
胡畫家也說:「其實我們畫人像也是追求一般與個體的統一,共性與個性的統一。首先是人,然後才是這個具體的人。首先是人臉,然後才是青禾的臉,然後才是富有青禾個性的五官。」畫家說著拿過那張速寫,與青禾對照細看。
青禾像是被強光射著,不自覺有點閃避,鋼筆也停在紙上,墨水向旁邊洇開。青禾看到,心中一動,說:「畫家先生,我看運墨於紙和用藥於人有點相像,同樣的墨,畫到不同的紙上效果就不一樣,好像同一劑量的藥,用到不同的人身上,療效也不一致。」
「是呀!」胡畫家一拍沙發,「我當初學中國畫時窮,買不起好紙,臨摹名家的畫總是達不到那個水墨淋漓磅基的效果。這國畫家掌握各種紙性,和中醫們瞭解病人個性,二者有些相通。」
「通過中西醫對比,可以看出:中醫是更傾向於非標準化的個體醫學,而西醫是更傾向於標準化的群體醫學——不過必須注意,這裡所說的中西醫差別,為了使你有鮮明的印象,是極而言之,有誇張的成分。事實上西醫一直都有個體化用藥,中醫也引入了統計學處理。」張老師總結道。
「因為中國畫與中醫都是非標準化的,所以醫家的處方猶如畫家的作品,常常隨個人的學派、性格、閱歷等差別,而表現出鮮明的個人或學派風格。」青禾想起第一天與張老師的談話。
「處方還有個人風格?這越說醫畫越相通了。」胡畫家感到驚奇,長髮晃到眼前,忙又掠開。
「當然了,」青禾說:「風格可不只是藝術作品的專利。」
「在這方面中醫和畫家最為相似,兩者都強調提高個人技藝,個人修養,不依附於機器或儀器,難以標準化,不得不彼此差別,不得不形成風格,猶如指紋,想擺脫都擺脫不掉。」張老師補充。
「我這有個集子,」胡畫家說著,從提包裡拿出一本精裝的《歷代中國畫選•人物畫分冊》遞給青禾:「你看看這冊子名家名畫的風格,是不是與名醫名方的風格對應。」
青禾看看目錄,翻到宋代梁楷的《李白行吟圖》,對張老師說:「這畫的風格大概與仲景經方類似吧。」
張老師見此畫用筆勁利放縱,線條質樸簡練,所繪李白形雖簡略,而神氣特足,將詩仙豪爽、傲岸的氣概表現得淋漓盡致,點頭說:「不錯,仲景經方,用藥雖簡,未必兼顧各症,但配伍精當,切合病機,抓到問題的關鍵,藥少而效宏——堪比此畫。」
「與這種大寫意風格相對的是當代王叔暉的畫風。這是她的代表作《西廂記》,工整細緻,刻畫入微,一絲不苟。」說著,青禾翻到其中的「聽琴」那面。
張老師看後說:「這一派的畫近似於時方派,處方用藥綿密細膩,輕靈纖巧——可見中醫診治疾病與其說是技術,不如說是藝術;與其說是技術操作,毋寧說是藝術創作。古人『醫誠藝也』之言,不余欺也。」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青禾學醫記:認識中醫的十七堂課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0 |
二手中文書 |
$ 221 |
小說 |
$ 238 |
小說/文學 |
$ 246 |
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青禾學醫記:認識中醫的十七堂課
讀小說學中醫?讀小說也能認識中醫?
本書採用傳統章回小說的形式來表述中醫學生青禾跟診的心路歷程。猶如武林菜鳥拜師學藝一般,我們與青禾一同闖進老中醫的練功房,跌跌撞撞在中醫浩瀚遼闊的典籍中、在功夫深不可測的師父身邊,與病魔一招半式過拳腳。既能感受真實的帶教過程,又進行了藝術加工,使得全書既具有難得的趣味性、可讀性,且不失嚴謹性,使讀者在輕鬆的氣氛中學醫悟巧,避免了單調枯燥。是醫學與文學融合的成功力作。
每個人都有看中醫的經驗,
但你還是不明白中醫,不懂為何不用量血壓就能降血壓,
不懂分明腳痛為何醫頭,不懂怎麼不用化療就能治癌症。
看醫生要說清楚問明白,看病才能安心,
說到底,你要了解中醫辨症論治的根本道理。
可是,看中醫的人懂中醫嗎?
對西方西醫療體系迷宮般的結構感到徬徨,強調「視病猶親」的中醫,又是用什麼樣的概念來治病,以及對待醫病關係的呢?簡單說,我們看病時,對三指下的診療裡面所含的精深文化,了解多少呢?
然而本書作者並沒有完全拘泥於臨床技巧這一層次,而是時常借此將讀者帶到中醫之道的大境界,通過中西醫學及中西方文化的比較,引導讀者從較高的層次俯瞰兩大醫學體系,開闊了讀者的視野,可使讀者從東西文化差异的角度,更爲深刻地理解中醫學的文化底蘊,中醫學的思維方法,中醫學特色之所在,這皆有助於從根本上,從實質上理解中醫臨床思路,意識到中國傳統文化這只無形的手對中醫臨床的統攝指導作用。
《青禾學醫記》,作為中醫愛好者、中醫院校學生的普及讀物,她可以悄然使人們與中醫靠近;作為高層次專業人員的欣賞作品,她能給人以有益的啟發和思索。淺者可得其淺,深者則得其深,是一本難得的好書!
作者簡介:
張大明
中國著名中醫學者 中醫期刊主編
文筆精湛 善於以小說或現代文字 闡述中醫藥的深刻論述
章節試閱
第二回 觀方藥測病情絲絲入扣 治疾病如寫真樣樣相似畫家可以運用色彩為人物畫像,而醫家能夠遣用藥物為疾病畫像,並且畫有畫格,醫有醫風,二者相通。此回中通過畫像與治病相比,說明中醫治病的特色與西醫的區別。欲知中醫如何用處方對疾病畫像,中醫大家治病有何風格,請看此回分解——今天青禾在研究室整理病例,通過這一段時間的實習,對張老師所說的巧又有所領悟。「姑娘,張大夫今天上班了嗎?」青禾抬頭,見一個四十多歲的瘦高男人,提黑色大提包,晃著長髮站在門口。「張老師開會去了,可能一會兒回來。」青禾回答。「那——」來...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張大明
- 出版社: 臉譜 ISBN/ISSN:978986235102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88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