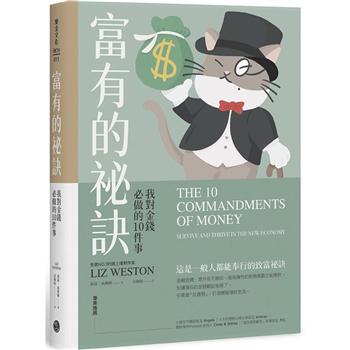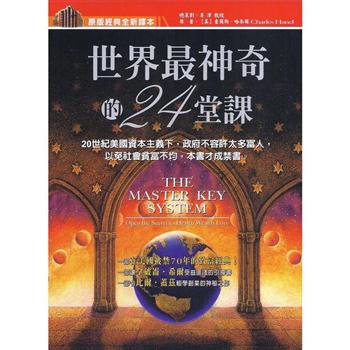克林伊斯威特 的《神祕河流》
班艾佛列克 的《再見寶貝,再見》
馬丁史柯西斯 的《隔離島》
奧斯卡金獎導演都選了他的書——丹尼斯.勒翰
他的聲音,稱得上是獨創的原型。──麥可康納利(Michael Connelly)
勒翰高質感的偵探小說簡直成了我的命脈。——史蒂芬金(Stephen King)
夏姆斯獎最佳首作、全球銷售千萬冊的冷硬男女偵探搭檔派崔克/安琪系列
從來沒人需要她,為了一份神祕文件,突然間,全世界都在找她
而我會完成這個任務,不.計.代.價——
不被需要的感覺
可有可無的人生
這世界太殘酷
他x的,你需要來上一杯
一開始只是個尋人任務,
三個地方政治角頭的委託案,
波士頓最佳偵探搭檔派崔克和安琪奉命找出一個偷走機密文件的黑人清潔婦。派崔克和安琪原想,只要動用黑白兩道的人脈,查出清潔婦落腳所在,打個電話通知雇主,任務即可圓滿結束,賞金即可輕鬆落袋。
沒想到,清潔婦拿走的不是機密文件,而是幾張藏在不知名地點的照片。想要這幾張照片的也不只是三個政客,還有兩個彼此廝殺的幫派首腦。才剛接到任務不到二十四小時,派崔克就遭到狙擊,才剛和清潔婦碰面,她就慘死在派崔克面前,胸膛被轟成蜂窩。
無法阻止的死亡,無法挽回的街頭暗殺與對決,這條貧窮、醜陋、每個人都看不起每個人的街上,派崔克與安琪決定要為這個死去的女人做點事,為她從未被人需要的人生找回公道。
即便用盡力氣去恨,這世界也不會停止運轉
一旦你開始讀《戰前酒》,你就可以體會什麼叫做「不忍釋卷」──聖匹茲堡時報
不寒而慄……一個布局完美、極好讀、極耐讀的故事。——波士頓週日環球報
作者簡介:
丹尼斯.勒翰
一九六五年八月四日出生於美國麻州多徹斯特,愛爾蘭裔,現居住在波士頓。八歲便立志成為專職作家,出道前為了磨練筆鋒、攥錢維生,曾當過心理諮商師、侍者、代客停車小弟、禮車司機、卡車司機、書店門市人員等,以支持他邁向作家之路的心願。
一九九四年以小說《戰前酒》出道,創造了冷硬男女私探搭檔「派崔克/安琪」系列,黑色幽默的對話與深入家庭、暴力、童年創傷的題材引起書市極大回響,五年內拿下美國推理界夏姆斯、安東尼、巴瑞、戴利斯獎等多項重要大獎,外銷二十多國版權,並以此系列寫下北美一百三十萬、全球兩百四十萬冊的銷售成績。
勒翰真正打入主流文學界,登上巔峰的經典之作是非系列作品《神祕河流》。小說受好萊塢名導克林伊斯威特青睞改拍成同名電影,獲奧斯卡六項提名,拿下最佳男主角、男配角兩項大獎,小說也因此一舉突破全球兩百五十萬冊的銷售佳績。二○○七年,好萊塢男星班艾佛列克重返編劇行列,取材勒翰的派崔克/安琪系列第四作改拍成同名電影《Gone, Baby, Gone》(中文書名:再見寶貝,再見;中文片名:失蹤人口),首週便登上北美票房第六名。小班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勒翰的作品氣氛懸疑、人物紮實,以寫實的筆法書寫城市犯罪與社會邊緣問題,是他將小說改編搬上大銀幕的主要原因,原著小說也隨之攻占紐約時報暢銷小說榜第三名。
二○一○年二月,勒翰另一部暢銷小說《隔離島》也搬上大銀幕,由馬丁史柯西斯執導、李奧納多狄卡皮歐主演,本片是兩人繼《神鬼無間》後再次攜手合作,這也是馬丁史柯西斯首次嘗試驚悚懸疑風格的影劇作品。
相關著作
《神祕河流》
《隔離島》
《雨的祈禱》
譯者簡介:
朱孟勳
政治大學西洋語文學系畢,曾任出版社編輯,現為專職翻譯。譯作包括《我所緘默的事》、《特洛伊首部曲:銀弓之王》、《玫瑰迷宮》、《國王的五分之一》、《失竊的孩子》、《美人魚的椅子》、《大師的身影》、《魔鬼的羽毛》、《在德黑蘭讀羅莉塔》、《古文明之旅》、《鴿子與劍》、《爬樹的女人》、《吻了再說》、《二十世紀的書》等。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本文內容涉及《戰前酒》一書情節,請自行斟酌是否繼續閱讀。
這酒後勁極強,一如現實人生──關於《戰前酒》
文/臥斧(作家)
或許有人會覺得老套,但我還是想從《神祕河流》講起。
童年好友吉米、大衛及西恩有天在街上玩耍,突然出現兩個狀似警探的男人,將大衛帶上車;吉米及西恩眼睜睜地看著汽車離去,直至回家通知家長,大人們才發覺事態有異。數日後,被綁架虐待的大衛脫逃,那兩名臠童犯伏法,但三個好友就此漸行漸遠。過了幾年,三人各自長大成人,吉米在混過黑道坐過牢後,經營起一家雜貨店,西恩搬離小鎮成為警探,大衛也有了自己的家庭。某日,公園內發現一具女屍,西恩趕去處理時,發現死去的女孩是吉米的長女,而頭號嫌犯,正是案發當晚浴血回家的大衛……
誤解、遺憾、埋藏的罪與不得不繼續往下走的現實,《神祕河流》,如此開始。
《神祕河流》的原著小說二○○一出版,在二○○三年由克林.伊斯威特執導,搬上大銀幕,同名小說隨後在國內出版譯本,觀眾與讀者都給了頗正面的評價。在我看來,《神祕河流》這個故事,絕對算是「好的大眾文學」——「大眾文學」不是那種非要以極前衛文字技巧或者極天才藝術風格來躋身文史的作品,而是以絕大部分人都能夠接受的風格所敘述的故事;這類小說既然不在技巧上頭做文章,那麼要從「普通」變成「好」,就非得在內容當中顯能耐不可。也就是說,《神祕河流》這本小說好讀、好看,而且它裡頭還有些東西,讓我們每次回頭想想,都能體會出一些關於人性的什麼。不過,我猜在那個時候,絕大部分的讀者,並沒有把勒翰的《神祕河流》,歸屬於某種「類型小說」。
畢竟,「類型小說」這個標籤,同時兼具「快來!」和「別摸!」的效果。
記得有個朋友在終於克服「不讀推理小說」的心理障礙、讀完卜洛克的《八百萬種死法》之後,不解地問我,「這個故事很好看呀,但……『冷硬』在哪裡?」——這正是類型標籤的「別摸!」效果。打個更泛論式的比方:如果某本小說貼上「推理小說」的貼紙,那麼一個推崇福爾摩斯超人智慧(或任何一種推理小說常用元素)的讀者,可能會馬上把它從書店的新書平台拿起來、帶到櫃台付帳,還沒回到家就在路上翻讀起來;但一個討厭福爾摩斯老是跩得二五八萬(或任何一種推理小說常見設定)的讀者,可能連摸都不會摸一下。弔詭的是:所謂的「類型小說」,其實正屬於「大眾文學」;既然這類故事好讀好看,那麼僅因那個類型標籤就與之絕緣,豈不可惜?
從《神祕河流》講到大眾文學,繞兜了一圈,其實是因為我們要聊聊《戰前酒》。
《神祕河流》的作者丹尼斯.勒翰,在出版二○○一年的《神祕河流》及二○○三年的《隔離島》兩本單集完結作品前,曾在上個世紀末的九○年代,出版過五本系列作品;這個被稱為「Kenzie/Gennaro」的系列,以派崔克及安琪這對一男一女的偵探搭檔為主角、龍蛇雜處的波士頓大城為背景,敘述殘酷街區上的人性故事。這個系列大多被歸類成「推理小說」系譜中的「冷硬派」,系列作的第一本,就是《A Drink Before The War》——《戰前酒》。 剛講過「類型小說」標籤的問題,所以咱們先甭管這書的分類,直接來看故事。
《戰前酒》的故事在一段回憶似的獨白之後開始:主角派崔克穿著體面地走進一家「低調奢華」的飯店,三名政治人物正在裡頭準備同他會面。帶頭的參議員表示,有個在州議會大樓工作的黑人清潔婦,從另一個參議員的辦公室裡偷走一些機密文件後消失無蹤,因他久聞派崔克擅長尋人,因此願意提供優渥的賞金,要求派崔克盡快把文件找回來。派崔克與搭檔安琪循著線索找到了清潔婦的藏身地點,軟硬兼施地要求對方交出文件,卻發現自己莫名其妙地遭到狙擊……由小事件而大麻煩,似乎是種常見的主線行進方式,但《戰前酒》的故事除了這個尋人的主軸之外,還有許多旁生纏繞的支線故事,而所有支線,幾乎都同主線故事推展時逐漸揭示的幾個主題有關。
第一個得注意到的主題,應當是「暴力」。
「暴力」指的不一定是那種血濺當場的械鬥或者火花四射的爆炸場面,事實上,在生活的各個層面當中,暴力一直無所不在,最常見的型式之一,或許就是「家暴」——書中最明顯的例子來自於派崔克的搭檔安琪。安琪是一名美麗幹練的女偵探,卻嫁了一個會對她施暴的丈夫菲爾;有回派崔克想替她出頭所以揍了菲爾一頓,卻讓安琪氣得幾週不同他交談;參議員口中偷竊文件的清潔婦珍娜、街頭新興幫派的青年頭目,甚至是主角派崔克自己,都是(或曾是)在家暴陰影中掙扎求生的受害者。
將視點從這種人與人之間的角度往後拉,就能發現另一種暴力的型式。
這種暴力存在於不同的街頭幫派之間、不同的種族(或者在這個島上生活的我們更熟悉的所謂「族群」)之間,以及政客與一般民眾之間;在不同的型式當中,暴力以不同的樣貌橫亙其中:有的是因微不足道爭執而引發的明刀明槍爭鬥,有的是因根深柢固觀念所造成的偏執錯誤見解,有的則是在獲得授權之後以一種為所欲為的姿態去欺瞞、利用、煽惑或愚弄當初賦予自己權力的授權者。 如此看來,暴力似乎無所不在,但身處其中的當事人不應總是無計可施才是。 當然,有些極巨大(例如種族議題)的問題可能沒有什麼簡單的解決方式,但,在理想的民主制度中,選民在評定政客作為之後,是有能力決定是否繼續授予他們執政權力的;就算不看這個可能得要耗費社會成本及動員大量人力才能完成的動作,像家暴這種只發生在自個兒屋子裡的事情,照理說應該不難解決才是——只是事實證明,這類暴力一直理直氣壯地蠻橫存在,道理為何?
其實讓這些暴力活得自由自在的原因,常是簡單的「感情」因素。 正如安琪對派崔克說的,「菲爾並不是一直這麼混蛋的」,因為感情付出過就收不回來、因為感情付出後就一直存在,所以當暴力的使用者披著某種依附著我們感情的外套,我們就無法理智地與其對抗,反倒是心甘情願地接受愚弄、操控,甚至會貼心地替施暴者編織美麗的理由來包裝他們的暴力作為。這種屬於凡人的、現實的、明知偏離卻只能隨波逐流的感情因子,在《戰前酒》當中是另一個隨處可見的主題,有時令人動容,有時令人扼腕。
但當感情投注的對象回應以暴力,無論如何,我們總會有另一種情緒因而孳生。
這種簡而言之謂之「恨」的情緒,在所有為所愛之人暴力相向的角色心中,時時與前述的「感情」相互抗衡,也成為《戰前酒》當中埋伏於字裡行間的重要主題。幫派火拚或者種族歧視是某種恨的表態,連公理或者正義都可能是某種恨的包裝。但,當暴力已經實行、心已經留下創口之後,無論是讓愛壓著恨或者是讓恨顛覆愛,傷口都不會消失;它要嘛就是愈裂愈大直至把靈魂撕成破片,要嘛就是留下癒合後的傷疤,每當夜深人靜時就隱隱地抽痛,或者悄悄地淌血。
世界是不完美的。在其中討生活的每個人也都如此。
但日子還是得過下去。於是《戰前酒》當中的角色一如現實當中的吾等之輩,在工作場合或者人群當中有一種樣子,在家庭裡頭或者孤獨一人時則顯出另一種長相;道貌岸然的政治人物有令人髮指的嗜好、身為救火英雄的父親有非理性的畏懼及無法控制的暴力、好勇鬥狠的幫派首領有不堪回首的童年往事、聰明強悍的偵探有乏力掌握的情感糾葛。派崔克在故事一開始的獨白當中便如此說道,「……去年夏天有人死了,那些人大多數是無辜的,有的人比某些人罪有應得。去年夏天也有人動手殺人,他們沒一個是清白的,我很清楚,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凝視著細窄的槍管,看著布滿恐懼與憎恨的眼睛,發現我自己的倒影就在那眼底。我扣下扳機,好令它消失。」 死去的人有好有壞,但存活的人沒有一個是清白的。
照這麼看來,《戰前酒》故事的主軸極為沉重,似乎有種讀了難以下嚥的嫌疑,但在勒翰高明的敘事技巧及節奏掌控下,透過第一人稱主述者派崔克的賤嘴,使得《戰前酒》的閱讀經驗,意外地有種輕快、帶著黑色幽默的基調。派崔克/安琪這對非情侶(派崔克單身、安琪已婚;派崔克有意追求安琪,但安琪多次拒絕)工作搭檔的互動,還常帶著某種情境喜劇的調調。 話說回來,派崔克與安琪並不是第一對男女偵探搭檔。
大約與「謀殺女王」克莉絲蒂同期的推理小說創作者賈德諾,便已創造出柯白莎及賴唐諾這對工作夥伴;在這兩組人馬當中,男性(賴唐諾及派崔克)一般都負責外勤任務,而女性(柯白莎與安琪)則大多負責後援工作。只不過,這兩組搭檔的相同處,大約也僅止於此,較之智勇雙全、讓系列作品中絕大部分女性角色愛得要死的無照律師賴唐諾,勒翰筆下的派崔克似乎比較接近一般人,會粗心大意、會受騙上當,行事計畫比較直線,一點兒都沒有賴唐諾那種隨手設計不可思議妙計的本領;而與毫無身材可言、臃腫市儈尖酸勢利的柯白莎相比,勒翰創造出來的安琪簡直人如其名、是個天使的化身:美麗苖條、識情重義,雖然大多擔任後勤工作,但真上了前線,她的槍法可比派崔克還準。
雖然無法確定勒翰是否特意造成這些同中之異,但這些設定,卻很忠實地反應了時代的變遷。
戰後美國依然維持男尊女卑的社會型態,這不但是瘦小又溫柔的賴唐諾讓其他女性角色大為傾倒的原因,可能也是賈德諾之所以把柯白莎塑造成一個巨大俗氣、不同於絕大部分女性角色的理由;而在派崔克與安琪初登場的一九九四年,男女關係看起來似乎較先前來得平等,女性的行事也較為自主,在《戰前酒》的故事裡,派崔克正在努力戒菸,而安琪仍然照抽不誤,派崔克的槍法不大靈光,安琪可就好多了。不過雖然安琪是個新世代女性,但她仍需面對故事中男性角色(有時還包括她自己的搭檔派崔克)在言語上輕薄揶揄的狀況,這也反應了在所謂兩性平權的新時代當中,有些因性別而衍生的不平等,依舊存在。
聊過這些《戰前酒》的主題,讓我們回到「類型小說」這件事情上頭。
事實上,一開始承辦小案件但卻隨著劇情發展而扯進愈來愈多麻煩、掀翻高尚階級(無論是政治人物或富商名流)的裙腳曝光不堪入目的污穢內裡、與自己乃至於整個社會的不完美搏鬥抗爭、語出譏誚(可能是對所有人、也可能是針對自己)地嘲諷對抗所有偏差……這些《戰前酒》當中俯拾可見的元素,都是達許.漢密特、雷蒙.錢德勒、羅斯.麥唐諾及勞倫斯.卜洛克等一脈相承冷硬派犯罪小說創作者常用的設定。冷硬派(Hard Boiled)這個從傳統推理小說當中分岔生長的支系,沒有洞察全局的神探、沒有布局精巧的詭計,而是翻出街頭的殘酷面向,用以彰顯人性的骯髒與美好。
所以,是的,《戰前酒》自然是本類型小說,但它也的確是個極好讀、也極耐讀的故事。
父權的傾壓、愛情的不對等、階級間的相互仇視、誤解、利用及關懷,在所謂的美好童年當中可能留下必須一輩子與之抗衡的印記,在感情當中可能生出不可解的張狂暴力。這些混在《戰前酒》裡頭的原料,完全取材自你我浸泡其中的現實生活,像是一杯後勁極強的烈酒,愈是回味,感觸就愈是層出不窮,現實、以及小小暖暖的溫柔,無奈、以及巨大難忍卻得背負承擔的憂傷。人生是場無法脫逃的惡戰,勒翰的《戰前酒》,一如所有在冷硬街頭打滾的偵探,盡自己的力量去抵擋某種歪斜,雖然無法改造世界,但卻能撐住一點希冀。
現在,這杯人性的酒已然上桌;你,是否已經準備好要讓它入喉?
媒體推薦:
一旦你開始讀《戰前酒》,你就可以體會什麼叫做「不忍釋卷」──聖匹茲堡時報
不寒而慄……一個布局完美、極好讀、極耐讀的故事。——波士頓週日環球報
父權的傾壓、愛情的不對等、階級間的相互仇視、誤解、利用及關懷,在所謂的美好童年當中可能留下必須一輩子與之抗衡的印記,在感情當中可能生出不可解的張狂暴力。這些混在《戰前酒》裡頭的原料,完全取材自你我浸泡其中的現實生活,像是一杯後勁極強的烈酒,愈是回味,感觸就愈是層出不窮……──作家 臥斧(摘自本書導讀)
名人推薦:※本文內容涉及《戰前酒》一書情節,請自行斟酌是否繼續閱讀。
這酒後勁極強,一如現實人生──關於《戰前酒》
文/臥斧(作家)
或許有人會覺得老套,但我還是想從《神祕河流》講起。
童年好友吉米、大衛及西恩有天在街上玩耍,突然出現兩個狀似警探的男人,將大衛帶上車;吉米及西恩眼睜睜地看著汽車離去,直至回家通知家長,大人們才發覺事態有異。數日後,被綁架虐待的大衛脫逃,那兩名臠童犯伏法,但三個好友就此漸行漸遠。過了幾年,三人各自長大成人,吉米在混過黑道坐過牢後,經營起一家雜貨店,西恩搬離小鎮成...
章節試閱
麗池卡爾頓飯店的酒吧正對市立花園,入內須打領帶。我曾經從其他觀景點眺望過市立花園,沒打領帶,也不覺得手足無措,不過或許有些事麗池比我還清楚。
牛仔褲和休閒衫是我平常的穿著,但西裝領帶是為了公事,因此這是他們的時間,不是我的。何況最近我的髒衣服來不及拿去洗,我的牛仔褲也不可能自己跳上地鐵,來這兒跟我會合,讓我一有機會就換上。總之,我從衣櫃挑了一套亞曼尼的深藍色雙排釦西裝——我的客戶拿來付我費用的幾樣東西之一——找到搭配的鞋子、領帶和襯衫,在你還沒來得及稱讚我「夠GQ」,我便光鮮得足以參加正式的晚宴了。
穿越阿靈頓街時,我對著酒吧的暗色玻璃櫥窗顧影自賞。我的步伐輕快,眼神炯亮,頭髮一絲不苟,完全符合這世界的標準。
年輕的門房臉頰滑嫩得彷彿直接跳過青春期,他打開沉重的黃銅門說:「歡迎光臨麗池卡爾頓飯店,先生。」他說得倒也真心——我選中了他的小飯店,令他不覺流露出自豪的語氣。他以誇張的姿勢把手臂往前一伸,為我指路,以免我自己搞不清方向。我還來不及謝他,門就在我身後關上,他已忙著為下一位幸運兒招呼全世界最高級的計程車了。
我的鞋踩在大理石地板上,發出軍人踏步清脆的劈啪響,長褲清晰的褶痕反映在黃銅菸灰缸上。我總以為能在麗池的大廳看見飾演克拉克.肯特的喬治.里夫斯,或鮑嘉與雷蒙.馬西同抽一根菸。麗池是那種充滿低調奢華的飯店:地毯是深沉富麗的東方風格;櫃台與門房的桌子是熠熠生輝的橡木做的;大廳是形形色色的人熙來攘往的中途站,除了野心勃勃的股票經紀人手提軟皮公事包,忙著運送著自己的前途外,還有披著毛皮大衣、自命不凡的貴婦,不耐煩地等待著每日例行的修指甲約,以及大批身穿海軍藍制服的男僕,推著黃銅行李車經過厚厚的地毯發出最輕柔的咻咻聲。無論外界有什麼變化,站在這大廳,看著這些人,你會以為現在還是德軍大肆空襲倫敦的時代。
我越過酒吧的男服務生,自己打開門。他究竟高興與否,表面上看不出,究竟有無生氣,表面上也看不出。厚重的門在我身後關上,我站在長毛地毯上,發現他們坐在酒吧深處臨花園的一張桌子。那三個人所擁有的政治勢力,足以阻撓我們進入二十一世紀。
年紀最輕的吉姆.福南見到我立即起身,面露微笑。吉姆是我們本地選出的議員;這件事是他的工作。他邁出三大步跨越地毯才伸出手,臉上立即綻露甘迺迪式的笑容。我握住他的手。「嗨,吉姆。」
「派崔克。」他說,彷彿一整天都在停機坪望穿秋水,等我從戰俘營歸來。「派崔克。」他又說了一次,「很高興你能來。」他拍拍我的肩,打量我的眼神又好像昨天才跟我碰過面。「你穿得很帥。」
「想跟我約會嗎?」
吉姆聽了立即發出真誠的笑聲,似乎有點過頭。他帶我到桌邊,「派崔克.肯錫,史特林.穆爾康參議員,布萊恩.保羅森參議員。」
吉姆說「參議員」這幾個字時,帶著令人難解的敬意,就像有人說「海夫納」時的那種口氣。
史特林.穆爾康臉色紅潤、肥碩健壯,是那種把體重當作利器而非負擔的人。他有一頭僵硬的白髮,幾乎可以在上面降落DC-10噴射運輸機,握手的勁道足以造成對方麻痺。打從內戰結束後,他就一直是本州多數黨領袖,而且至今仍未打算退休。他說:「派特小子,很高興又見面了。」他還帶有濃重的愛爾蘭腔,應該是在波士頓南區成長養出來的口音。
布萊恩.保羅森瘦骨嶙峋,光滑的頭髮顏色如錫般灰白,他的手握起來感覺潮濕而多肉。他等穆爾康就座自己才坐下,我不由得懷疑他是否先經過他允許才敢在我手心流了滿手的汗。他向我點頭、使眼色,以示招呼,正是只肯暫時跨出別人影子的人會做的事。不過他們說他即使當了穆爾康多年的跟班,還是很有頭腦。
穆爾康揚起眉,看著保羅森。保羅森揚起眉,看著吉姆。吉姆揚起眉,看著我。我頓了一下,然後揚起眉,看著他們每一個人。「可以告訴我是怎麼回事嗎?」
保羅森一臉困惑,吉姆似笑非笑。穆爾康開口說:「該怎麼開始呢?」
我看了後方的酒吧一眼。「先來一杯如何?」
穆爾康發出開懷的笑聲,吉姆與保羅森也跟進。現在我知道吉姆的笑聲從何而來了,不過至少他們沒有一起拍膝蓋。
「當然。」穆爾康說:「當然。」
他舉起手,一個甜膩的小妞隨即出現在我身邊,她身上的金質名牌寫著瑞秋。「參議員!有什麼需要嗎?」
「麻煩給這年輕人一杯酒。」這句話從他的大嗓門和笑聲間迸出。
瑞秋的笑顏更加燦爛,她微轉過身,俯頭看我。「當然,請問先生想喝什麼?」
「啤酒,你們這兒有啤酒嗎?」
她笑了,政客們跟著笑。我克制住自己,保持正經的臉色。天啊!這可真是個歡樂的地方。
「有,先生。」她宣布:「我們有海尼根、貝克、摩爾森、山姆亞當斯、聖保利、可樂娜、羅文布勞、多斯伊奎斯——」
我趁天還沒黑趕緊打岔:「摩爾森就可以了。」
「派崔克。」吉姆說著邊交握雙手,挨到我面前。該談正經事了。「我們有一點……」
「棘手難題。」穆爾康說:「我們手頭上有一點棘手難題,希望能低調處理,然後盡快把它拋到腦後。」
一時之間,沒人講話。或許大家心裡都在想,了不得,我們居然認識一個會在閒談中用「棘手難題」這種字眼的人。
穆爾康往椅背靠,一面盯著我瞧。瑞秋又來了,把一只冰涼的玻璃杯擺在我面前,倒了三分之二瓶的摩爾森進去。我發現穆爾康的黑眼珠定定地注視著我。瑞秋說:「享用愉快。」然後就走了。
穆爾康的目光毫不動搖,或許要發生大爆炸才能讓他的眼睛眨一下吧。「我跟你爸爸很熟,小伙子。我沒見過……呃,比他更好的人,他真是個不折不扣的英雄。」
「他提起你也是讚不絕口,參議員。」
穆爾康點點頭,表示這是理所當然。「可惜,他走得早,看起來像傑克.拉蘭那麼硬朗,可是——」他用指關節敲敲胸口「——心臟的毛病誰也說不準。」
我父親與肺癌搏鬥了半年,最後不敵而病逝,但穆爾康硬要認為是心臟病就隨他吧。
「如今,這是他兒子。」穆爾康說:「幾乎長大成人了。」
「幾乎。」我說:「上個月,我甚至開始刮鬍子了呢!」
吉姆臉上的表情彷彿吞下了一隻青蛙。保羅森斜眼瞄了一下。
穆爾康綻開笑容。「好了,小伙子,好了,我懂你的意思。」他嘆口氣。「我告訴你,派特,等你到我這年紀,就會知道除了昨天以外,一切似乎都才剛發生過。」
我若有所思地點點頭,其實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穆爾康攪拌一下他的酒,然後拿出攪拌棒,輕輕放在雞尾酒紙巾上。「我們都知道說到找人,沒人比你更在行。」他攤開手掌,朝我這兒一捧。
我點點頭。
「啊!不謙虛一下?」
我聳聳肩。「這是我的工作,最好還是專精一點。」我啜了一口摩爾森,甘苦參半的強烈滋味在我舌間漫開,這已不是頭一次我寧願自己還抽菸。
「總之,小伙子,我們的問題是:我們有個相當重要的法案即將在下週提出,我們的攻擊火力很強,可是某些我們用來集中火力的方法與服務有可能被……誤解了。」
「誤解?」
穆爾康點頭微笑,彷彿我說了「好傢伙」。
「誤解。」他重複道。
我決定陪他繼續玩下去。「而這些方法和服務——有紀錄和文件資料?」
「他的反應真快。」他對吉姆和保羅森說:「沒錯,真的很快。」他看著我說:「文件資料,沒錯,派特。」
我不知該不該告訴他我最痛恨別人叫我派特,乾脆我改口叫他史特,看他喜不喜歡。我喝了口啤酒。「參議員,我的專長是找人,不是找東西。」
「容我插句話。」吉姆打岔道:「檔案在一個人身上,而這個人最近失蹤了,是——」
「——是州議會大樓裡一個原本挺可靠的員工。」穆爾康說。穆爾康正是「不怒而威」的極致代表,他的態度、語氣和臉色並未流露出責難之意,但吉姆卻一副做錯事被逮個正著的神情。他拿起威士忌喝一大口,搖晃得冰塊撞擊杯緣,叮噹作響。我懷疑他是否還敢再插嘴。
穆爾康看著保羅森,保羅森便伸手拿起公事包,抽出一小疊文件,遞給我。
最上面一頁是張照片,解析度不佳,是州議會大樓員工證的放大影本。照片中是個黑種女人,中年、雙眼飽經風霜、臉上表情疲憊不堪。她的嘴唇微開,斜向一邊,彷彿正要對攝影師表示不耐。我翻過這一頁,第二頁是她的駕照影本,擺在一張白紙中央。她叫珍娜.安傑林,現年四十一歲,看來卻像五十歲。她的駕照是麻州三級駕照,未被吊扣。她的眼睛是棕色的,身高五呎六吋,地址是多徹斯特區肯尼斯街四一二號,社會福利號碼是○四二——五一——六五四三。
我看著這三個政治人,發覺我的視線不由得被穆爾康的黑眼珠吸引過去。「還有呢?」我說。
「珍娜是我辦公室的清潔女工,布萊恩的辦公室也是她負責的。」他聳聳肩。「以黑人來說,我對她沒什麼好挑剔的。」
穆爾康覺得沒把握可以在對方面前用「黑鬼」這類字眼,便改口說「黑人」。他就是這種人。
「直到……」我說。
「直到她九天前失蹤。」
「自動放假?」
穆爾康看我的神情,彷彿我剛說的是大學籃球賽沒作弊。「她﹃自動放假﹄時,也帶走了那些文件。」
「拿去當海灘假期的讀物?」我問。
保羅森往我面前的桌子用力一拍,說:「這可不是鬧著玩的,肯錫,你懂嗎?」
我用懶洋洋的眼神看著他的手。
穆爾康說:「布萊恩。」
保羅森抽回手,以便檢查他背後的鞭痕。
我仍用睡眼瞪著他——安琪說我這是死人眼——然後對穆爾康說:「你們怎麼知道她拿了那些……文件。」
保羅森的目光從我眼睛移開,往下垂,落在他自己的馬丁尼上。那杯酒還沒動過,此時他也沒喝,八成在等批准吧。
穆爾康說:「我們確認過了,相信我,除了她,沒有人是合理的嫌疑犯。」
「為什麼是她?」
「什麼?」
「為什麼說她是合理的嫌疑犯?」
穆爾康皮笑肉不笑地說:「因為她失蹤那天,文件也不見了。誰搞得懂這些人?」
「嗯。」我說。
「你可以幫我們找她嗎?派特。」
我朝窗外望去,門房正忙著把一個人連推帶拉地送進計程車。花園內有一對身穿「歡樂酒店」運動衫的中年男女對著華盛頓的雕像猛拍照,等他們帶回家鄉欣賞時,肯定會連連叫好。人行道上有個酒鬼用抓著酒瓶的手撐住自己;另一手掌心朝上往前伸,穩如泰山地等人施捨零錢。美麗的女人成群結隊經過。
「我收費很貴。」我說。
「我知道。」穆爾康說:「但是你為什麼還住在舊區?」聽他的口氣,彷彿要我相信他的心也還留在那兒,彷彿如今那裡的意義大過另一條可以讓人飛黃騰達、出人頭地的捷徑。
我思索著該怎麼回他,想了些念舊情、歸屬感之類的答覆,最後我說了實話:「我的公寓有租金管制。」
***
聖巴托洛穆教堂的鐘樓就是我的辦公室,我一直沒查出以前鐘樓裡那口鐘的下落,在隔壁教會學校教書的修女們也不肯透露。年紀較長的索性來個相應不理,較年輕的似乎覺得我的好奇心很有趣。海倫修女有一次告訴我,那口鐘「被奇蹟似地變走了」,這是她說的。和我從小一塊兒長大的喬伊絲修女老說它被「放錯地方了」,然後對我露出修女不該有的邪惡笑容。我是偵探,但即使山姆.史貝德也會被這些修女耍得團團轉。
我拿到偵探執照那天,教區神父杜門德就問我願不願意為教堂提供保全服務。有些不信神的人又闖進來偷聖餐杯和燭台,套句杜門德神父說的:「這種鳥事最好別再發生。」他提供我到神父宅用三餐、第一件案子以及來自上帝的感謝,只要我進駐鐘樓,等待下一次闖空門事件發生。我說我可沒這麼便宜,我要求他在我找到自己的辦公室之前,暫時先讓我使用鐘樓。以教士而言,他算滿容易讓步的。但是,當我看到裡面的狀況時——九年沒使用——就知道原因何在了。
安琪和我勉強把兩張桌子塞進去,還有兩張椅子。當我們明白再也沒有空間可以擺得下檔案櫃時,我又把所有的舊檔案搬回住處。我們裝了一台個人電腦,拚命把資料往磁碟機裡塞,再將一些正在處理的檔案擺在辦公桌上,給客戶留個專業的印象,好讓他們幾乎忘了這辦公室的寒傖。「幾乎」。
我爬上頂階時,安琪正坐在辦公桌後面,忙著研究最近的安.蘭德斯專欄,於是我躡手躡腳走進去。起初她沒注意到我——安正在處理的必定是個棘手的人物——難得她如此安詳自若,我便趁機仔細端詳她。
「嘿,側滑小子。」她說著從桌上的菸盒抽出一根菸。
只有安琪會叫我「側滑小子」,這或許是因為十三年前我開著爸爸的車繞竿單側滑行時,只有她在旁邊。
「嘿,美人。」我說,坐進自己的椅子。我想叫她美人的應該不只我一個,這是習慣使然或事實的陳述,就隨你挑了。我對她的墨鏡點點頭。「昨晚又玩過頭了?」
她聳聳肩,朝窗外望去。「菲爾喝了酒。」
菲爾是安琪的丈夫,也是個混蛋。
我把想法說了出來。
「是啊,反正就是這樣……」她掀起窗簾的一角,在手中翻來覆去。「你打算怎樣?」
「和以前一樣。」我說:「我十分樂意照以前的方法做。」
她低下頭,墨鏡便滑落到鼻梁下方,露出從左眼角延伸至太陽穴的一道瘀青。「等你算完帳,他會再回家,到時候會讓我現在的傷痕看起來只是小意思而已,就跟打情罵俏留下的痕跡差不多。」她將太陽眼鏡推回眼睛前方。「我說的對不對?」她的聲音輕快,卻嚴厲如冬日的陽光。我討厭這種聲音。
「隨妳吧!」我說。
「樂意之至。」
安琪、菲爾和我從小一起長大。安琪和我是最好的朋友,安琪和菲爾是最好的情侶。有時是如此。這是根據我的經驗,但幸好只是有時如此,而非經常如此。幾年前,安琪帶著墨鏡和兩顆腫得像八號撞球的眼睛,來到辦公室。還有手臂、脖子上各式大小不一的瘀青,以及後腦勺一吋高的腫塊。我的臉八成洩露出心中的盤算,因為她劈頭就說:「派崔克,理智一點。」看來那並不是頭一回,事實也是如此。只不過那是最嚴重的一次,所以當我在俄芬姆斯角的吉米酒吧找到菲爾時,我們心平氣和地喝了幾杯酒,心平氣和地玩了幾局撞球,然後我切入正題,他的反應則是:「關你什麼鳥事,派崔克?」於是我便用結實的撞球桿打得他半死不活。
為此我沾沾自喜了幾天,可能還做了些跟安琪共同生活的幸福美夢,我記不太清楚了。接著菲爾出院了,換安琪整整一個星期沒來上班。當她再度出現,一舉一動都小心翼翼,而且每次坐下或起身都得深吸一口氣。他沒碰她的臉,但她幾乎渾身青紫。
她兩星期不跟我講話。兩星期,還真久。
此時我看著望向窗外的她,這已非我頭一次想不透為什麼這樣一個女人,一個不輕易受騙上當,敢狠狠修理巴比.羅伊斯的女人(他竟敢抵抗我們溫和的勸進,不肯去見替他付保釋金的人),居然受得了當丈夫的受氣包。那次巴比.羅伊斯當場倒地不起,我則是常想何時也輪到菲爾,不過截至目前為止,時候還未到。
我可以想見她怎麼回答我的問題——她每次談到他,就會用那種有氣無力的聲音說話。她愛他,就這麼簡單。我再也無法在他身上看到的某種特質,他們私下相處時或許仍顯現在她面前;或許在她眼裡,他所具有的某種美好特質仍像聖杯一樣閃閃發亮。事情一定是這樣,因為不論是我或任何一個認識她的人,都覺得他們之間的關係毫無道理可言。
她打開窗戶,把手中的香菸彈了出去。道地的都市女孩。我等著窗外某個夏令營的學生發出尖叫,或某個修女拖著大屁股爬上樓來,眼中燃著上帝的怒火,手裡捏著未熄的菸屁股。但是什麼也沒發生。安琪從開著的窗戶轉過身,清涼的夏日微風吹進了餘煙、自由和撒滿校園地上的紫丁香花瓣香氣。
「所以,我們又有工作了?」她說著靠回椅背。
「我們又有工作了。」
「好耶。」她說:「對了,這身行頭不錯。」
「讓妳忍不住想撲過來嗎?」
她緩緩搖頭。「呃,不。」
「所以妳不知道我去了哪?」
她又搖頭。「我很清楚你去了哪,側滑小子,問題就出在這兒。」
「爛女人。」我說。
「臭小子。」她對我吐舌頭。「什麼案子?」
我從西裝外套的胸口暗袋抽出珍娜.安傑林的資料,扔到她桌上。「單純的尋人案件。」
她翻閱資料。「為什麼會有人重視中年清潔女工失蹤的案件?」
「看來有些文件跟著她一起失蹤了,州議會的檔案。」
「哪方面的文件?」
我聳聳肩。「妳也知道這些政客,什麼事都神祕兮兮的。」
「他們怎麼知道是她拿的?」
「妳看照片。」
「啊!」她說著點起頭。「她是黑人。」
「對大多數人而言,這就是足夠的證據了。」
「即使是本地參議會裡的自由派?」
「本地參議會裡的自由派在休會期間,也只不過是另一個來自南區的種族歧視分子。」
我把我們見面的情形,以及有關穆爾康與他的哈巴狗、保羅森,和麗池飯店極盡諂媚的工作人員都告訴她。
「這個吉姆.福南議員——在那些議會大老面前,表現得如何?」
「妳看過大狗和小狗的卡通片嗎?就是那種小狗吐著舌頭哈哈哈,一面跳上跳下,一面不停問大狗:『我們要去哪,老大?我們要去哪,老大?』的卡通。」
「看過。」
「他就像那樣。」我說。
她把鉛筆放進嘴裡咬,然後又用鉛筆敲門牙。「你轉述給我的二手資料不清不楚,到底怎麼回事?」
「大概就這樣了。」
「你信他們嗎?」
「鬼才信他們。」
「所以事情並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麼單純,大偵探?」
我聳聳肩。「他們是民選的官僚,哪天他們說出全部的實情,妓女也免費賣身了。」
她笑笑。「你的比喻向來精采,你可真是良好教養下的奇特產物。」她看著我,笑得更開,鉛筆繼續敲著左門牙,有點小裂縫那顆。「那麼,其餘的內情呢?」
我拉鬆領帶,把它從頭頂解套。「妳問倒我了。」
「這算哪門子的大偵探。」她說。
麗池卡爾頓飯店的酒吧正對市立花園,入內須打領帶。我曾經從其他觀景點眺望過市立花園,沒打領帶,也不覺得手足無措,不過或許有些事麗池比我還清楚。
牛仔褲和休閒衫是我平常的穿著,但西裝領帶是為了公事,因此這是他們的時間,不是我的。何況最近我的髒衣服來不及拿去洗,我的牛仔褲也不可能自己跳上地鐵,來這兒跟我會合,讓我一有機會就換上。總之,我從衣櫃挑了一套亞曼尼的深藍色雙排釦西裝——我的客戶拿來付我費用的幾樣東西之一——找到搭配的鞋子、領帶和襯衫,在你還沒來得及稱讚我「夠GQ」,我便光鮮得足以參加正式的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