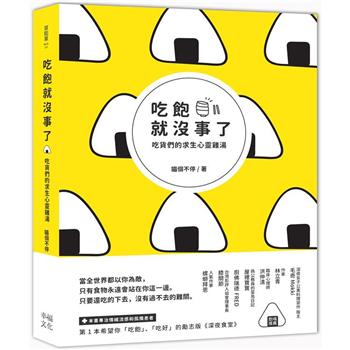第六章
來自水平式組織人的請求:請正視我們的存在!
左撇子本身沒什麼不好的,但如果全世界以右撇子為中心旋轉,左撇子這時真的會變成殘障人士。光看大學教室裡的課桌椅就知道了,那椅子前方加了塊由左往右掀開,給人寫筆記墊著用的板子。左撇子坐在這種椅子上寫筆記時,她的左手臂不得不懸在空中,再不然就是整個人蜷縮在椅子裡頭,左手臂放在右撇子平常放筆記本的地方,而真正的筆記本被推到右撇子平常放右手臂的板子邊緣。我們可以稱左撇子為「情境性殘障」(situational handicap),意即:當周遭事物以右撇子思維為運作核心,左撇子的人這時確實可稱為殘障人士。
我不是左撇子,但我屬於其他比較不為人注意的情境性殘障。我是一個水平式組織人,但我身處在一個為了垂直式組織人設計的世界裡頭。這問題很值得放入本書討論,因為就我觀察,很高比例的結構式拖拉人也都屬於水平式組織型。
「垂直式組織」這個概念,靈感出自高高長長的直式檔案櫃。這世界正朝著無紙化前進,因此將來這種檔案櫃應該會褪入黯淡的記憶之中,不過目前很多辦公室中仍可看見直式檔案櫃霸踞一方。對於水平式組織人來說,直式檔案櫃代表一種他們無法了解的生活型態。不過,雖然他們無法了解箇中道理,身邊眾多垂直式組織人倒是真的懂得使用這種櫃子。說來也有道理,反正垂直式組織人的其中一個顯著特徵就是,他們知道要如何利用像直式檔案櫃這種東西。以下是莎莉.艾倫(Sally Allen)在教人如何收拾東西的部落格中,聽來令人歡欣鼓舞的建議:
就讓紙張順著流向它的終點站吧。什麼,你說沒有終點站?我的朋友,這就是檔案櫃的存在意義啊!迷失的紙張渴望找到一個家呢!設計出令你滿意的檔案整理系統,就像(童話故事中)在彩虹彼端找到滿滿一壺金子那般美好!好的檔案整理系統能讓你找回主控權,加強你的專業形象,大大提升你的生產力。
我知道莎莉.艾倫是位可愛迷人的女士,她說的這番話也相當正確,但這番話不折不扣就是垂直式組織人的思考結果。垂直式組織人很自然地就懂得使用檔案櫃,存放他們預定一小時、一天或一周後用的資料。當他們要用那些資料的時候,他們便會打開檔案櫃,找出存放文件的資料夾,將文件抽出來,繼續先前的工作。不過,他們不曉得對水平式組織人而言,這種方法說有多陌生就有多陌生。
某天我在寫一封給帕羅.奧托診所(Palo Alto Medical Clinic)的信,告知他們開給我的帳單寫錯了,我沒有欠他們這麼高的費用。要寫好那封信頗有難度,於是我那時把帳單和通聯紀錄全攤開來放在眼前。我還有別的事要做,因此還沒寫完就先離開桌前了。這時如果是一個垂直式組織人,就會把這東西收進檔案夾中,回來後再拿出來寫完。但如果我也這樣做,這份文件就會變成我書桌上的一個整齊的區塊而已。這種整齊的區塊正是垂直式組織人的特有象徵,但對我來說文件一旦變成整齊的區塊,下場大概只剩扔掉一途了。
當然,我沒有真的照著上述建議做,而是把未完成的信留在桌上,攤放四處的文件也留在原位。不過更精確地說,信和文件並非真的放在「桌面上」,因為其他待完成的工作早就放在桌上了,它們其實是疊在改到一半的報告、寫了一半的課堂講義、讀了一半的小冊子等等東西上頭。
其實,我就是個百分之百水平式組織人。我喜歡把待完成的所有資料全攤放在眼前的平面上,如此一來所有資料都映入眼簾,提醒著我繼續完成它們。假使我把資料放進資料夾,我就再也看不到它們了。問題不在於我找不到資料或檔案(儘管這也發生過),而是我把東西放進去之後,我就再也不會費心去看了。我與生俱來的本質就是欠缺打開檔案櫃、拉出做到一半的工作,回到桌前繼續完成的能力。
你可能會想,電腦說不定能解決上述問題,但如同我們前一章所說的,電腦對這問題也束手無策。水平式組織人會把檔案散落於電腦各處資料夾,結果亂七八糟的程度和真實生活中的模樣差不了多少。如我早先說的,像我這樣的人即使改用電子信件聯絡,也只有處理收件匣中新信件的能力。就算開了個稱作「緊急事務」的資料夾,也不會有什麼效用,因為我們永遠不會準備好打開那個資料夾。
話說回來,我其實真的有用檔案櫃的習慣。我的檔案櫃中會放:(一)、已完成且不打算再看到的工作;(二)、丟了會有罪惡感但根本不想細看的文件。例如,你以前的同事寄給你一篇她剛寫好的文章,篇幅長而且內容無聊,但如果直接丟掉的話實在太無情太惡劣了,而且下次她問起的時候非撒謊不可。但如果你把這篇文章放入檔案櫃,你就可以說:「噢,我已經把這篇文章放入暑假要讀的文件資料夾裡頭了。」這句話道出的不過就是你有個標為「暑假要讀的文件」的資料夾,以及你把文章放入這資料夾裡頭。如此一來,你也不是真的在說謊,雖然你今年夏天(或未來任何一年的夏天、秋天、冬天、春天)讀這篇文章的機率其實是零。
回頭看看我的書桌,它的模樣應該會引發莎莉.艾倫等垂直式組織人的批評。這些人認為各式物件散落在桌上,反映了這個人也同樣雜亂無章。但事實並非如此,這好比一個左撇子學生擠在前面提到的那種椅子上做筆記,別人看到卻認為這學生有肢體不協調的問題。這同時也是所有水平式組織人的問題!整個世界就是為了垂直式組織人而設計的,他們利用檔案櫃讓自己的生活有條有理,而其他水平式組織人擁有的收納空間就只剩下書桌、檔案櫃的「上面」、附近的椅子和地板而已。如果有人願意花時間想想,如何幫水平式組織人設計出好的檔案儲存與修復系統,我們自然也可以和其他人一樣收得乾淨又整齊。
我有個想法,與其在書桌前工作,我倒希望在研究室擺張那種會出現在中式餐廳的旋轉餐桌。這種餐桌上頭會有個大大的圓型轉盤,占了整張桌子的大部分,剩下的餐桌外圍剛好可讓客人放自己的餐盤。各種菜餚會擺上圓形轉盤,而每個客人可以自行轉動轉盤(要慢慢地轉,除非你想把整盤蘑菇雞片灑到襯衫上),將想吃的菜轉到自己面前。
我想一張直徑十五呎的旋轉餐桌剛剛好可放進研究室,而我生活的所有片段就可以灑落在這張桌上。我可以把圓桌用切比薩的方式區分成幾個不同區塊,分別用不同字母標記起來。當我工作進行到可以處理醫學診所的信的時候,我只需要把轉盤一轉,轉到正確的比薩區塊,拿起餐盤上頭放的資料就行了。(我想對應的字母應該是醫學〔medical〕的M,或者是診所〔clinic〕的C?可以是信件〔letter〕的L,或者未完成〔unfinished〕的U?也許還會有「某些讓我很不爽的東西」〔something I am upset about〕的S?我想等我買了一張旋轉餐桌後,我就知道要怎麼用字母分類了。)
當我把工作全攤開來放在旋轉餐桌上,它們每樣物品都能分得我的注意目光,而如果它們被整齊放入檔案櫃收起來,大概就永不見天日了。如果我把資料全部攤開在旋轉餐桌上,每樣物事一定都會很有條理,就像其他垂直式組織人能做的那樣。
坦白說,一張直徑十五呎的旋轉餐桌肯定會占去我研究室不少空間,因為整間研究室也才十六呎大而已。我多少會把自己想成鐵路模型俱樂部照片中的成員那樣,整個房間全被鐵路模型板占去,地上滿是小小的城鎮模型、紙做的山,還有散落一地的鐵軌。模型製作人埋首於這整片混亂中,偶爾從中冒出頭來。由於旋轉餐桌是圓的,而我的研究室是方的,我的椅子大概會放在剩下的其中一個角落裡頭。於是,我可以走進研究室,鑽進圓桌下爬到椅子所在的角落,再冒出頭來,像個垂直式組織人一樣,準備要俐落有型且效率高超地完成工作。我還可以像玩具模型的鐵路工人一樣,戴頂丹寧布工程師帽,不過我想這頂帽子應該不是讓整套旋轉圓桌系統流暢運作的必要條件。
第九章
拖拉人真的很白目嗎?
有好幾年的時間,本書第一章都放在我的網站上。有位女士讀了這篇文章後,把文章連結寄給她的丈夫(我暫且稱他為尼爾),而這位先生讀完以後,寄了這封電子信件給我:
我那位身為拖拉人的太太,寄了這篇文章給我看。她覺得這篇文章很風趣,我則覺得很白目。這篇文章可能提供了一些對付拖拖拉拉的有效方法,但並沒有解釋拖拖拉拉的成因,也沒有質疑為何學術界比其他地方更常出現拖拖拉拉的情形。我任教於一所大學,經常看到同事連寫篇短文都拖上好幾個禮拜,遲交成績搞得整個統計分數的流程烏煙瘴氣,訂書單拖了好幾周甚至好幾個月都還沒寄出,逼得書店抓狂。為什麼會這樣呢?我懷疑原因某程度上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中寫到的變態精神有關:自願做出傷害自己的行為,只為了證明自己不是一台無人性的機器。不過我想主因應該是學術界的傲慢心態,認為偉大的思想家可以不受世俗法則束縛,就算會導致他人受到傷害也不願委屈自己。所以我認為你的文章既不幽默也沒什麼實質助益,只不過暴露出高等教育中這方面問題的症狀有多嚴重罷了。
尼爾的來信提醒了我們一個重點(如果我們需要這個提醒的話),那就是:我們拖拉人確實常惹惱別人,尤其是我們的另一半和同事。從尼爾的信來判斷,他似乎不是個拖拉人。但從過往經驗看來,拖拉人連自己的拖拖拉拉界同胞都能惹惱,其中最容易動怒的就是同屬拖拉人的另一半。所以,大家最好比自己的另一半更懂得拖拖拉拉。當然了,這絕不是必要行為。
尼爾的診斷是,我們拖拖拉拉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想藉著耽溺於自傷行為,證明自己不是一台無人性的機器,這是他從杜斯妥也夫斯基作品中得到的靈感。這是他的說法,但我沒有被說服。起碼我不認為他的說法切中他人認為拖拉人最白目之處。如果我要證明自己是一台無人性的機器,我可以做很多麻煩自己但不會麻煩別人的事情。我可以很晚才出發去教室上課,幾乎遲到以致於不得不在路上狂奔。儘管我到教室時氣喘如牛,但我可以藉此說服自己並非一台無人性的機器。不過,這並不是我太太與同事最可能覺得我白目的行為。
我認為最容易讓別人發怒的拖拖拉拉行為,通常是你想表現出自己不受他人控制而做的行為。比方說我在書房工作,我太太忽然進來,提醒我要檢查信用卡帳單,因為她覺得其中幾筆刷卡紀錄有問題。她很顯然是希望我停下手邊工作,把筆電移開,拿起(她好心地攤在我眼前的)帳單,立刻照她的要求做——即使我們沒有任何重要理由非得今天就處理信用卡帳單不可。
本來我大概也沒在做什麼正經事,可能是看Harbor Supply寄來的電子信件,裡頭附了絞盤、太陽能發電器扭力扳手之類的商品折價券,雖然我不用這些東西,但還是想成為會用到這種東西的人。其實我的太太不曉得(當然她應該會懷疑一下)她進來的時候我正在打混,她還以為我正在寫那篇寫到一半,(如果她沒在這時候進來打擾的話)可能為哲學界帶來空前改變的偉大文章。所以我當然有被打擾到。
被惹惱了之後,我故意拖了比平常更久的時間,就是不想檢查信用卡帳單。這樣做的理由不是要傷害我自己,也不是要證明我並非一台機器,而是(如果真的要找出什麼理由的話)要讓我太太知道,硬是在她丈夫絞盡腦汁、埋首於論文當中的時候闖進來,並不會讓她的計畫得逞。
我知道自己這樣很幼稚,不能當作結構式拖拉的正面例子,因為我遲遲不檢查信用卡帳單的時候,並沒有把時間拿去做其他有用的事情。原本我藉著讀廣告信好延後某件工作,比方說決定下個學期要用哪本課本,但我太太的打擾反而給了我新的拖拖拉拉機會,讓我可以把原本的工作延到更久以後再做。
我故意拖著不立刻檢查信用卡帳單,好挫挫我太太的銳氣,讓她以後不要再打擾我工作。這種模式聽來確實很怪,不過已經持續約莫五十年了。
我的建議是:結構式拖拉,和向你的配偶宣示你的自主權,是截然不同的兩碼子事。想用拖拖拉拉的方式讓對方知道自己對某事的反對立場,等到對方真的提出很不合理的要求時再做吧。不過,我太太目前為止提出的要求沒有不合理過。
尼爾覺得最不爽的對象是他學術圈的同事,他認為出現這情況的原因應該是學術傲慢,他認為「偉大的思想家可以不受世俗法則束縛,就算會導致他人受到傷害也不願委屈自己。」我相信他有些同事真的有這種傲慢心理,但我也很確定標準的結構式拖拉人不會有這種症狀。多數的拖拉人錯過死線的時候都會有罪惡感,而且我們發現自己拖拖拉拉的行為傷害到別人時也會難過不安。真正傲慢的學者不會覺得自己在拖拖拉拉,反而會認為他的作法才是安排事物的正確順序,而別人無法領會到他們的聰明才智:「我現在忙著重讀康德,說不定讀著讀著就得到靈感,寫出了十頁精彩之作,為目前多如牛毛的康德研究更添一筆榮光,他們那些人難道要我在這偉大的早晨改考卷?」
然而,結構式拖拉人相較之下比較謙虛,造成別人麻煩的時候也會覺得不好意思。比方說,我自己就很仔細地算過,假使我過了繳交成績的死線,卻仍拖著不交出學生成績,在不造成學生困擾的情況下究竟還可以拖多久,最後算出的結果是半天。我把這半天當成絕對不可以錯過的絕對死線,因此我不太會連這道死線都置之不理。我認為傲慢的拖拉人和結構式拖拉人應該是完全不同的兩種類型。
還有,為什麼尼爾要替書店感到憂心忡忡呢?如果我的同事很擔心我遲交書籍訂單,我很可能會懷疑他∕她正在進行所謂的「多管閒事」,因此我很可能會啟動先前討論配偶關係時提到的「不受控制型拖拖拉拉」模式。不過,這樣做當然還是很幼稚的,也沒必要這樣做。
比上面好得多的作法,是正面迎擊那位(很可能在)多管閒事的同事,送給他幾則很不錯的哲學建議。我把尼爾的來信貼到網頁上之後,有位讀者給了以下的回覆:
為什麼人有時候就是不走斑馬線?為什麼每次說派對七點開始,大家都等到八點之後才陸續出現?為什麼很多人開車會超速?為什麼女孩們說她們喜歡好人,但從來不會和好人約會?為什麼大家老是言行不一?為什麼大家不能乖乖遵守常規就好?
「把鏡頭拉遠一點吧,一切很快就會走到終點,太陽即將爆炸。」
——吉米.史東(Jim Stone),名攝影家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拖拖拉拉,人生照樣精采:史丹佛教授給拖拉人的成功提案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40 |
二手中文書 |
$ 158 |
職場學 |
$ 170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拖拖拉拉,人生照樣精采:史丹佛教授給拖拉人的成功提案
後天才要完成的事,幹嘛明天就開始做?
為拖拉人洗刷壞名聲的第一書!
搞笑諾貝爾獎得主、史丹佛王牌教授教你如何成為快樂又成功的拖拉人!
你是個愛拖延的人嗎?
你是否對自己這個習慣深感罪惡?
你曾經努力告別拖拉,卻總是失敗嗎?
恭喜你!讀完本書,你將從此不必再心煩,抬頭挺胸地高喊「我是拖拉人」吧!
「告別拖拉」、「別『拖』壞你的人生」、「克服拖延惡習」、「拖延是成功最大的絆腳石」……諸如此類的陳腔濫調,你一定聽膩了,也免疫了吧?
這一次,讓同為拖拉一族的史丹佛大學退休教授約翰.培利,帶你一起宣讀最實用有最有趣的拖拉宣言:
◎拖拖拉拉不是罪──「我就是拖拉人!」
讀了你的文章後,我終於能抬頭挺胸,了解自己雖然老是拖拖拉拉,卻也完成了非常多的工作,是個有用的人,也終於生平第一次鼓起勇氣,叫我的兄弟閉嘴然後滾蛋。對了,我已經七十二歲了。
晉身成功拖拉人的第一步就是承認,如果正視自己的拖拉本質、順應拖拉做調整,就能變得更有效率、迅速完成更多事情!
◎看穿事情真相、調整步調,讓節奏掌握在自己手中!
人們經常認為有些事情絕對不能拖,因此給自己造成巨大的壓力。那些事情通常有兩種特徵:一、看起來有明確的期限(實則不然);二、看起來無比重要(其實一點也不)。唉,我們的生活中就是充斥著重要性被誇大的工作和虛假的死線(攤手~),放輕鬆點,慢慢來,還原每件事情的真實樣貌,就能丟掉許多不必要的煩憂,找出最合適自己的生活步調!
◎學會「拆」事情,跟「一事無成」說byebye!
如果你經常不小心拖延,也許你會沮喪地覺得自己「什麼事也沒做」,但若是回頭深思一下,其實你會發現自己做了很多事,只是都不是最要緊的事罷了。所以呢,不要覺得自己很沒用,你需要的只是學會如何列出待做清單的順序而已。先把大到嚇人的工作拆解成一個個小任務吧。這樣一來,你就會在完成每件小事後得到莫大的成就感,日復一日,完成大事的日子就不遠啦!
拖拖拉拉不是罪也不是壞習慣,只是許多拖拉人還沒有找到和這個特質的相處之道而已。掌握書中提出的一些小技巧,你就可以今天拖過明天,在拖拖拉拉中不知不覺完成很多事,成為活出自在人生的快樂拖拉人!
咦!你又來不及交出某份報告啦?
欵,沒關係,先翻開本書看下去吧!這將是你唯一不想拖延的一件事!
作者簡介:
約翰.培利
於一九六八年獲得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哲學博士,此後曾任教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和史丹佛大學等多所名校。二○○八年於史丹佛大學榮譽退休後,在加州大學的河堤分校講授哲學課程。他在網路上發表的一篇關於〈結構性拖延〉(Structured Procrastination)的論文,受到廣大的迴響,並讓他獲得二○一一年的「搞笑諾貝爾獎」,本書的內容即是建立在該篇論文的基礎之上發展而成。
譯者簡介:
蔡惠伃
台大法律系畢業,現就讀師大翻譯研究所,譯有《零的力量》、《百大CEO都上過的哈佛領導課,你怎麼能不學?》。感興趣的翻譯領域多元,歡迎寫信指教:tsaiatwork@gmail.com
章節試閱
第六章
來自水平式組織人的請求:請正視我們的存在!
左撇子本身沒什麼不好的,但如果全世界以右撇子為中心旋轉,左撇子這時真的會變成殘障人士。光看大學教室裡的課桌椅就知道了,那椅子前方加了塊由左往右掀開,給人寫筆記墊著用的板子。左撇子坐在這種椅子上寫筆記時,她的左手臂不得不懸在空中,再不然就是整個人蜷縮在椅子裡頭,左手臂放在右撇子平常放筆記本的地方,而真正的筆記本被推到右撇子平常放右手臂的板子邊緣。我們可以稱左撇子為「情境性殘障」(situational handicap),意即:當周遭事物以右撇子思維為運作核心...
來自水平式組織人的請求:請正視我們的存在!
左撇子本身沒什麼不好的,但如果全世界以右撇子為中心旋轉,左撇子這時真的會變成殘障人士。光看大學教室裡的課桌椅就知道了,那椅子前方加了塊由左往右掀開,給人寫筆記墊著用的板子。左撇子坐在這種椅子上寫筆記時,她的左手臂不得不懸在空中,再不然就是整個人蜷縮在椅子裡頭,左手臂放在右撇子平常放筆記本的地方,而真正的筆記本被推到右撇子平常放右手臂的板子邊緣。我們可以稱左撇子為「情境性殘障」(situational handicap),意即:當周遭事物以右撇子思維為運作核心...
»看全部
推薦序
拖拖拉拉的迷思
人類天生就是有理智的動物。我們的思辨能力,正是我們的發展之所以能夠迥異於其他動物的原因。這麼說來,我們應該理智非凡才對,我們的每項行為都應該先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再根據深思熟慮的結果,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盡力做到最好。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就曾經困在這個理想的推論之中,但人在現實生活中就是無法達成理想中的結果,以至他們後來將之衍伸成為一個哲學概念:自律欠缺(Akrasia),即人類明明知道最應該要做的事是什麼,卻不做,反而選擇去做別的事情。
「人類是理性的動物,凡事都會仔細思量,計算出...
人類天生就是有理智的動物。我們的思辨能力,正是我們的發展之所以能夠迥異於其他動物的原因。這麼說來,我們應該理智非凡才對,我們的每項行為都應該先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再根據深思熟慮的結果,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盡力做到最好。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就曾經困在這個理想的推論之中,但人在現實生活中就是無法達成理想中的結果,以至他們後來將之衍伸成為一個哲學概念:自律欠缺(Akrasia),即人類明明知道最應該要做的事是什麼,卻不做,反而選擇去做別的事情。
「人類是理性的動物,凡事都會仔細思量,計算出...
»看全部
目錄
致謝 7
導 論 拖拖拉拉的迷思 13
一旦我們了解自己就是所謂的結構式拖拉人,我們不僅會提升自信,同時我們完成工作的能力也會多少有所改善。
第一章 什麼叫作「結構式拖拉」? 21
所有拖拉人都會拖延這拖延那的,而「結構式拖拉」就是一門將這個壞習慣轉化為你做事動力的藝術。……拖拉人很少什麼事都沒做,只不過他們做的是相對不重要的事情而已。
第二章 追求完美的拖拉人 29
拖拉人的完美主義,和是否真的把事情做得完美或者近乎完美無關,而是用你接下的工作去餵養你的幻想,想像自己會把事情做得完美或超棒。 ...
導 論 拖拖拉拉的迷思 13
一旦我們了解自己就是所謂的結構式拖拉人,我們不僅會提升自信,同時我們完成工作的能力也會多少有所改善。
第一章 什麼叫作「結構式拖拉」? 21
所有拖拉人都會拖延這拖延那的,而「結構式拖拉」就是一門將這個壞習慣轉化為你做事動力的藝術。……拖拉人很少什麼事都沒做,只不過他們做的是相對不重要的事情而已。
第二章 追求完美的拖拉人 29
拖拉人的完美主義,和是否真的把事情做得完美或者近乎完美無關,而是用你接下的工作去餵養你的幻想,想像自己會把事情做得完美或超棒。 ...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約翰‧培利 譯者: 蔡惠伃
- 出版社: 臉譜 出版日期:2012-09-28 ISBN/ISSN:978986235212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36頁
- 類別: 中文書> 心理勵志> 職場學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