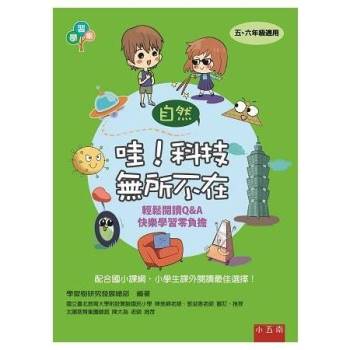擁有最強大的咒術,卻讓我從此無法擁有妳
《骸骨之城》卡珊卓拉.克蕾兒熱情推薦:「危險、黑暗,無懈可擊的奇幻世界。」
◆2010年科克斯書評年度最佳青少年小說◆
◆2010年諾頓文學獎青少年奇幻/科幻小說提名◆
◆2011年美國青少年圖書聯盟年度最佳青少年小說書單◆
◆2011年美國圖書館協會最佳有聲書單◆
◆2012德州圖書館聯盟年度書單◆
★與《骸骨之城》作者同為美國都會奇幻小說界的天才雙姝★
萊拉,我的摯友,我本來以為我殺了她。
媽用手一碰,就讓萊拉愛上了我。但這麼一來卻也讓我永遠、永遠都無法擁有她。
我當時就應該跟她說我愛她的,趁那句話還有意義的時候。
卡瑟並不是沒有咒術能力的普通少年,他的真實身分是七種咒者中最強大、也最罕見的一種──變形咒者。卡瑟的大膽計謀讓兩個哥哥免於遭受最大犯罪家族的報復,也成功救回了變成白貓的萊拉。
但現在一切都毀了。
因為剛出獄的母親多管閒事──對萊拉下咒,讓她愛上卡瑟──他知道他永遠無法真正得到萊拉的心。就在卡瑟極力避開萊拉、希望咒術自然消退時,FBI卻找上他,帶來了噩耗──哥哥菲立普被槍殺身亡,而最大嫌疑犯是監視器畫面中一位戴紅手套的年輕女子。
FBI以威脅卡瑟家人的方式強迫他一起查案。同時,萊拉的父親──東岸最強大的咒者犯罪家族首腦──也積極拉攏卡瑟成為他的手下。
黑白兩邊社會都對他緊追不捨,如果他不加入其中一邊,他的家族與未來就會被摧毀殆盡。
卡瑟知道他沒有選擇的餘地,但他也自有盤算,不會傻傻地讓人牽著鼻子走。他將要揭開有史以來最大騙局的序幕,而賭注就是所有他在乎的人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