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村伊兵衛賞得主 /九○年代揭竿打破性別意識的女性前衛攝影師 唯一散文集
榮獲2010年講談社散文賞、三島由紀夫賞文提名 評審委員盛讚!全員無異議通過!
榮獲2010年講談社散文賞、三島由紀夫賞文提名 評審委員盛讚!全員無異議通過!
封印在記憶深處的幼年風景鮮明地復甦,
曾經放置在一旁遺忘的感情也漸漸被搖動喚醒,
十三篇如珠玉般圓潤的人生故事——背影的記憶。
烙印在孩子的眼裡,那幅哀傷卻又惹人愛憐的家族肖像。
透過影像企圖以「親密」表達「疏離」與「孤獨」,並藉此持續「對人際關係的本質」提出強烈質疑的日本前衛攝影師長島有里枝,在成為母親後,不斷回想起自己的童年。當兒子六歲時,她也會想起自己六歲的情景,但很快就又忘記了。
有一回,她路經惠比壽車站的一個二手書店,在安德魯‧魏斯(Andrew Wyeth)畫冊中,看到一幅名為「克莉絲汀娜的世界」的殘障女子的孤獨背影,頓時感受到時間的凝結,心的節奏也變慢了,想起從小疼愛她的外婆,那個帶她認識世界、給她最大自由、默默守護她的身影。
日本作家角田光代有次看到長島發表的文章非常欣賞,後來兩人有機會合作時,角田便三番兩次地跟長島說:「有里枝,寫點什麼吧!」
原來生命是可以永恆的。書店午后的悸動和角田的鼓勵,讓長島動了以筆代鏡的記錄念頭,「儘管每天日思夜想,外婆的影像還是漸漸稀薄起來。因為這個意念,我不知不覺拿起了照相機,仔細尋索記憶中的景象細部……我在想,有沒有辦法把那些事物源頭的記憶、沒拍到而永遠留在腦海的影像重新顯像呢?已經過去的事物無法留在相片上,但是如果寫成文章,就能把它重現了吧?」於是前後花了四年的時間,寫完她對祖母和家人的記憶。
「敲著鍵盤的過程中,我找尋著對自己而言比真實更在乎的東西。而我感覺找得到,是我曾視若無睹、擱置不理的許多情感。……經由書寫,就像兩支閃光燈,在『我』出生存在的世界,與自己記憶的世界,完全同步的閃了光。」
《背影的記憶》是長島的第一次創作也是唯一散文集,在2010年講談社文學獎評審過程中壓倒性的勝出,全體委員無異議通過,榮獲該年度2010年散文賞。
開啟長島追憶寫作之旅的角田光代感動的說:「不知為何,這本書裡的全部,我全部都懂得。因為太懂了而看得哭了出來。那些回不去的日子,以及那些絕對不會消失的東西被清清楚楚地攤在眼前,我的眼淚為此而流。」
知名攝影家暨作家大竹昭子相知相惜的認為「從攝影出發,並且超越攝影,卻還是讓人感受到攝影感,也只有長島才能做到。」新生代優質演員加瀨亮也以「這散文並非記憶而已,這是結痂之下全新的肌膚。」表達他對長島的推崇。
得獎紀錄
第二屆Urbanart展 Parco賞,一九九三年
木村伊兵衛賞,二○○一年
講談社散文賞,二○一○年
三島由紀夫賞提名,二○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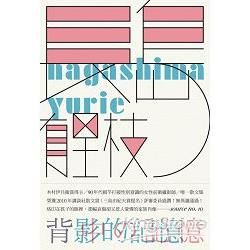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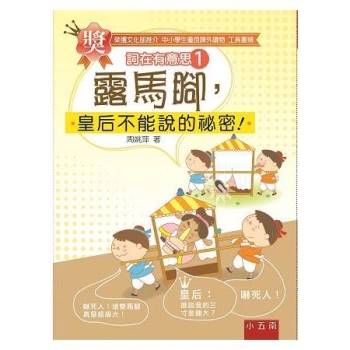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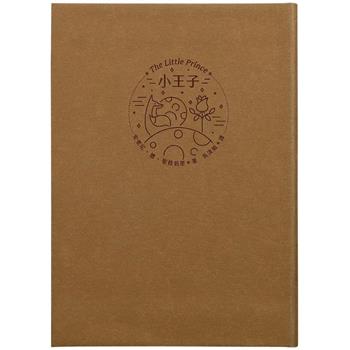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