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知道夜晚躺在自己身邊的人究竟是誰嗎?
「哈蘭.科本是現代懸疑大師。他從第一頁就牢牢抓住你的心,又在結尾帶來震撼。」——丹.布朗
全球貝塔斯曼20家圖書俱樂部共同推薦暢銷作者
作品已在全球三十多個國家、三十二種以上的語言出版發行、
銷量近5000萬冊、20多家圖書俱樂部共同推薦的暢銷作者
《第43個祕密》、《最親密的陌生人》作者、懸疑大師 哈蘭.科本 暢銷力作
★《紐約時報》讚譽為「天才作品」。
★洛杉磯時報、休士頓紀事報、芝加哥時報、費城問訊報、出版商周刊、人物雜誌、出版人周刊、華爾街日報、亞馬遜網路書店等媒體一致好評推薦。
有些過去,不是你不想提起
而是你根本不知道它就在那裡……
九年前,麥特為了朋友失手殺了人。九年後,他服滿刑期,重新開始自己的人生。他找到了穩定的工作,也娶了一位溫柔風趣的女人,她名叫奧麗維亞。在兩人的努力之下,奧麗維亞終於懷了第一個孩子。就在為了慶祝懷孕而買了照相手機的四天後,麥特的手機忽然響起,螢幕上傳來的是一張陌生男子的自拍照,以及一段影片,拍攝地點是一間賓館房間。
麥特一眼認出,那個戴著假髮坐在床上的女人,是他理應正出差到波士頓的妻子……
麥特好不容易聯絡上奧麗維亞,她卻表現出毫不知情的樣子,甚至匆匆掛了電話。既憤怒又憂心的麥特決定找來認識多年的私家偵探,一起追查妻子的動向。原先以為可能是單純外遇,卻在一名警探被謀殺、照片中的男子被槍殺,而麥特的行蹤竟與兩樁命案不謀而合後,事件急轉直下。有著前科的麥特被警方懷疑,他只好踏上逃亡一途,並與私家偵探繼續合力調查真相。但他們發現,這些謀殺案件並不是針對自己,而是下落、身世皆成謎的奧麗維亞……
真相的代價永遠無法預知。
唯一可確定的是,謎底一旦揭曉就無法反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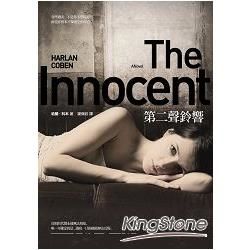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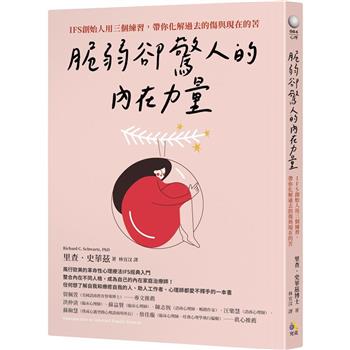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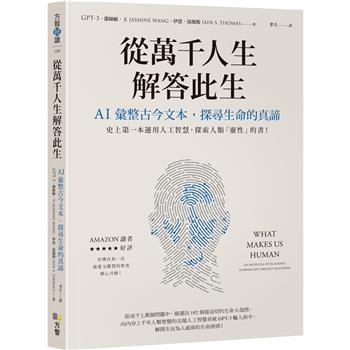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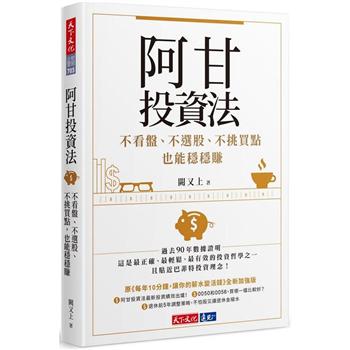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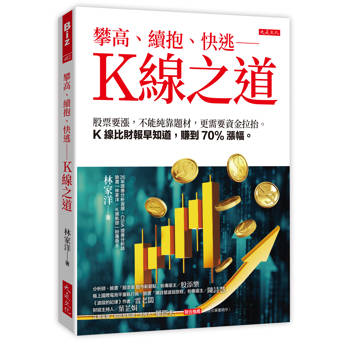






Joyce Brothers說:「愛的最好證明就是信任。」相反的,「猜疑」總是扮演破壞人與人之間彼此情感的頭號兇手。在「真相」尚未揭開之前,我們通常只看見最膚淺的表面,然而大家卻最常在這個階段中做出自以為正確的判斷。因此,緊接著「誤會」的出現,伴隨著憤怒、痛苦、忌妒……等情緒,開始慢慢將「真相」愈推愈遠,造成之間的情感縫隙如山谷般徹底撕裂……。 《第二聲鈴響》考驗著麥特對自己妻子奧麗維亞的信任,是她真有了外遇,還是另有難言之隱的秘密?!麥特選擇信任奧麗維亞並追尋真相,因為他如此深愛著她。但在獲知事情原委後卻不是一切的終結,而是另外生命威脅的開始,因為一件真相背後隱藏更多其他不為人知的陰暗。作者哈蘭.科本擅長緊湊懸疑的精采布局,從《第43個秘密》、《21條左斜線》、《最親密的陌生人》到《第二聲鈴響》,在在讓讀者從一翻開就被帶入那處處充滿吊足胃口、撲朔迷離的情節,過程享受著大呼驚嘆的意外轉折,最後則常帶有溫暖人心的故事結局。如果您喜歡哈蘭.科本的作品,那絕對不能錯過這次最新之作《第二聲鈴響》,一樣會讓您愛不釋手。本書其實是換個名字換間出版社後重新出版的舊書,之前的中譯書名是《無罪之罪》,也許很多讀者已經看過,我必須先提醒。 在閱讀本書之前,我已經看過哈蘭.科本的《第43個祕密》(The Woods)、《死亡印記》(Just one look),加上本書為止,哈蘭.科本的作品沒有讓我失望過,比起勞倫斯.卜洛克而言,可惜的是,台灣讀者對哈蘭.科本相對比較陌生,我想這是多數讀者習慣英美派冷硬警探作風的作品,或者偏向近來主流的北歐推理所致。哈蘭.科本這位比較偏向美式社會心理派別的推理大師,反倒是比較不受台灣讀者的青睞,十分可惜。 哈蘭.科本的作品有著濃濃的日本松本清張的風格,喜歡松本清張日式推理的讀者應該會喜歡他才對,從我已經看過的三部作品歸納出幾點共同風格,他喜歡描寫人們被隱藏的秘密、複雜的背景與不堪的過去,總會去掀開、去面對塵封多年的苦痛,為了守護隱瞞已經快要昭然若現的過往罪惡,走進死胡同的兇手只能不斷自欺欺人甚至殺人滅口。 另一個優點是哈蘭.科本的小說懸疑刺激,佈局及結構不拖泥帶水,結尾時一定給讀者一個大驚奇,讓人很難猜到小說的結局或答案。 哈蘭.科本在開始正式進入主題之前的布局時,多半會先對主要出場人物作個速寫或特寫,如主角的過去與現在、乍看之下毫無關係的週邊人事物描繪,讓讀者對主角有個初步的印象定位,就創做手法來說,這是一種定錨效應,有時會讓讀者更容易進入狀況,但往往也會變成故意誤導讀者思路的狡猾工具。 哈蘭.科本的文字優點還有「有夠會鬼扯」,他不會把全部的篇幅押在男女主角上,反而會放在男女配角或一些小角色上頭,配角的戲份通常不會太小且各各搶戲,大到身世之謎、世代仇恨,小到生活雞毛蒜事、與路人甲的互動,都能寫得活靈活現。 哈蘭.科本出道的時間是36歲,屬於中年出道的作家,出道之前在旅行社工作,為什麼我想提這些?因為中年出道所以比較有社會經驗,作品中會偏向從社會現時面去取材,也因為曾作過旅遊業工作,所以他的作品的角色們都很會跑,一下子東岸、一下子西岸到處跑。反觀23歲就出道的勞倫斯.卜洛克,因為比較缺乏作者工作以外的社會歷練,所以作品會比較不重視社會心理,取材與選角也比較浪漫,如殺手、雅賊或私家偵探,而且主角與故事清一色把場景放在紐約市,連到個紐澤西都會大張旗鼓地描寫「出差之苦」(紐約到紐澤西不過一水之隔)。 回到本書吧!書名The Innocent說明的不可言喻的一切。 主角麥特年輕的時候只因為勸架不小心推了他人一把而造成對方死亡,因此葬送了美好前途,大學生涯被迫中輟而去坐牢,蹲個幾年的苦牢,好不容易出社會混個好幾年,總算找到願意面對他過去的美麗妻子,妻子也懷孕,一切似乎相當美好,麥特擺脫了一切衰運。但有一天,麥特的手機忽然響起,螢幕上傳來的是一張陌生男子與他太太坐在旅館床上的自拍照以及一段影片,他太太理應正出差到波士頓,原本以為只是單純外遇,然而在麥特契而不捨地追查老婆下落的過程中,意外地再度碰到兇殺事件,無辜的麥特一步步地又被捲入成為兇嫌的陷阱。 這是很典型的贖罪-辯解-無罪(或脫罪)的過程,有罪的人須要全新的身份,無罪的人要洗刷冤屈(不管是法律上或內心靈魂上),故事中有幾個經歷贖罪-辯解-無罪過程的角色,除了男主角麥特之外,他的老婆奧麗維亞其實也有著埋著很深很深的過去與傷痛,幾個重要配角們各各都有沈重不堪的過往,有人想要藉由隱藏身份獲得重生的機會,有人處心積慮想要除去過往罪惡的紀錄,也有人背負著身世苦痛默默地在社會角落努力生存著。 看這本書別只從推理或警匪追逐的表面角度切入,若能掌握「贖罪-辯解-無罪(或脫罪)」這個循環去檢視每個角色,便會發現這本書的閱讀層面相當豐富,至少不會陷入勞倫斯.卜洛克作品中那些角色們的無病呻吟與喃喃自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