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被謀殺的男人六年前娶了我的摯愛,但現在所有人都告訴我,我愛的那個女人,從來沒有存在過……
全球發行近5000萬冊,《紐約時報》暢銷榜作家、驚悚懸疑名家
《第43個祕密》、《最親密的陌生人》作者、懸疑大師 哈蘭.科本 暢銷新作
作品以37種以上語言出版發行
美國平均每本發行150萬冊, 全球發行近5000萬冊
全球貝塔斯曼20家圖書俱樂部共同推薦暢銷作者
第一位入選圖書奧斯卡(英國年度圖書獎)的美國人
第一位同時獲得愛倫坡獎、安東尼獎和夏姆斯獎的推理作家
《紐約時報》讚譽為「天才作品」
《紐約時報》10年來首次邀請撰寫小說專欄的作家
「你要保證不跟蹤我們,不打電話,連電子郵件都不寫。答應我你不會來煩我們。」
我會遵守娜塔莉的請求。我會信守承諾。
直到六年後。
六年前,傑克.費雪看著畢生摯愛娜塔莉嫁給另一個男人。而娜塔莉在婚禮後對他下達的禁令,更是徹底粉碎了他的心。六年來,他遵守不打擾她的諾言,隱藏著內心的悲痛,專心在大學母校教書。
六年後,傑克偶然看到了陶德的訃聞,於是懷抱著再見娜塔莉一面的心願,衝動地出席了葬禮。在那裡,他如願看到了陶德的太太……但她不是娜塔莉。更令他震驚的是,他發現這位哀慟的遺孀已與陶德結縭將近二十年,甚至還有兩位青少年孩子。
大惑不解的傑克開始調查,這六年間娜塔莉究竟出了什麼事。但當年兩人共同的朋友不是不知去向,就是根本不認得傑克。就連他們六年前初識的度假村,也彷彿從地表消失一樣,沒有留下任何痕跡,附近居民也從來不知道度假村的存在。傑克深受打擊,甚至連最好的朋友也開始懷疑他是否因為六年前的喪父之痛,才幻想出娜塔莉的存在,以彌補內心的空洞……
但傑克堅持自己沒有發瘋,誓言找出這位曾經撕裂他的心的女人。但不久之後,不明人士開始一一找上門來,威脅取他的性命,傑克才發現,這六年的空白和痛苦,可能都出自於一場精心策劃、規模龐大的陰謀……
哈蘭•科本又一次帶給讀者令人心驚肉跳的引人入勝作品,靈巧地探討愛的力量,以及這樣的愛可能潛藏了什麼足以致命的祕密與謊言。
失去的愛有多深刻、多熾烈
藏在其中的感情就有多危險、多強大……大到足以改變生命的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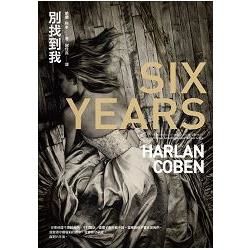
 2015/09/19
2015/09/19 2015/09/08
2015/09/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