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野圭吾最推崇的推理小說大師——派翠西亞.康薇爾
最暢銷的經典法醫小說系列,全球銷售突破一億冊
翻譯為三十六國語言、熱銷一百二十國
最暢銷的經典法醫小說系列,全球銷售突破一億冊
翻譯為三十六國語言、熱銷一百二十國
經典法醫小說系列新裝出場第二彈《肉體證據》——
《紐約時報》暢銷榜冠軍
為美國奪得第一座金匕首大獎
美國文學會X雙日X推理協會三大讀書俱樂部選書
我是貝蘿。我是絲卓。我很恐懼。
每當我聽到電話鈴響,我就會想起來。
每當我聽到有人走在我後面,我就會回頭。
一到晚上,我就會查看我的衣櫥、窗簾後面、床底下,然後拿一張椅子架在門後面。
天啊!我不想回家。
才華洋溢的女作家貝蘿為了躲避變態男子如影隨形的監視和電話騷擾,倉皇逃往佛羅里達的小島,過著避人耳目的生活,一邊寫作。然而,就在她旅費用鑿、被迫返家的當晚,即被人發現陳屍家中,身體佈滿刀痕、面目全非。
女法醫凱.史卡佩塔隨著馬里諾副隊長一同調查此案的同時,發現貝蘿那份近來引發相關人士不滿、擔憂的自傳手稿,竟不翼而飛。不久,曾與她關係密切、卻因自傳而決裂的普立茲文學奬得主也在自家門口慘遭殺害,死狀悽慘。
就在案情越來越錯綜複雜的時候,史卡佩塔發現,貝蘿生前經歷的恐懼困境也開始重現在她身上⋯⋯
獨居的你一定要知道的自保之道:
■開車前先把鑰匙拿出來,並看一下車底
■有人跟蹤時,把車開到最近的消防隊
■把習慣打亂,別固定去同一家商店
■不要讓不認識的人進門
■不要等天黑了或沒人了才離開辦公室
■千萬不要喝醉了睡覺,因為你不知道誰會上門來……
得獎紀錄
文學史上首位甫出道便在一年內囊括五項歐美重量級獎項的作家——
1990年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約翰.克雷西獎
1991年國際推理讀者協會麥卡維帝獎最佳首作
1991年美國推理作家協會愛倫坡獎最佳首作
1991年鮑查大會安東尼獎最佳首作
1991年法國Roman d’Aventures大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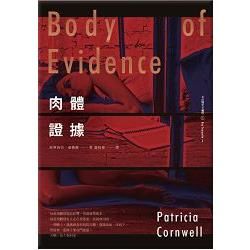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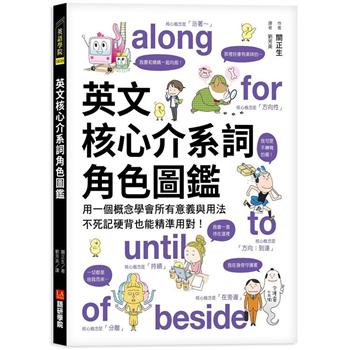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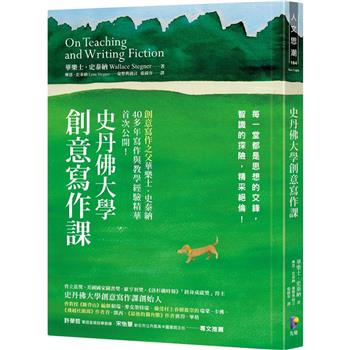








《肉體證據》是作者派翠西亞.康薇爾所著女法醫 史卡佩塔系列中的第二本,亦是臉譜出版社重新印刷再版的作品。對於女法醫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泰絲.格里森筆下的靈魂人物--莫拉,與派翠西亞.康薇爾塑造的女法醫史卡佩塔兩者間有著共同的特徵,只要有她們的地方都充滿著血腥、懸疑和死亡,而她們聰慧過人的判斷與鍥而不捨的追查,使她們成為無可取代的死者代言人。但兩者也有極大的差異,如果要以優劣分,莫拉將獲得最高分,而史卡佩塔則略遜一籌,因為在展現法醫專業程度上前者發揮較為精湛深入且精彩,後者的著墨就顯得薄弱了。 「一件事總是牽連著另外一件事,邪惡之事都其來有自。」現場一樣稀有又關鍵的纖維,牽扯出一串串看似遙遠卻又相關的連結,拉著讀者的思緒陷入謎團的濃霧。緊湊的劇情,高度的懸疑,錯縱複雜的轉折讓《肉體證據》充滿閱讀的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