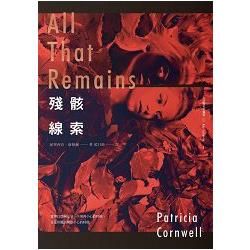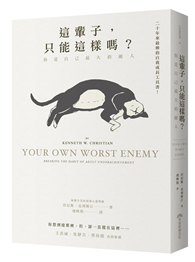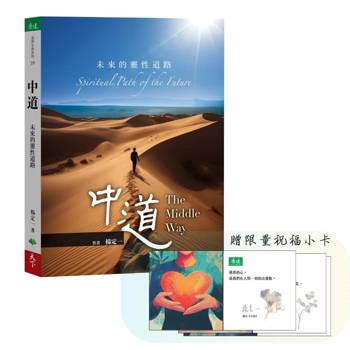東野圭吾最推崇的推理小說大師——派翠西亞.康薇爾
最暢銷的經典法醫小說系列,全球銷售突破一億冊
翻譯為三十六國語言、熱銷一百二十國
繼《屍體會說話》後,再次向謎題極限挑戰的連續殺人案件!
當你以為夠安全、不用再小心的時候,正是你應該開始小心的時候——
第五對情侶失蹤了
開心出門的年輕男女、憂心至狂的父母
棄置的空車、顫抖的警犬,與只剩枯骨腐肉的八具殘骸
還有什麼線索是法醫可以提供的,
除了幾近直覺的不祥預感以外──
布魯斯與茱蒂、吉姆與波妮、班與卡洛琳、蘇珊與麥克,四對情侶,八個花樣年華的年輕人,他們開開心心的駕車出門,然後只剩車子、鑰匙、個人物品留在車上……
幾個月後,失蹤的年輕人出現在樹林中,卻已成了殘破腐爛的屍體。家人、親友的痛哭傷心,警方的無奈焦躁,看在女法醫史卡佩塔的眼裡,也只是更添無力。因為這名凶手顯然夠精明,選了跨區地點棄屍,更增添警方管轄、蒐證與分工上的困難,而屍體腐爛的程度更是讓史卡佩塔連死因都難以確定。
不過,眼前的大麻煩是,最新一樁失蹤案的女孩,居然是知名反毒政治人物──「毒品沙皇」珮德.哈韋的女兒。一向趾高氣昂的國家毒品政策執行長珮德.哈韋找上史卡佩塔,請她務必協助找回女兒。但是史卡佩塔擔心的是,或許他們再次見面的地點會是停屍間。況且,以哈韋的工作內容看來,她女兒身陷危機的原因很有可能是政治鬥爭?又或是小情侶受不了家長干涉,約好私奔?還是年輕孩子以身試毒,卻誤踩毒窩,惹禍上身?!
猜測、較勁、爭論之際,史卡佩塔逼近了事件的真相,卻懷疑起身邊每一個人。所幸眼前出現一張指引她的紙牌──紅心J,這是每個案件中都存在卻被隱瞞的一個共同點。然而,瘋狂的母親、別有用心的官僚角力之下,她的立場與安危也陷入空前的危機之中……
文學史上首位甫出道便在一年內囊括五項歐美重量級獎項的作家——
1990年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約翰.克雷西獎
1991年國際推理讀者協會麥卡維帝獎最佳首作
1991年美國推理作家協會愛倫坡獎最佳首作
1991年鮑查大會安東尼獎最佳首作
1991年法國Roman d’Aventures大獎
作者簡介:
派翠西亞.康薇爾(Patricia Cornwell)
一九五六年出生於邁阿密。她的職業生涯從主跑社會新聞的記者開始,一九八四年在維吉尼亞州的法醫部門擔任檢驗紀錄員。一九八四年~八六年間,康薇爾根據自身的法醫工作經驗寫下了三本小說,然而一開始的出書過程並不順利。
後來,康薇爾聽從建議,推翻原本以男性偵探為主角的構想,改以女法醫為主軸,終於在一九九○年出版了她的第一本推理小說《屍體會說話》,結果一炮而紅,為她風光贏得一九九○年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約翰.克雷西獎。一九九一年,此書榮獲一九九一年美國推理作家協會愛倫坡最佳首作、國際推理讀者協會麥卡維帝獎最佳首作、鮑查大會安東尼獎最佳首作,以及一九九一年法國Roman d’Aventures大獎。
譯者簡介:
藍目路
台東縣池上鄉人。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現於英國攻讀博士學位。曾譯有《法蘭柴思事件》、《暗室》。
章節試閱
星期六,八月最後的一天。我從破曉一直工作到下午兩點,才回到家。柏莎正在廚房忙碌的打掃。她每星期六來幫我整理一次,並早已習慣不去理會電話鈴聲。這會兒,電話正響著。
「我不在,」我大聲叫著打開冰箱。
柏莎停止打掃。「一分鐘前就響過了,」她說:「幾分鐘前也是,同一個男人。」
「沒人在家啦。」我重複。
「隨便你,凱醫生。」拖把拖過地板的聲音再度響起。
我試著不去理會答錄機轉動的聲音,但那無形無體的聲音卻霸氣的入侵陽光滿室的廚房。
答錄機在「嗶」一聲後,傳來一個熟悉的男性聲音。「醫生?我是馬里諾……」
喔,老天爺,我叫著,順便把冰箱的門用屁股「砰」的一聲關上。
「我一直試著跟你連絡,但現在必須出門,請用傳呼機跟我連絡……」馬里諾的聲音聽來很緊急,我一把抓起話筒。
「我在這兒。」
「真的是你,還是答錄機?」
「猜猜看。」我回答。
「壞消息。他們發現另一輛被棄置的車子,在紐肯特,第六十四號公路往西的休息站。班頓剛找到我──」
「另一對?」我打岔。
「弗瑞德.柴尼,白人男性,十九歲。黛伯拉.哈韋,白人女性,十九歲。最後被看到的時間是昨晚八點左右,當時他們正從里奇蒙市的哈韋家開往司平得弗方向。」
「而他們的車是在往西邊的公路上被發現?」我問,司平得弗位於北卡羅萊納州,在里奇蒙市東方約三小時半車程處。
「是的。他們顯然往反方向走,似乎要回到市內。一位州警在一個鐘頭前發現那輛車子,是部吉普車,還沒找到人。」
「我現在就過去。」我告訴他。
我抓起皮包,衝向我的車子,一股懼意涼颼颼的爬上背脊。
截至目前為止,已經有四對了。每一對都是先報失蹤,接著被人發現陳屍在威廉斯堡方圓半徑五十哩範圍內。
這些案件的凶手,如今已被媒體封為「情侶殺手」。整個案情相當撲朔迷離,叫人難以理解,沒有任何線索或可靠的推測。即使聯邦調查局或其轄下之暴力罪犯逮捕計畫利用智慧型電腦比對失蹤人口、連續犯等資料,都無法提供有效資訊。兩年多前,當第一對屍體被人發現後,聯邦調查員班頓.衛斯禮和里奇蒙市的凶殺組刑警老鳥彼德.馬里諾組成的暴力罪犯逮捕計畫,就應地方警局的請求前往協助調查。接著,另一對宣告失蹤,隨後又有兩對。每一次的情形都是︰當暴力罪犯逮捕計畫接到消息,迅速連絡全國犯罪資料中心開始連上全美各地警察局追尋線索時,就發現失蹤的青少年已慘遭謀殺,屍體棄置在樹林裡任其分解腐化。
我經過公路收費亭,關掉車裡的收音機,猛踏油門往六十四號公路急駛而去。這時腦中湧上一堆圖像,夾雜著一團聲音。支離骨頭、腐朽衣物混雜在落葉堆裡。報紙上印出來一張張可愛且笑容滿面的年輕臉龐,電視上記者訪問著不知所措、痛心憂傷的家人,以及那些找我的電話。
「我很遺憾那些事發生在你女兒身上。」
「請你告訴我,我的孩子是怎麼死的。喔,老天爺呀,她是否受了很多苦?」
「她的死因目前尚無法確定,班納特太太。我實在無法在這個階段提供你任何進一步的消息。」
「你說你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馬丁先生,他整副軀體只剩骨架,當軟組織腐化後,所有可能的傷口也消失了……」
「我不是來聽你講那些醫學狗屎!我只要知道是什麼殺了我的兒子!警方在問有關嗑藥的問題!我兒子從來沒有喝醉過,更別說嗑藥了!你聽清楚了嗎?他死了,而他們卻想把他變成一個不學無術的壞蛋……」
「首席法醫的迷思:凱.史卡佩塔醫生無能辨別死因。」
無法確定。
一次又一次,八個年輕人了。
這實在很糟糕。真的,對我而言,這種情形實屬前所未有。
每一個法醫都多多少少會接到一些無頭案件,但像我眼前這樣互相牽連的倒還真不多見。
紐肯特郡的六十四號休息站,就像維吉尼亞州中任何一個休息站一樣,有野餐桌、燒烤爐、木製垃圾桶、磚砌洗手間和販賣機,還有新栽植的樹木,但眼前目光所及之處,沒有一名旅客或卡車司機,倒是警車隨處可見。
一名穿著藍灰色制服、滿臉嚴厲毫無笑容的州警,走向正把車駛近女用洗手間的我。
「對不起,女士,」他俯身靠向開著的車窗,說「休息站今天暫時關閉,我得請你繼續往前開。」
「凱.史卡佩塔醫生,」我表明身分,將車子熄火。「警方請我過來。」
「為了什麼呢?」
「我是首席法醫,」我回答。
我可以感受到他眼神裡充滿了不信任。是啦,我是看起來一點兒也不像什麼「首席」。我身上穿的是件石洗的丹寧布裙,粉紅布質襯衫,腳上是雙皮製登山靴,全身上下沒有一點兒標示著權威,包括我的車,也不過是一輛等著進廠換輪胎的老爺車。乍看之下,我像是個不怎麼年輕的雅痞,迷亂的頂著個泛灰金髮,開著黑灰色的賓士車往商場駛去。
「我需要看看你的證件。」
我在手袋裡翻了一會兒,拿出一個薄薄的黑色夾子,打開裡頭黃銅盾紋證件,再拿出駕照遞給他。他研究了好一陣子,我可以感覺到他有些尷尬。
「史卡佩塔醫生,請把你的車子停在這,你要找的人在後面。」他指著大型車輛停車場的方向。「祝好運。」他無意義的補充,然後舉步離開。
我循著磚道往前走,繞過建築物,經過一叢樹影,眼前出現了更多警車,還有一輛閃著燈的拖吊車,和至少一打以上穿著制服和便服的人們。但直到來到近前,我才發現那輛兩門吉普車。它躺在出口彎道的中途,偏離道路的斜坡上,隱身於濃密樹叢之後,車身披蓋著一層灰塵。我從駕駛座車窗向裡看,發現灰褐色皮革裝飾的車內非常乾淨,後座整齊的堆疊各種行李,有彎道用滑雪橇、捲成一圈的黃色尼龍滑橇繩,和紅白相間的塑膠冰櫃。鑰匙懸吊在發動孔上,窗戶都半開著。從車道往草坡上去的方向留下兩道明顯的車輪痕跡,車子前端的鉻鋼護柵被茂密的松樹叢往上擠壓了。
馬里諾正在跟一位瘦長的金髮男子說話,那是在州警局任職的傑.摩瑞,我並不認識他。但他看來像是掌局的人。
「凱.史卡佩塔,」我自報姓名,馬里諾從來只稱我「醫生」。
摩瑞抬起他墨綠色的雷朋太陽眼鏡朝我看了看,又點了點頭。他身著便服,還炫耀性的擺弄看來只比青少年絨毛厚一些的鬍髭,整個人籠罩在我相當熟悉的那種新官上任的虛張聲勢裡。
「我們目前只知道,」他神經兮兮的環視四周,「吉普車是黛伯拉.哈韋的,她和她的男朋友,嗯,弗瑞德.柴尼,昨晚大約八點鐘左右離開哈韋家。他們開車前往司平得弗,哈韋家在那兒有棟海濱別墅。」
「這對年輕人離開里奇蒙時,哈韋家有沒有人在?」我詢問。
「沒有。」他簡短的望向我這邊。「他們都已經在司平得弗,那天稍早先出發的。黛伯拉和弗瑞德想自己開車前往,因為他們計畫星期一就回里奇蒙。他們倆人是卡羅萊納大學的學生,需要早點回去準備課業。」
馬里諾熄掉香菸解釋道,「昨晚他們出發前曾打電話到司平得弗,告訴黛伯拉的一個弟弟說他們正要出發,預計在午夜和凌晨一點之間到達。但直到今天清早四點鐘他們都沒有出現,接著珮德.哈韋就通知了警方。」
「珮德.哈韋!」我不可置信的看著馬里諾。
摩瑞警官回答我,「沒錯。我們碰上了個好案子。珮德.哈韋現在就正在往這兒的途中。一架直升機──」他看了看手錶,「約在半小時前過去接她。至於父親呢,嗯,鮑伯.哈韋,因公在外,本來預計明天會到達司平得弗。就我們所知,尚未連絡上他,所以他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珮德.哈韋是國家毒品政策執行長,被媒體稱為「毒品沙皇」。她被總統授命任職,前不久才上了《時代雜誌》的封面。哈韋太太可以說是當今美國最有影響力,也最受尊崇的女人之一。
我轉過身看見班頓.衛斯禮瘦長、熟悉的身影,打男生廁所方向走來,很勉強的跟我們打了個招呼。他太陽穴上的銀髮溼漉漉的,藍色西裝翻領上有著點點水漬,看起來像剛用水洗過臉。他目無表情的瞪著那輛吉普車,再從胸前口袋拿出一副太陽眼鏡戴上。
「哈韋太太到了沒?」他問。
「沒有,」馬里諾回答。
「記者呢?」
「沒有,」馬里諾說。
「很好。」
衛斯禮的嘴抿得很緊,讓他那有稜有角的臉看起來比平常更嚴峻、更難親近。他如果不是老掛著那一副冷硬的表情,應該可以稱得上俊美。他的思想和情緒也往往叫人捉摸不清、無從猜測,而近來更變本加厲的成為隱藏自我情緒的高手,讓我幾乎完全無法了解他。
「我們要盡可能的封鎖這個消息,」他繼續道。「一旦消息走漏,事情就會變得更加棘手。」
我問他,「班頓,你對這對年輕人知道多少?」
「相當少。哈韋太太今早報的案,她打電話到局長家裡,局長再打給我。她女兒和弗瑞德.柴尼在卡羅萊納大學認識,大一起就開始交往。據聞這兩人都算是好孩子,沒有不良記錄,也沒有什麼招惹麻煩的歷史──至少哈韋太太是這麼說。不過,我倒是發現一件事,她對於他們的交往有些矛盾的情緒,她認為她女兒和柴尼單獨相處的時間太多了。」
「那也許可以說明為什麼他們要自行開車到海邊去,」我說。
「是的,」衛斯禮回答,同時環顧四周。「也許那就是理由。從局長的轉述中我得到的印象是,哈韋太太不太高興黛伯拉帶她的男朋友到司平得弗去,那原是個家庭聚會。哈韋太太星期一到星期五都住在華盛頓,這個夏天她並沒有多少機會跟她的女兒和兩個兒子相處。老實說,我覺得黛伯拉和她母親的關係近來也許並不融洽,而且很可能昨天早上全家人在離開北卡羅萊納時發生過爭執。」
「那兩個小鬼一塊私奔的機會有多大?」馬里諾說。「他們很聰明的,不是嗎?他們也許看了報紙、新聞,尤其看到近來有關這些情侶案件的電視特別報導。重點是,他們也許知道這些案件就發生在這附近。誰敢保證他們沒有可能這樣做?一個狡猾、有計畫的失蹤,為的是想為難父母。」
「這是我們要考慮的眾多可能性之一,」衛斯禮回答。「也因為這樣,我希望盡可能的不讓新聞界知道這個案件。」
當我們走向出口彎路上的吉普車時,摩瑞加入我們。另外有兩位身著暗色連身衣、長靴的一男一女,從一輛淺藍色敞篷小型貨車裡下來。他們打開車尾橫板,兩隻急促喘著氣、興奮搖著尾巴的獵犬跳出牠們的籠子。他們接著把長長的狗鏈扣在他們腰間的皮帶上,再抓住兩隻狗的項圈。
「鹽巴、海王星,我們走!」
摩瑞對牠們露齒一笑,並伸出手來。「你們好呀,小傢伙們!」
狗教練從約克鎮來,叫傑夫和吉兒。
「沒人動過,」馬里諾告訴他們,一邊彎下身來撫弄狗兒們耳後的頸子。「我們還沒有開過車門。」
傑夫緊抓住架在狗身上的行頭,吉兒繼續詢問,「你們可有什麼東西能讓狗兒聞氣味用?」
「已經要求珮德.哈韋帶些黛伯拉最近穿過的衣服來了。」衛斯禮說。
如果說吉兒對她要找的是誰的女兒感到驚訝的話,她可是一點也沒顯現出來,只定定的看著衛斯禮說下去。
「她搭直升機過來,」衛斯禮道,看了一眼手錶。「應該快到了。」
「好吧,只要注意不要讓那隻大鳥在這裡降落就行了,」吉兒邊指示著,邊走向吉普車。「最怕的就是打亂現場。」透過駕駛座邊的窗子,她察看著車門的裡側,一寸不漏的研究著。然後稍微退後一些,再久久注視著車門外側上黑塑料製的把手。
「也許最好用裡面的座椅,」她決定著。「我們會讓鹽巴聞一個,海王星聞另一個。但首先,我們必須想辦法在不破壞任何東西的情況下進到車裡去。有人有鉛筆或鋼筆嗎?」
衛斯禮從胸前襯衫口袋裡掏出一支原子筆交給她。
「還要一支,」她再說。
「折疊式小刀怎樣?」馬里諾伸手到他牛仔褲袋裡。
「太好了。」
吉兒接著一手握著瑞士刀,一手握著筆,一邊壓著駕駛座旁車門外側把手上的拇指凹點部位,同時拉開把手,然後以腳尖擠進被拉開出縫隙的車門,輕輕把門拱開。這時我聽到直升機螺旋槳轟隆轟隆的聲音由遠而近,越來越清晰。
不一會兒,一架紅白相間的直升機盤旋在休息站上空,像隻蜻蜓般翱翔,在地面引發小小龍捲風。地面上所有的聲音都被掩蓋住,咆哮而起的風搖晃著群樹,更在草地上吹皺起一圈圈漣漪。吉兒和傑夫半瞇著眼睛,蹲坐在狗旁,緊緊的抓住狗的項圈。
珮德.哈韋出任國家毒品政策執行長之前,是里奇蒙市的州檢察官,然後升任為東維吉尼亞區的聯邦檢察官。我曾解剖過由她負責的幾件引起公眾注意的毒品案裡的被害人,但我從未被要求出庭作證;只有引用我的檢驗報告,因而哈韋太太和我還沒真正見過面。
電視中和報紙照片上的她看起來一派女強人模樣,親眼見到她,卻多了些女性的柔婉,非常吸引人。瘦長,身軀完美,陽光把她紅褐髮上的金色和紅色反映得鮮明亮麗。衛斯禮一一介紹我們,哈韋太太帶著政治人物久經訓練的適度禮儀和自信同每人握手。但她臉上沒有笑容,也沒有和任何人的眼神交會。
「這裡有件上衣,」她說,把一個紙袋交給吉兒。「我在海灘別墅,黛比的房間找到的。不知道她最後一回穿是什麼時候,但我想這件最近沒洗過。」
「上回你女兒是什麼時候到海灘別墅?」吉兒問,沒有馬上打開紙袋。
「七月初。她和幾個朋友到那兒度週末。」
她眼光穿過我們,看向車門敞開著的吉普車,短暫落在發動孔上的鑰匙,鑰匙鍊上懸掛著一個銀製D字母墜飾。有好一會兒大家都沒說話,我可以看到她力圖避免驚慌的情緒掙扎。
她轉向我們說,「黛比應該帶著一個錢包,尼龍質料,鮮紅色,就是那種用魔鬼膠開合的體育用品店買的錢包。你們有沒有發現它?」
「沒有,夫人,」摩瑞回答。「還沒有發現那樣的東西。但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只是從車外往裡看,還沒有在車裡搜尋,我們等著救援狗來。」
「你最後和她的談話中,她的心情怎樣?」馬里諾問。
「昨天早上我和我兒子們出發前往海灘別墅前,我們說了幾句話,」她以平和安靜的聲音回答。「她對我很不滿。」
「她知道這附近發生的事嗎?知道那些失蹤的情侶嗎?」馬里諾問。
「當然,我們曾談過那些事,猜想他們可能的行蹤。她知道這些案子。」
吉兒對摩瑞說:「我們應該開始了。」
「好主意。」
「最後一件事。」吉兒看著哈韋太太。「你知道是誰開的車嗎?」
「弗瑞德,我猜,」她回答。「通常他們如果一塊到什麼地方,都是他開車。」 吉兒點點頭說:「我需要再用一次那把小刀和筆了。」
從衛斯禮和馬里諾處借到後,她繞到駕駛座另一側,將車門打開。她抓住一隻獵犬的項圈。狗兒急切的跳上車,完美的配合著女主人的行動;牠到處嗅著,鬆垮發亮的皮毛下,矯健的肌肉一圈圈的波動著;耳朵沉重下垂,好像懸掛著鉛錘似的。
「加油,海王星,讓我們看看你神奇的鼻子有多厲害。」
我們靜靜的看著,她引導著海王星去嗅黛伯拉.哈韋昨天可能坐過的椅子。突然間,牠嗥叫起來,像是乍然見到響尾蛇般,猛然跳出吉普車,激烈扭動身軀,力量大到吉兒幾乎無法抓住項圈。牠把尾巴緊緊夾在後腿間,背上的毛一根根的豎立著,一股寒意冷冷的沿著我的背脊爬上來。
「噓,乖,噓!」
海王星全身顫抖,嗚咽抽噎著。
星期六,八月最後的一天。我從破曉一直工作到下午兩點,才回到家。柏莎正在廚房忙碌的打掃。她每星期六來幫我整理一次,並早已習慣不去理會電話鈴聲。這會兒,電話正響著。
「我不在,」我大聲叫著打開冰箱。
柏莎停止打掃。「一分鐘前就響過了,」她說:「幾分鐘前也是,同一個男人。」
「沒人在家啦。」我重複。
「隨便你,凱醫生。」拖把拖過地板的聲音再度響起。
我試著不去理會答錄機轉動的聲音,但那無形無體的聲音卻霸氣的入侵陽光滿室的廚房。
答錄機在「嗶」一聲後,傳來一個熟悉的男性聲音。「醫生?我是馬里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