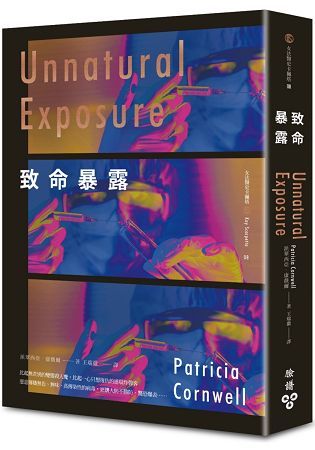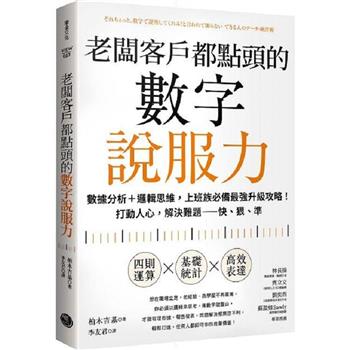比起無差別的變態殺人魔
比起一心只想復仇的連環炸彈客
惡意傳播無色、無味、高傳染性的病毒
更讓人防不勝防、驚恐爆表……
維吉尼亞州的垃圾掩埋場發現了一具遭到肢解的殘骸,手法與近來發生的連續殺人案十分類似。消息傳出後再次引發居民極度恐慌。這件案子困擾著大西洋兩岸的警方,凶手犯案時間長達十餘年,地點從早先的愛爾蘭,轉移到近年來的維吉尼亞州。不幸的是,警方握有的線索非常有限,凶手依然逍遙法外。就在女法醫史卡佩塔為了新受害者不完全符合舊有的作案模式而感到困惑之際,凶手卻大膽的透過網路寄給她彷如第一現場的照片,直接向她挑戰。
新受害者陸續出現,然而這一次令人驚駭的已不是個別受害者的淒慘遭遇,而是遍布死者身上的那些膿疱--疑似傳染性極強但絕跡已久的天花病毒造成的症狀。站在第一線工作的史卡佩塔首當其衝面臨感染的危險,若不盡快採取行動,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下個犧牲者,疫情一觸即發……
最暢銷的法醫小說系列,全球銷售突破一億冊!
翻譯為三十六國語言、熱銷一百二十國
刑事鑑識與法醫探案的先驅,「CSI犯罪現場」相關熱門影集取材原點
超越《屍體會說話》,挑戰鑑識科技極限之作!
「情節持續緊繃……令人凝神屏息……史卡佩塔再度出擊並且躍上顛峰……冷靜、絕不屈服﹔憑藉比史崔克電鋸更為犀利的敏銳直覺,這位法醫病理專家四處奔波追蹤疑似天花的不明病毒,強悍引人的性格統馭著整篇小說。」
──《紐約時報書評》
「極度悚慄……近乎超現實的開場令康薇爾這部最新的凱‧史卡佩塔法醫推理小說即刻緊攫讀者的心,並流露豐富的文學感性……讓我們再次見識到這位法醫令人激賞的膽識和才氣。」
──《舊金山紀事報》
「這是康薇爾自《波特墓園》以來又一傑作,通篇充斥一股詭密的陰暗氣息……在康薇爾的小說裡,謀殺乃是法醫內心深層惡魔的具體呈現……史卡佩塔心中近乎偏執的強烈恐懼將她的世界推入鬼魂出沒的歌德式超現實氛圍當中。」
──《亞特蘭大立憲報》
「康薇爾直探犯罪辦案的精髓……卓越的賞心之作……康薇爾深諳推理書寫之妙……『她』擁有讓受害者遺留的細微線索變得引人入勝且極具說服力的獨特稟賦。」
──《今日美國》
女法醫史卡佩塔系列作家 Patricia Cornwell
文學史上首位甫出道便在一年內囊括五項歐美重量級獎項的作家——
1990年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約翰.克雷西獎
1991年國際推理讀者協會麥卡維帝獎最佳首作
1991年美國推理作家協會愛倫坡獎最佳首作
1991年鮑查大會安東尼獎最佳首作
1991年法國Roman d’Aventures大獎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致命暴露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00 |
二手中文書 |
$ 283 |
推理 / 驚悚小說 |
$ 284 |
驚悚/懸疑小說 |
$ 284 |
西洋驚悚/恐怖小說 |
$ 306 |
小說/文學 |
$ 316 |
中文書 |
$ 324 |
美國文學 |
$ 324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圖書名稱:致命暴露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派翠西亞.康薇爾 Patricia Cornwell
一九五六年出生於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她的職業生涯從主跑社會新聞的記者開始,一九八四年在維吉尼亞州的法醫部門擔任檢驗記綠員。一九八四~八六年間,康薇爾根據自身的法醫工作經驗寫下了三本小說,然而出書過程並不順利。
後來她聽從建議,推翻原本以男偵探為主角的構想,改以女法醫為主軸,終於在一九九○年出版了她的第一本推理小說《屍體會說話》,結果一炮而紅,為她風光贏得一九九○年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約翰.克雷西獎,一九九一年美國推理作家協會愛倫坡獎最佳首作、國際推理讀者協會麥卡維帝獎最佳首作、鮑查大會安東尼獎最佳首作,以及一九九二年法國Roman d’Aventures大獎。
一九九三年,康薇爾再以《失落的指紋》拿下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代表年度最佳小說的金匕首獎。系列作品中的主人翁凱.史卡佩塔醫生,則在一九九九年獲頒夏洛克獎最佳偵探獎。
派翠西亞.康薇爾目前擔任國家法醫學院,應用法醫科學部門的主任。
一九五六年出生於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她的職業生涯從主跑社會新聞的記者開始,一九八四年在維吉尼亞州的法醫部門擔任檢驗記綠員。一九八四~八六年間,康薇爾根據自身的法醫工作經驗寫下了三本小說,然而出書過程並不順利。
後來她聽從建議,推翻原本以男偵探為主角的構想,改以女法醫為主軸,終於在一九九○年出版了她的第一本推理小說《屍體會說話》,結果一炮而紅,為她風光贏得一九九○年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約翰.克雷西獎,一九九一年美國推理作家協會愛倫坡獎最佳首作、國際推理讀者協會麥卡維帝獎最佳首作、鮑查大會安東尼獎最佳首作,以及一九九二年法國Roman d’Aventures大獎。
一九九三年,康薇爾再以《失落的指紋》拿下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代表年度最佳小說的金匕首獎。系列作品中的主人翁凱.史卡佩塔醫生,則在一九九九年獲頒夏洛克獎最佳偵探獎。
派翠西亞.康薇爾目前擔任國家法醫學院,應用法醫科學部門的主任。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