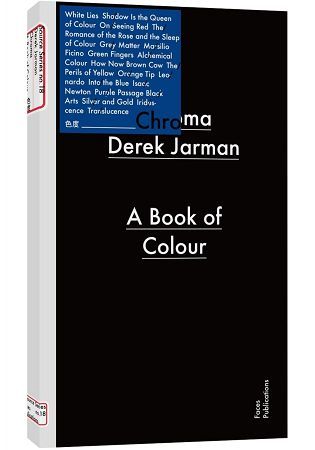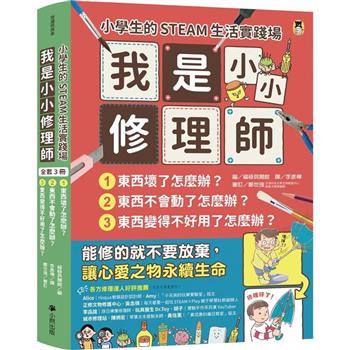英國二十世紀最具爭議性的視覺藝術家
以不絕的啟程移動力,探討生理視力(sight)與感悟視域(vision)的關聯性
在逐步走向失明之際,以詩人的情懷帶領你╱我重新審視這個多彩世界
反思我們「看到了什麼?」
賈曼唯一中文繁體版著作,轟動全世界的電影《藍》,出自本書第13章〈進入藍色Into the Blue〉
◆賈曼私筆記《色度》裝幀製作設計特色
●全書採用日本進口美術紙
●內文雙特色印刷
●書口不規則紙邊+紗布紙裸背廣開穿線裝訂+5特製貼紙完整呈現筆記感
賈曼,英國前衛的同志電影大師,1960年進入倫敦國王學院唸藝術史,1963-1967年在斯萊德藝術學校攻讀繪畫。第一次接觸到電影,是為肯•羅素(Ken Russell)的電影《魯登的惡魔》(The Devils,1971)擔任藝術總監。70年代開始進入電影圈,繪畫的薰陶使得賈曼有別於傳統的導演,對電影形式和傳達思想的在意勝過故事情節,喜歡用最原始的攝影機拍攝超8毫米的實驗性短片。賈曼也發表裝置藝術作品,擔任歌劇舞台設計,除了電影,他也為當時的流行歌手和樂團拍攝了大量的Video,如英國知名樂團寵物店男孩(Pet Shop Boys)、Orange Juice、The Smiths等。
對於政治、性、權利、死亡、慾望和生命的探討,是賈曼電影永恆的主題。詩意的作品中包含著對社會公共議題的強烈指涉。開啟巴洛克時代的義大利畫家卡拉瓦喬(Caravaggio),是賈曼景仰的畫家之一,他在1986年用顛覆性的手法拍攝了《浮世繪》(Caravaggio),片中光影和構圖的設計採用了卡拉瓦喬的明暗繪畫法。這部宛如卡拉瓦喬傳的作品,在1987年獲得了第36屆柏林電影節銀熊獎,讓賈曼聲名大噪。
1993年威尼斯雙年展上首映,引起了世界性轟動的《藍》,是電影史上的一個重要文本,也是賈曼在藝術上的最後一次創新。這部電影構思了將近二十年,緣起於泰德現代美術館在1974年3月推出的法國先鋒藝術家伊夫•克萊因(Yves Klein)作品展。賈曼參觀展覽之後在筆記本上寫下:為伊夫•克萊因做一部藍色電影。
1994年,賈曼因愛滋病去世。他不僅敢於面對自己的性向,終其一生也都在為同性戀者的權利奔走,是少數贏得世界尊敬的電影導演,前衛藝術家們和年輕同性戀者們的偶像。與賈曼合作最久的影后蒂妲•絲雲頓曾表示:「如果上帝沒讓我遇到賈曼,我可能這輩子也演不到那些令我癲狂的電影。與賈曼的合作確實是一個奇蹟。」倫敦電影協會也在2008年設立鼓勵電影創作、向前衛電影先驅致敬的賈曼獎。
◆一個失明者離世前以詩一般的語言,訴說對藝術的熱愛與生命的回憶
《色度》是藝術涵養深厚的賈曼唯一談論色彩與人生的專書,全書用字與意境頗具詩意與想像力,令人讚嘆,像一道單色光芒通過稜鏡之後,散發出繽紛色彩。賈曼在書中談論繪畫、電影、人物,以及個人對於色彩的種種思考與回憶。旁徵博引,援引哲學家語錄、詩作、神話故事,並論及歷史、社會文化現象,說明各種顏色的意涵。此外,也提及從童年回憶到晚年罹病等種種個人經歷,宛如進入賈曼的另一部電影。
●白色謊言White Lies
白色似乎是單純、缺乏色彩,然而果真如此?本篇談到白色被視為是缺乏色彩,直到牛頓發現白色包含多種顏色(光的白色其實是由三原色以不同比例構成。)而在文化上,白色也有多種意義:例如純真、貞潔,但白色也有強大的掩飾能力,例如新娘白色婚紗底下其實有蠢蠢欲動的慾望。
白色也不是一種絕對的顏色,例如花朵的白帶點黃,雪的白則帶點藍。賈曼在文章後半述說成長過程中,白色所代表的意義,例如住在「白人」社區。綜言之,白色並非如表面般那麼單純,其意涵無法一言以蔽之。
●陰影是色彩之后Shadow Is the Queen of Colour
本篇論及亞里斯多德的《論色彩》,與畫家小普林尼(Pliny)的美學觀。亞里斯多德認為一切顏色皆源自於風火水土四元素,其與黑色及光線混和之後,就是我們眼睛所看見的色彩。普林尼則認為,繪畫越是擬真、越和大自然的物體相同,則越是佳作。無論是亞里斯多德或普利尼,都重視大自然本真的顏色,然而眾人卻漸漸偏好用從大自然掠奪的昂貴礦物,來創作藝術品與調配精美的顏料。
賈曼筆鋒一轉,表示當前的繪畫並非重視畫家的才能,而是重視材料探索。然而無論是以何種素材作畫,最好的作品往往是過往輝煌時代的影子。色彩,終究會在歷史的薄暮中逐漸褪去。
●看見紅色On Seeing Red
紅色是一種特殊的顏色,和黑或白都不同,因為提到紅色時,每個人心中的紅色一定都不同。本篇賈曼先談到在生活中所接觸到的紅色,例如檢查視力使用的器材、童年記憶中蔓延無際的紅色花海,接著談起紅色的文化意義(例如愛、戰爭),以及歷史上紅色出現的知名場景(如十字軍東征)。此外,也提及鎘紅、威尼斯紅、茜草深紅等各種紅色的製作知識。賈曼在文末指出,這篇文章是給讀者的信,他把信裝在紅信封裡,代表「急件」,接著放在紅色的信箱裡,下午四點,郵差會開紅色的車來收信。
●玫瑰的傳奇與沉睡的色彩The Romance of the Rose and the Sleep of Colour
提到中世紀,多數人會想到為數眾多的農奴,腦海浮現的也是單調的褐色。然而賈曼指出,其實這時期的宗教建築與書籍上,會運用如寶石般繽紛亮眼的色彩,不僅顏色鮮艷,顏料也很貴重。今天雖然顏料取得容易,然而現在採用標準化的「色表」與略帶有石灰色彩的塗料限制之下,恐怕很難會再出現如中世紀那樣光彩奪目的建築與藝術。
●馬西里歐.費奇諾Marsilio Ficino、李奧納多Leonardo、牛頓Isaac Newton
這三篇是以人物為主題的小品文。費奇諾將柏拉圖的論述譯成拉丁文,對文藝復興影響甚大。他是提出「柏拉圖式愛情」的人,讚美同性之愛。他的思想(例如對顏色的看法)不受基督教認可,著作也被打入冷宮,但仍影響深遠。
李奧納多是指達文西。賈曼在文中表示,他並不熱中達文西的畫作,反倒喜歡達文西的筆記,因為達文西觀察入微,對於光影的觀察有獨到之處,而從筆記中更能看出他的天才。然而,賈曼在讚賞達文西之際,還寫了一段軼聞:蒙娜麗莎的微笑原本要畫翡冷翠的銀行家之妻,但是要幫肖像畫上臉龐的那天,她罹患重感冒,於是派了俊美年輕的男孩告知達文西。達文西乾脆在肖像上畫男孩的臉,之後還給他一個吻。
牛頓這一篇非常短,文中提到他發現白色的光,其實是由各種顏色所組成。這一篇雖然沒有提到太多牛頓的軼事,但他曾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到牛頓是「很知名的單身漢」,似乎暗指這名天才也是同性戀。
全書中只有這三篇是以人物為主題,賈曼在說明這些人的天分之餘,不忘指出他們同性戀的身分,由此觀之,這幾篇其實涉及同性戀的身分認同。
●進入藍色Into the Blue
本書的多數文章是以一種顏色為主題,以許多觀點來看這種顏色的意涵,並抒發自己的美學觀或情感。和其他章節不同的是,這篇除了談論藍色的意涵之外,還有一大段是賈曼電影《藍》的腳本。這部電影的手法特殊,畫面只有一整片藍,並配上旁白與音效,以模擬賈曼因愛滋病失明,什麼都看不見,而旁白就是在訴說他的境遇。文中提及他失明、接受治療的狀況,還提到他許多朋友已死於愛滋,字裡行間透露出無盡的憂傷,是全書中最悲傷的一篇。
賈曼在寫本書時已病重,然而我們看不到怨天尤人或激進憤怒的言語,只有一個在步入人生最後階段的失明者,以詩一般的語言,訴說對藝術的熱愛與生命的回憶。
| FindBook |
有 14 項符合
色度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色度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德瑞克•賈曼Derek Jarman
賈曼(Derek Jarman,1942-1994)
英國前衛的同志電影大師。1960年進入倫敦國王學院念藝術史,1963-1967年在斯萊德藝術學校攻讀繪畫。賈曼第一次接觸到電影,是為肯•羅素(Ken Russell)的電影《魯登的惡魔》(The Devils,1971)擔任藝術總監。70年代開始進入電影圈,繪畫的薰陶使得賈曼有別於傳統的導演,對電影形式和傳達思想的在意勝過故事情節,喜歡用最原始的攝影機拍攝超8毫米的實驗性短片。賈曼也發表裝置藝術作品,擔任歌劇舞台設計,除了電影,他也為當時的流行歌手和樂團拍攝了大量的Video,如英國知名樂團寵物店男孩(Pet Shop Boys)、Orange Juice、The Smiths等。
對於政治、性、權利、死亡、慾望和生命的探討,是賈曼電影永恆的主題。詩意的作品中包含著對社會公共議題的強烈指涉。1975年,賈曼拍攝了首部以男同志情慾為題的劇情片《塞巴斯提安》(Sebastiane),敘述聖徒塞巴斯提安因堅持基督教信仰,拒絕為迪奧克勒辛國王提供床笫之歡而被迫害致死。這部影片不僅是英國電影中獨樹一幟的作品,也是世界電影史上重要的一頁。三年後拍攝了《慶典》(Jubilee),把歷史引入現實,讓女王伊莉莎白一世在魔術師的陪同下共遊70年代的龐克倫敦城,真實記錄了那個時代頹廢瘋狂的次文化。
開啟巴洛克時代的義大利畫家卡拉瓦喬(Caravaggio),是賈曼景仰的畫家之一,他在1986年用顛覆性的手法拍攝了《浮世繪》(Caravaggio),片中光影和構圖的設計採用了卡拉瓦喬的明暗繪畫法。這部宛如卡拉瓦喬傳的作品,在1987年獲得了第36屆柏林電影節銀熊獎,讓賈曼聲名大噪。《浮世繪》前後花了七年的時間才完成,是賈曼劇情性較強的影片之一,也是當今影后蒂妲•絲雲頓(Tilda Swinton)的長片處女作。她是賈曼的紅顏知己,自此開始包辦賈曼所有長片的女主角,直至賈曼去世。此片也是電影配樂大師Simon Fisher Turner,從偶像明星轉為電影配樂大師的出道作。在獲獎的同一年,賈曼公開他是同性戀者,並宣布自己罹患了愛滋病。
出櫃後賈曼的病情日漸惡化,儘管死亡逼近,但創作力卻絲毫未減:1988年的《英倫末路》(Last of England)、1989年的《戰爭安魂曲》(War Requiem)、1990年的《花園》(The Garden)、1991年的《愛德華二世》(Edward II)、1993年的《維根斯坦》(Wittgenstein),以及在生命盡頭、雙目失明下拍攝的最後一部電影《藍》(Blue)。
「我獻給你們這宇宙的藍色,藍色,是通往靈魂的一扇門,無盡的可能將變為現實。」《藍》片長八十分鐘,從頭至尾只是一片藍色,沒有活動的影像,沒有場面調度,沒有任何記號,放棄了傳統的技法和媒材,把失明之後的瀕死體驗具象化,通過虛無來呈現真實,引發觀眾進入冥想的狀態,感知無限藍中的死亡感覺。該片在1993年威尼斯雙年展上首映,引起了世界性的轟動。《藍》是電影史上的一個重要文本,也是賈曼在藝術上的最後一次創新。這部電影構思了將近二十年,緣起於泰德現代美術館在1974年3月推出的法國先鋒藝術家伊夫•克萊因(Yves Klein)作品展。賈曼參觀展覽之後在筆記本上寫下:為伊夫•克萊因做一部藍色電影。
1994年,賈曼因愛滋病去世。他不僅敢於面對自己的性向,終其一生也都在為同性戀者的權利奔走,是少數贏得世界尊敬的電影導演,前衛藝術家們和年輕同性戀者們的偶像。
譯者簡介
施昀佑
台大歷史系(2007),芝加哥藝術學院雕塑研究所(2014),曾共同合譯《攝影的精神》、《攝影師之魂》、《不合理的行為》、《瑞士做到的事》,譯有《當代攝影的冒險》、《想設計:保羅‧蘭德的永恆設計準則》。
德瑞克•賈曼Derek Jarman
賈曼(Derek Jarman,1942-1994)
英國前衛的同志電影大師。1960年進入倫敦國王學院念藝術史,1963-1967年在斯萊德藝術學校攻讀繪畫。賈曼第一次接觸到電影,是為肯•羅素(Ken Russell)的電影《魯登的惡魔》(The Devils,1971)擔任藝術總監。70年代開始進入電影圈,繪畫的薰陶使得賈曼有別於傳統的導演,對電影形式和傳達思想的在意勝過故事情節,喜歡用最原始的攝影機拍攝超8毫米的實驗性短片。賈曼也發表裝置藝術作品,擔任歌劇舞台設計,除了電影,他也為當時的流行歌手和樂團拍攝了大量的Video,如英國知名樂團寵物店男孩(Pet Shop Boys)、Orange Juice、The Smiths等。
對於政治、性、權利、死亡、慾望和生命的探討,是賈曼電影永恆的主題。詩意的作品中包含著對社會公共議題的強烈指涉。1975年,賈曼拍攝了首部以男同志情慾為題的劇情片《塞巴斯提安》(Sebastiane),敘述聖徒塞巴斯提安因堅持基督教信仰,拒絕為迪奧克勒辛國王提供床笫之歡而被迫害致死。這部影片不僅是英國電影中獨樹一幟的作品,也是世界電影史上重要的一頁。三年後拍攝了《慶典》(Jubilee),把歷史引入現實,讓女王伊莉莎白一世在魔術師的陪同下共遊70年代的龐克倫敦城,真實記錄了那個時代頹廢瘋狂的次文化。
開啟巴洛克時代的義大利畫家卡拉瓦喬(Caravaggio),是賈曼景仰的畫家之一,他在1986年用顛覆性的手法拍攝了《浮世繪》(Caravaggio),片中光影和構圖的設計採用了卡拉瓦喬的明暗繪畫法。這部宛如卡拉瓦喬傳的作品,在1987年獲得了第36屆柏林電影節銀熊獎,讓賈曼聲名大噪。《浮世繪》前後花了七年的時間才完成,是賈曼劇情性較強的影片之一,也是當今影后蒂妲•絲雲頓(Tilda Swinton)的長片處女作。她是賈曼的紅顏知己,自此開始包辦賈曼所有長片的女主角,直至賈曼去世。此片也是電影配樂大師Simon Fisher Turner,從偶像明星轉為電影配樂大師的出道作。在獲獎的同一年,賈曼公開他是同性戀者,並宣布自己罹患了愛滋病。
出櫃後賈曼的病情日漸惡化,儘管死亡逼近,但創作力卻絲毫未減:1988年的《英倫末路》(Last of England)、1989年的《戰爭安魂曲》(War Requiem)、1990年的《花園》(The Garden)、1991年的《愛德華二世》(Edward II)、1993年的《維根斯坦》(Wittgenstein),以及在生命盡頭、雙目失明下拍攝的最後一部電影《藍》(Blue)。
「我獻給你們這宇宙的藍色,藍色,是通往靈魂的一扇門,無盡的可能將變為現實。」《藍》片長八十分鐘,從頭至尾只是一片藍色,沒有活動的影像,沒有場面調度,沒有任何記號,放棄了傳統的技法和媒材,把失明之後的瀕死體驗具象化,通過虛無來呈現真實,引發觀眾進入冥想的狀態,感知無限藍中的死亡感覺。該片在1993年威尼斯雙年展上首映,引起了世界性的轟動。《藍》是電影史上的一個重要文本,也是賈曼在藝術上的最後一次創新。這部電影構思了將近二十年,緣起於泰德現代美術館在1974年3月推出的法國先鋒藝術家伊夫•克萊因(Yves Klein)作品展。賈曼參觀展覽之後在筆記本上寫下:為伊夫•克萊因做一部藍色電影。
1994年,賈曼因愛滋病去世。他不僅敢於面對自己的性向,終其一生也都在為同性戀者的權利奔走,是少數贏得世界尊敬的電影導演,前衛藝術家們和年輕同性戀者們的偶像。
譯者簡介
施昀佑
台大歷史系(2007),芝加哥藝術學院雕塑研究所(2014),曾共同合譯《攝影的精神》、《攝影師之魂》、《不合理的行為》、《瑞士做到的事》,譯有《當代攝影的冒險》、《想設計:保羅‧蘭德的永恆設計準則》。
目錄
序言Introduction
白色謊言White Lies
陰影是色彩之后Shadow Is the Queen of Colour
看見紅色On Seeing Red
玫瑰的傳奇,沉睡的色彩The Romance of the Rose and the Sleep of Colour
灰質Grey Matter
馬西里歐.費奇諾Marsilio Ficino
綠手指Green Fingers
煉金之色Alchemical Colour
耗、腦、布朗、考How Now Brown Cow
黃色的危險The Perils of Yellow
橙尖Orange Tip
李奧納多Leonardo
進入藍色Into the Blue
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
紫色辭藻Purple Passage
黑色藝術Black Arts
銀色與金色Silver and Gold
彩紅色Iridescence
半透明Translucence
白色謊言White Lies
陰影是色彩之后Shadow Is the Queen of Colour
看見紅色On Seeing Red
玫瑰的傳奇,沉睡的色彩The Romance of the Rose and the Sleep of Colour
灰質Grey Matter
馬西里歐.費奇諾Marsilio Ficino
綠手指Green Fingers
煉金之色Alchemical Colour
耗、腦、布朗、考How Now Brown Cow
黃色的危險The Perils of Yellow
橙尖Orange Tip
李奧納多Leonardo
進入藍色Into the Blue
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
紫色辭藻Purple Passage
黑色藝術Black Arts
銀色與金色Silver and Gold
彩紅色Iridescence
半透明Transluc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