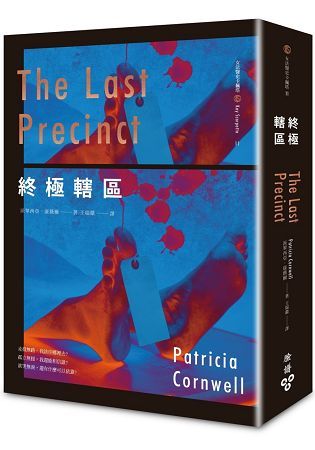最暢銷的法醫小說系列,全球銷售突破一億冊!
翻譯為三十六國語言、熱銷一百二十國
刑事鑑識與法醫探案的先驅,「CSI犯罪現場」相關熱門影集取材原點
超越《屍體會說話》,挑戰鑑識科技極限之作!
在失去至愛之後的聖誕前夕,我收到一封他給我的親筆信
在遭到狼人突襲、險些丟掉小命的兩個月後,法院傳票翩然而至
我欲哭無淚、孤立無援、走投無路
上天對我的磨難,究竟何處才是盡頭?
才剛被襲擊險些淪為「狼人」另一名受害者的維吉尼亞州首席法醫凱‧史卡佩塔原以為,凶嫌遭逮正義終得伸張,然而事情發展遠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一股詭異的氣氛悄悄形成,她赫然發現自己竟然成為女警官命案的主要嫌犯,檢調單位私下正對她展開積極調查。
不利的證據接連出現,另一方面「狼人」的犯案記錄似乎比原先所知更早且範圍擴及紐約,甚至牽涉到她不願觸及的傷痛記憶。為了釐清紐約的一樁陳年懸案,來自紐約的精悍女性檢察官來到維吉尼亞加入調查,史卡佩塔不得不挺身為自己所認知的真相辯護。在艱難的處境下,她審視自己的內心與過去的職業生涯,怎麼也沒想到會受到如此不堪聞問的指控……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終極轄區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52 |
小說/文學 |
二手書 |
$ 310 |
二手中文書 |
$ 355 |
推理 / 驚悚小說 |
$ 356 |
推理小說 |
$ 356 |
西洋推理/犯罪小說 |
$ 356 |
小說 |
$ 356 |
歐美推理小說 |
$ 396 |
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終極轄區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派翠西亞.康薇爾Patricia Cornwell
一九五六年出生於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她的職業生涯從主跑社會新聞的記者開始,一九八四年在維吉尼亞州的法醫部門擔任檢驗記綠員。一九八四~八六年間,康薇爾根據自身的法醫工作經驗寫下了三本小說,然而出書過程並不順利。
後來她聽從建議,推翻原本以男偵探為主角的構想,改以女法醫為主軸,終於在一九九○年出版了她的第一本推理小說《屍體會說話》,結果一炮而紅,為她風光贏得一九九○年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約翰.克雷西獎,一九九一年美國推理作家協會愛倫坡獎最佳首作、國際推理讀者協會麥卡維帝獎最佳首作、鮑查大會安東尼獎最佳首作,以及一九九二年法國Roman d’Aventures大獎。
一九九三年,康薇爾再以《失落的指紋》拿下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代表年度最佳小說的金匕首獎。系列作品中的主人翁凱.史卡佩塔醫生,則在一九九九年獲頒夏洛克獎最佳偵探獎。
派翠西亞.康薇爾目前擔任國家法醫學院,應用法醫科學部門的主任。
相關著作:《人體農場》《失落的指紋》《屍體會說話》《死亡的理由》《殘骸線索》《波特墓園》《獵殺史卡佩塔》《肉體證據》《肉體證據》《致命暴露》《起火點》《鑑識死角》《黑色通告》《黑色通告》
譯者簡介
王瑞徽
王瑞徽
淡大法語系畢,曾任編輯、廣告文案,現專事翻譯。譯作包括雷.布萊伯利、派翠西亞.康薇爾、約翰.波恩等人作品。
派翠西亞.康薇爾Patricia Cornwell
一九五六年出生於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她的職業生涯從主跑社會新聞的記者開始,一九八四年在維吉尼亞州的法醫部門擔任檢驗記綠員。一九八四~八六年間,康薇爾根據自身的法醫工作經驗寫下了三本小說,然而出書過程並不順利。
後來她聽從建議,推翻原本以男偵探為主角的構想,改以女法醫為主軸,終於在一九九○年出版了她的第一本推理小說《屍體會說話》,結果一炮而紅,為她風光贏得一九九○年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約翰.克雷西獎,一九九一年美國推理作家協會愛倫坡獎最佳首作、國際推理讀者協會麥卡維帝獎最佳首作、鮑查大會安東尼獎最佳首作,以及一九九二年法國Roman d’Aventures大獎。
一九九三年,康薇爾再以《失落的指紋》拿下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代表年度最佳小說的金匕首獎。系列作品中的主人翁凱.史卡佩塔醫生,則在一九九九年獲頒夏洛克獎最佳偵探獎。
派翠西亞.康薇爾目前擔任國家法醫學院,應用法醫科學部門的主任。
相關著作:《人體農場》《失落的指紋》《屍體會說話》《死亡的理由》《殘骸線索》《波特墓園》《獵殺史卡佩塔》《肉體證據》《肉體證據》《致命暴露》《起火點》《鑑識死角》《黑色通告》《黑色通告》
譯者簡介
王瑞徽
王瑞徽
淡大法語系畢,曾任編輯、廣告文案,現專事翻譯。譯作包括雷.布萊伯利、派翠西亞.康薇爾、約翰.波恩等人作品。
序
「打從第一頁起,就高潮不斷……康薇爾將暴力、緊張、逐漸升高的偏執和驚悚、陰謀僅僅的交纏在一起。沒有人能像她這樣,把人的邪惡描繪得如此淋漓盡致……康薇爾筆下的女主角,塑造得既真實又撼動人心,讓人幾乎無法相信,她其實只是一個作者想像的虛構人物。」
──《今日美國》
「戲中有戲,氣氛詭譎,情節驚悚,一個又一個稍不留神就會墜入萬丈深淵陷阱的橋段,牢牢扣住讀者的心絃。巧妙的設計,驚奇連連的安排,加上康薇爾式的寫作技巧,讓《終極轄區》成為作者的代表之作。」
──《洛杉磯時報》
「這是女法醫史卡佩塔系列中最令人意外的一部小說……《終極轄區》內容曲折,從頭到尾你就一路跟著史卡佩塔在黑暗中摸索碰壁,直到隱隱然一道曙光乍現。雖然這種讓人喘不過氣的壓迫感是康薇爾的寫作特色,但《終極轄區》卻顯現了她更上層樓的實力。」
──《邁阿密論壇報》
「簡略的評語無法道盡康薇爾小姐敘事的精妙,結合她的法醫學知識、對執法者辦案手法的深究和製造張力以及邪惡氛圍的技巧……康薇爾小姐的最優表現一向來自她對細節的專注以及對一手經驗的堅持。這些特徵在本書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里奇蒙時遞報》
──《今日美國》
「戲中有戲,氣氛詭譎,情節驚悚,一個又一個稍不留神就會墜入萬丈深淵陷阱的橋段,牢牢扣住讀者的心絃。巧妙的設計,驚奇連連的安排,加上康薇爾式的寫作技巧,讓《終極轄區》成為作者的代表之作。」
──《洛杉磯時報》
「這是女法醫史卡佩塔系列中最令人意外的一部小說……《終極轄區》內容曲折,從頭到尾你就一路跟著史卡佩塔在黑暗中摸索碰壁,直到隱隱然一道曙光乍現。雖然這種讓人喘不過氣的壓迫感是康薇爾的寫作特色,但《終極轄區》卻顯現了她更上層樓的實力。」
──《邁阿密論壇報》
「簡略的評語無法道盡康薇爾小姐敘事的精妙,結合她的法醫學知識、對執法者辦案手法的深究和製造張力以及邪惡氛圍的技巧……康薇爾小姐的最優表現一向來自她對細節的專注以及對一手經驗的堅持。這些特徵在本書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里奇蒙時遞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