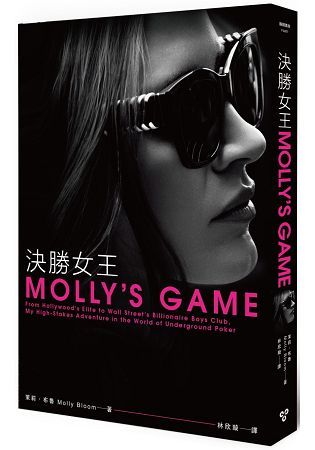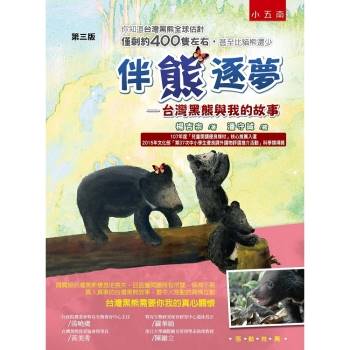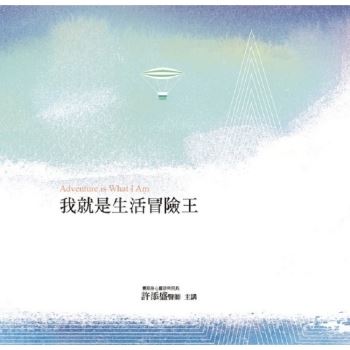在好萊塢巨星、華爾街富豪與俄羅斯黑幫一擲千金的祕密賭局
她從青澀單純的新鮮人,變成呼風喚雨的撲克牌女王
一筆野心勃勃的人生賭注,一場奢華危險的迷失與洗禮
同名改編電影入圍金球獎最佳女主角、最佳劇本項目
《史帝夫賈伯斯》、《社群網站》金獎編劇 艾倫‧索金/編導
《攻敵必救》潔西卡‧雀絲坦、《環太平洋》伊卓瑞斯‧艾巴/主演
地下世界的《穿著Prada的惡魔》+ 女性版《華爾街之狼》
二十多歲時獨自來到洛杉磯闖蕩的茉莉‧布魯,以為自己應徵上的是普通的商業助理,卻發現這份工作的內容還包括經營地下流動賭場、每週為好萊塢名流舉辦撲克牌賭局,賭局常客的名單令她瞠目結舌:李奧納多•狄卡皮歐、麥特•戴蒙、班•艾佛列克、陶比•麥奎爾……。剛出社會的她,在一場場牌局間,從這些或驕傲或親切的電影界紅人身上認識了人情世故、權謀手腕,學會這個紙醉金迷之地的生存之道,甚至知道什麼樣的音樂、點心與閒聊話題最能夠讓賭客豪爽下注。她的祕密事業擴展成了全美國規模最大、金額最高的地下博弈活動,每場賭局光是小費就數以萬計,洛城的上流社交圈人人渴望收到她的賭局邀請,在她精心布置的牌桌上以六位數字的籌碼宣洩壓力、追求刺激,紐約的財金菁英界也為她傾倒。
「記得,別被好牌迷昏了。因為翻牌時,妳那一手漂亮的牌可能變得醜到不行。撲克牌是關乎機運、簡單數學和讀心術的遊戲。
以牌技取勝並非總是有用。世界上最厲害的玩家也難免有時手氣背。走霉運的時候,要懂得見壞就收。
別忘了,撲克牌不只是遊戲。而是人生的策略。如果妳勇於冒險,請確定妳冒的險是經過精打細算的。」
然而,當她過著奢華生活、享受著操弄權貴人士於指掌間的成就感,聯邦調查局開始盯上她,兇殘的外國犯罪幫派企圖瓜分她的事業版圖,連曾經照顧提攜她的恩人也滿懷嫉妒地想看她一敗塗地。
面對名利爭奪、猜忌背叛,她該如何維繫自己一手打造的地下王國?如果輸掉了這一局,又該怎麼做才能夠全身而退?她也問著自己:除了金錢與虛榮,究竟還有什麼原因,使她沉溺在一場又一場的牌局中、不可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