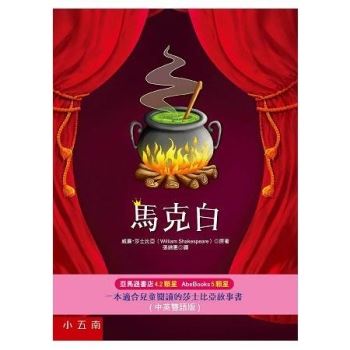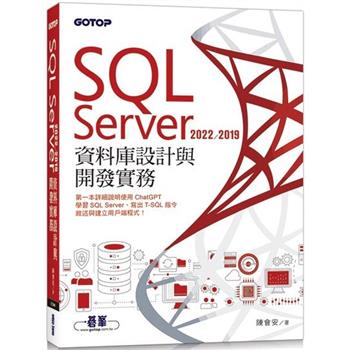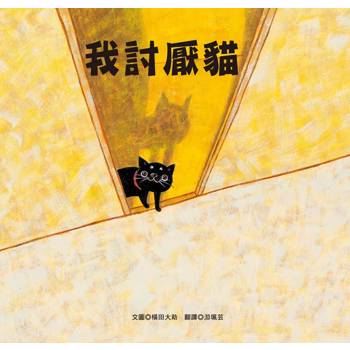我掃視著廢棄的荷蘭鐵器工廠。過去十多年裡,許多流浪漢在此命喪黃泉。整座工廠是由好幾棟磚房和兩根超大的煙囪組成的。窗戶很小,全布滿了灰塵和污垢,大多數都用木板封起來了,我猜我可能得打破點東西才能進得去。手指間的匕首輕輕顫動了一下。我開門,走下車。
我繞著建築物移動,枯草在我雙腿上摩擦。往前看,遠處黑暗廣闊的蘇必略湖隱約可見。我開了四小時的車,居然還沒開出湖的範圍。
一過轉角,我看到壞掉的鎖掛在半掩的大門上,突然間,我的胸部一緊,整個身體開始嗡嗡作響。我從沒想過要到這兒來,我對這裡一點興趣都沒有。可是現在我站在這裡,卻幾乎快喘不過氣來。自從我面對奧比巫魔後,這是第一次我又有這種進入了同調的狀態、猶如被一條細線拉住的感覺。我的手指在刀子的握柄上震顫,奇特而熟悉的感應又回來了,彷彿它是我的一部分,和我肌膚相融,滲進了我的骨頭裡。即使我想要,也無法讓它脫離我的手。
工廠裡的空氣有股酸味,但沒有臭味。無數的老鼠以此為家,牠們帶動了空氣的流通,可是還是驅不走酸味。塵埃下一定有死人,每個角落可能都藏著屍體。即使在老鼠屎中也不例外,牠們就是靠吃死掉的東西生存的。不過我沒感覺到任何血肉,看來不會有具腐屍在轉角處等我,不會有張爛了一半的臉點著頭歡迎我。達人是怎麼說的?警察找到屍首時,基本上他們已經全部乾縮了,只剩骨頭和骨灰。他們不過是把它們掃起來,直接拿去埋。根本沒人重視這些案子。
當然他們不重視這些案子。他們從來不重視。
我走到後方,看不出來這兒原來是在做什麼的。所有值得偷的東西都不見了,只剩一堆我辨認不出的機器殘骸。我走向大廳,緊緊握著手裡的匕首。月光從窗戶射進來,反射在室內的物件上,所以我的視線還算清楚。經過每個門口時,我都會停下腳步,用全身去聆聽、去聞、去感覺亡靈的藏身之處。在我左手邊的房間原來應該是間辦公室,或是小型的員工休息室。一張桌子被推到角落。我注意看著桌子下,一張舊毯子被扔在那兒,但在細看之後,我瞄到兩隻稍微伸出的腳。我等著,但是它動也不動。只是一具屍體,被吸乾的屍體,除了腐爛的皮膚外什麼都沒留下。我往前走,讓它繼續待在桌子下。我不想也不需要去檢視它。
走廊連接到一個很大、天花板很高的房間。梯子和狹小的通道在空中相會,還有許多鏽蝕的輸送帶。遠遠的牆邊放著一個巨大的黑色火爐,雖然已經失去了大部分的零件,只剩一堆殘骸,但我還是一眼就看出來它是個火爐。它一定製造過許多鐵器。幾千個人曾在這兒揮汗如雨,一滴滴的汗珠滲入了地板。對熱氣的記憶仍然飄盪在空中,即使已經過了許多許多年。
我愈往裡面走,感覺愈擁擠。有東西在這兒,而且它的存在感極為沉重。我更用力地握緊匕首,覺得那個沉睡了好幾十年的火爐隨時會醒來,重新噴出熊熊大火。突然間,我聞到了燒焦的人皮味道,然後我身後被敲了一記,臉朝下地倒在滿是灰塵的地板上。
我俐落地翻身,站了起來,手裡的匕首劃出一個大大的弧線。我以為鬼就站在我後面,但是沒有。有幾秒鐘的時間,我相信它逃走了,而我被迫得開始玩打地鼠或丟飛鏢的遊戲,直到我找到它。可是我還能聞到它的焦味。而且我感覺到怒氣猶如令人昏眩的浪潮在房間裡不停地轉動。
他站在房間離我最遠的一端,堵住通往走廊的出口,好像怕我逃了似的。他的皮膚和燒過的火柴一樣黑,裂縫不停流出灼熱的金屬熔液,彷彿整個人被一層正在冷卻的火山熔岩蓋住了。在一片漆黑中,他的眼睛顯得格外潔白。距離太遠,我無法判斷眼睛裡只有眼白,還是也有黑色的眼仁。天啊!我希望有眼仁,我討厭奇形怪狀的噁心眼睛。然而有眼仁也好,沒眼仁也好,他們的眼睛裡絕沒有人性。在死亡和燃燒的地獄中過了這麼久,再多的人性也消耗光了。
「來吧!」我一邊說,一邊轉動手腕。不管要刺要砍,匕首都已經準備好了。我的背部和肩膀被他打中的地方有點痛,但我不去理它。他慢慢地走近我。他的速度很慢,也許是在想為什麼我不逃跑。也許是因為他每移動一下,身上的皮膚就會裂出新的傷口,流出……我不知道是什麼的亮橘色金屬液體。
這是發動攻擊前的一刻。我大大吸進一口氣,眼睛連眨都不眨一下,感受到每一秒鐘都拉得好長。他和我的距離已經近到我能看出他有眼仁,亮藍色的眼珠,瞳孔因一直處在持續的疼痛中而緊縮。他的嘴巴微張,大部分的嘴唇因裂開剝落都不見了。
我想聽她說話,即使一個字也好。
他揮舞著右勾拳,在我右耳旁幾寸的空中劃過。我感到它帶來的熱氣,聞到了毛髮燒焦的味道。我的頭髮燒焦了。我想起達人提到過的屍首特點—只剩骨頭和骨灰。幹!那些屍體其實都才剛死不久,只不過全被這隻鬼高溫燒過,才會全成了乾屍。他的臉上滿是怒火,他沒有鼻子,只有一個好大的洞。他的臉頰上有些部分和燒過的木炭一樣乾,剩下的卻因感染而流膿。我往後退了兩步,避開他的喘息。因為嘴唇已經燒掉了,所以他的牙齒便顯得特別大,將他的表情固定成一個病態而永恆的笑臉。到底有多少個可憐的流浪漢曾對著這張可怕的臉醒來,然後立刻被從裡到外烤熟?
我身體往下一沉,用力猛踢,雖然如願把他絆倒了,卻也把自己的小腿燒傷了。我的牛仔褲有一部分融化黏在我皮膚上。但我可沒有抱怨的時間,他的手指伸向我,我急忙在地上翻滾避開。布料被他一把扯下,天知道那上面黏了我多少皮膚啊!
太爛了。他到現在連哼都沒哼一聲。誰知道他的舌頭是不是還在,更別說安娜會不會想藉著它來說話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麼。我決定等待,耐心等待。
我拉回手肘,準備好要將匕首插進他的肋骨裡。可是我遲疑了。如果我做得不對,極有可能匕首會直接黏在我皮膚上。我猶豫的時間沒超過一秒鐘,剛好長到讓眼角注意到一個飄過去的白影。
不可能的!一定不是。一定是隻死在這個可怕工廠的其他鬼魂。可是,如果它真是死在這工廠的其他鬼魂,它卻不是被燒死的。這個靜靜走在滿是灰塵的地板上的女孩和皎潔的月亮一樣白。棕色長髮垂在背後,從她極白的洋裝上散開。那件洋裝即使燒成灰我都認得出來,不管它是白到不可置信,還是紅到整件是血。是她,是安娜。她赤足踩在水泥地上,發出輕軟的磨擦聲。
「安娜。」我一邊說,一邊很快地爬起來。「妳還好嗎?」
她聽不見。或者該說,就算她聽見了,她也沒回頭。
躺在地板上的烈焰鬼用力抓住我的鞋子。我踢開他的手,完全不去理會他和橡膠燒焦的刺鼻氣味。我發瘋了嗎?我產生幻覺了嗎?她不可能真的在這兒?不可能的。
「安娜,是我,妳聽得見嗎?」我走向她,但不敢走得太快。深怕我移動得太快,她會消失不見;深怕我走得太快,就會看到我不想看的事。我怕我拉她轉身,卻看到她沒有臉,卻看到她只剩一身骨頭。我怕她會在我手中化為灰燼。
烈焰鬼在地板上慢慢起身,發出肉塊拖動的咯咯聲。我不管他。她在這兒做什麼?為什麼她不說話?她只是一直走,對她周圍的景象視而不見。不過……並非全部視而不見。
我望向在房間底部的廢棄大火爐,突然間一個不祥的預感緊緊掐住我的胸膛。
「安娜—」我尖叫。烈焰鬼抓住我的肩膀,燙得像有人在我上衣裡扔進一塊火紅木炭。我掙脫他的手掌,從我的眼角,我看到安娜似乎頓了一下,但我正忙著用匕首又刺又砍,從下面再次重踢他的腳,所以是或不是,我也無法確定。
匕首變得很燙,我只好不停地左右換手才不會把它掉到地上。只不過是在他的胸腔上割出一道淺淺的橘紅色傷口,就弄得這麼燙;我應該立刻就了結他,飛快地把匕首插入、抽出,嗯……也許該先用衣服包住刀柄,但是我並沒有這麼做。我只是讓他暫時不能動,然後轉身。
安娜站在大火爐前,用手指輕輕撫摸著又黑又粗的金屬爐面。我一次又一次地呼喚她的名字,但她沒有回頭。她握住把手,用力將爐灶的門拉開。
房間內的空氣變了。彷彿有一陣波浪推過,扭曲了我視線裡的空間。火爐的口開得更大,安娜爬了進去。灰燼染黑了她的白洋裝,在布料和皮膚上留下一條一條宛如瘀血的黑痕。而且她看起來不大對勁,她移動的方式不大對勁。她看起來簡直像個連線木偶。當她擠進火爐的開口時,她的手臂和大腿不自然的往後折,就像一隻被吸進吸管的蜘蛛那樣。我的嘴巴好乾。在我背後,烈焰鬼又再次爬了起來。我肩上的灼傷提醒我趕快遠離他,我幾乎沒注意到小腿上的燙傷讓我走路一跛一跛的。我的心裡只想著:安娜,離開那裡。安娜,看著我。
我彷彿身陷夢境,完全無能為力的噩夢,什麼都不能做。我的雙腿成了兩根鉛棒,不論我多努力嘗試,都沒辦法喊出一點聲音來警告她。當死了幾十年的大火爐重新活過來,噴出熊熊熊大火時,我大聲尖叫,只是叫,沒有字彙、沒有言語,只是放聲大叫。反正無所謂了,安娜在那火爐內已經被燒死了。她蒼白的手臂上起了水泡,很快轉成焦黑,抵住爐壁上的板條,彷彿她後悔得太遲。
烈焰鬼抓住我的襯衫,將我轉過來面對他,我感覺到熱氣和煙從我的肩膀傳來。他的雙眼從他黑漆漆的臉上突出來,他的牙齒不停地上下開合。我看向後頭的大火爐。我的雙手雙腿都失去了知覺。我的心臟還在跳動嗎?我不知道。除了肩膀上的灼痛感,我什麼感覺都沒有了,只是動也不動地呆立著。
「殺我啊!」烈焰鬼咬牙切齒地說。我想都沒想,只是將匕首送進他的肚子裡,然後立刻抽出來。但即使如此,還是灼傷了自己的手掌。我往後退,看著他掙扎倒向地板,然後我跑向一個舊輸送帶,跳上去掛住,避免他伸手來抓我的膝蓋。剎那間,房間裡安娜的尖叫聲和烈焰鬼的慘叫聲交纏在一起。他的手腳縮在一起,燃燒直到乾癟,最後終於縮到不成人形,只剩一塊扭曲的焦炭。
當他不再移動時,周圍的空氣立刻冷了下來。我深呼吸,張開眼睛。我甚至不記得自己是什麼時候閉上眼的。房間裡安安靜靜。我看向大火爐,它裡頭空空的,像睡著了一樣。而我知道,如果我走過去觸摸它,它會是冷的,彷彿安娜從沒在那兒出現過。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噩夢少女(《血衣安娜》完結篇.全新唯美插畫書封版)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噩夢少女(《血衣安娜》完結篇.全新唯美插畫書封版)
《幽影王冠》作者驚豔全美的超自然愛情驚悚小說
驚心動魄、淒美動人、超乎想像的精采完結篇
●榮獲六大最佳小說獎、售出15國版權、Goodreads好讀網超過30,000名讀者滿分評價
●改編電影將由《暮光之城》作者史蒂芬妮.梅爾監製
「安娜去了哪裡?她終於安息了嗎?
但我最想知道的是──她還能回到我身邊嗎?」
少女亡靈「血衣安娜」為了拯救將她從詛咒中釋放的少年卡斯,在他與邪惡力量的決戰中奮不顧身地拖著殘酷恐怖的奧比巫魔消失於魔法引發的爆炸。
卡斯在家人和朋友的幫助下,繼續進行獵殺作祟亡靈的任務,但他始終無法忘記安娜:他走到哪裡都看到她的形影,有時在他的睡夢中,有時在他清醒睜開的眼前。而且這些影像無比真實,他看見安娜飽受火焚、穿刺等酷刑折磨,全身布滿比她被謀殺時更恐怖的傷口,眼神空洞黑暗,彷彿無聲地呼喚著他。
卡斯不知道安娜消失後到底去了什麼地方,但他相信,她不應該遭受現在加諸在她身上的痛苦。安娜不只一次挽救過卡斯的性命,現在,他決定回報她的愛與犧牲。卡斯發誓,他會找到安娜,即使他必須再次跨越活人與亡靈之間的危險界線……
【好評推薦】
幽靈少女安娜的故事來到結局,充滿更多驚心動魄的懸念與巧妙的轉折,令讀者心滿意足。——《科克斯書評》,星級評論
這部續集絕不會讓《血衣安娜》的書迷失望......布雷克在創作恐怖故事的同時穿插幽默感的才華,帶來難得一見的閱讀享受。——《學校圖書館期刊》
《血衣安娜》是個錯綜複雜的陰森故事。書中的英雄以獵殺亡魂為天職,卻又不能自已地愛上了亡魂。
——《骸骨之城》作者卡珊卓拉.克蕾兒
這是個男孩遇見女孩的故事:只不過男孩是個偏執且奮不顧身的亡靈殺手,一心想要為父報仇;女孩卻是個與命喪她手下的亡靈一同被囚禁在故居的殺人惡鬼。不用說,卡斯和安娜是我現在最喜歡的一對。
——《咒術家族》作者荷莉.布萊克
令人毛骨悚然,卻又悲傷浪漫。《血衣安娜》絕對不是一般的鬼故事,『她』令人無法自拔、讓讀者無法呼吸,讀完最後一頁後還遲遲無法從中抽離。
——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
畫面感十足、令人讚嘆!布雷克將鮮血和羅曼史結合得恰到好處,絕對能吸引《暮光之城》的粉絲群。
——《書單》(Booklist)
從第一句就緊緊抓住讀者。這本小說充滿了機智和恐怖,絕對會吸引讀者一路翻到最後,停不下來。
——浪漫時潮書評網(RT Book Reviews)
我根本把自己黏在書頁上了。
——超自然書評網(Paranormal Book Reviews)
令人驚豔的原創性、娛樂性十足!絕對能擠身最佳恐怖小說之列。我們要看續集!
——《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星級評論
這是本非常有娛樂性的小說——節奏緊湊、和《向達倫》一樣恐怖、充滿令人愉快的機智諷刺,以及又苦又甜的浪漫愛情。
——我愛這本書!書評App程式(We Love This Book)
《血衣安娜》是我最喜歡的小說之一。它完全符合我的期待﹕炫麗、血腥、令人心碎、無情卻又精彩刺激到了極點。正是我等不及要一睹為快的好書!
——寇特妮.艾莉森.穆特(Courtney Allison Moulton),《天使之焰》(Angelfire)作者
我愛卡斯!他存在的世界是這麼萬分逼真,栩栩如生。做好開燈睡覺的心理準備,因為這本書不僅有牙齒,而且是超級鋒利的那種。
——史黛西.康德(Stacey Kade),《女鬼與哥德少年》(The Ghost and the Goth)作者
作者凱德兒.布雷克的寫作就像特技表演,精準無畏,讓讀者屏息期待下一段表演。她的作品是個奇蹟。
——安.阿吉雷(Ann Aquirre),《絕境三部曲》作者
今年最佳青少年小說書單之一!超棒又獨特的角色!……為了繼續往下看,我等不及要衝回家了!
——美國亞馬遜TOP500最佳書評家Christina (Ensconced in YA)
凱德兒.布雷克讓我連聲讚嘆:「哇天啊!」如果她看得到這則書評的話……拜託續集寫快一點!
——美國亞馬遜試讀本專屬會員Derrick Dodson
我非常享受閱讀這本小說:文筆絕佳、令人毛骨悚然卻又放不下書。
——美國亞馬遜TOP1000最佳書評家K.Sozaeva
我被這本小說的美麗和恐怖完全吸進去了……令人無法自拔。
——電子書癡書評網(KindleObsessed.com)
鮮明又真實的故事。
——英國書袋書評網(Bookbag)
作者簡介:
凱德兒.布雷克Kendare Blake
英國北倫敦密德薩斯大學(Middlesex University)文學創作藝術碩士。她住在美國華盛頓州,自幼便立志成為作家,喜歡看恐怖小說、欣賞希臘神話、生紅肉,還有素食主義。她曾發表數篇超自然奇幻短篇故事,活躍於各種類型寫作社群。她的長篇小說《血衣安娜》甫推出即獲得各大書評媒體讚賞、好評不斷,獲獎眾多,出版翌年即由《暮光之城》作者史蒂芬妮.梅爾迅速搶下電影版權,並親自擔任製片人,續集《噩夢少女》同樣受到讀者歡迎。稍後,布雷克推出挑戰史詩奇幻的華麗轉型之作《幽影王冠》系列,亦登上眾多暢銷排行榜、由好萊塢一線製片公司籌拍改編電影。
相關著作:《血衣安娜(全新唯美插畫書封版)》《幽影王冠II:血王座》《幽影王冠II:血王座【博客來獨家黑蝕╳爍光雙書衣,限量作者簽名&典藏書籤組】》《幽影王冠》《幽影王冠【博客來獨家暗湧╳流金雙書衣,限量作者簽名&典藏L夾】》《血衣安娜》
譯者簡介:
卓妙容
臺灣大學會計系畢業,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企管碩士。曾任職矽谷科技公司財務部十餘年。譯有《打造暢銷書》、《金融吃人魔:如何與高風險市場共舞》、《美人心機》、《百分之七的溶液》等書。
章節試閱
我掃視著廢棄的荷蘭鐵器工廠。過去十多年裡,許多流浪漢在此命喪黃泉。整座工廠是由好幾棟磚房和兩根超大的煙囪組成的。窗戶很小,全布滿了灰塵和污垢,大多數都用木板封起來了,我猜我可能得打破點東西才能進得去。手指間的匕首輕輕顫動了一下。我開門,走下車。
我繞著建築物移動,枯草在我雙腿上摩擦。往前看,遠處黑暗廣闊的蘇必略湖隱約可見。我開了四小時的車,居然還沒開出湖的範圍。
一過轉角,我看到壞掉的鎖掛在半掩的大門上,突然間,我的胸部一緊,整個身體開始嗡嗡作響。我從沒想過要到這兒來,我對這裡一點興趣都沒有。可...
我繞著建築物移動,枯草在我雙腿上摩擦。往前看,遠處黑暗廣闊的蘇必略湖隱約可見。我開了四小時的車,居然還沒開出湖的範圍。
一過轉角,我看到壞掉的鎖掛在半掩的大門上,突然間,我的胸部一緊,整個身體開始嗡嗡作響。我從沒想過要到這兒來,我對這裡一點興趣都沒有。可...
顯示全部內容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