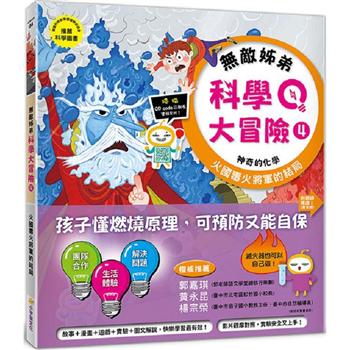真假難辨的出土名畫,暗藏黑幕的拍賣騙局,
身陷藝術犯罪陰謀的少女偵探與忠實助手,
唯一的盟友卻是百年來的宿敵「莫里亞提」……
★美國亞馬遜網路書店4.2星高分評價
★《柯克斯書評》星級好評
★Goodreads讀者票選獎(年度最佳青少年小說)入圍
★青少年圖書館服務協會(YALSA)年度最佳青少年小說
┤故事簡介├
福爾摩斯、華生與莫里亞提,
三個被刻下太多歷史痕跡的姓氏,
善與惡、忠誠與背叛,何時才能超脫血脈的牽繫……?
在雪林佛學院結束了驚心動魄的第一個學期、第一次聯手偵破謀殺案之後,詹米跟夏洛特一起造訪了福爾摩斯家的鄉間大宅。這棟英國豪宅裡雖然充滿了令他驚奇的家族古物,福爾摩斯一家的成員之間卻瀰漫著警戒不安的氣氛,使得他無所適從。不久,他們發現夏洛特的母親遭人下毒後病倒,卻不肯就醫或報警,叔叔林德也在監視系統遍布、宛如高科技密室的大宅裡突然消失無蹤,留下只有夏洛特能夠解讀的隱晦求救訊息。
擔任業餘調查員的林德,原本在德國臥底偵察一個偽造二戰時期佚失藝術品的犯罪集團,幕後主使與莫里亞提家關係密切。雖然莫里亞提教授的後代對外宣稱不再從事非法活動,也一度與福爾摩斯家族握手言和,甚至曾派數學天才奧古斯特‧莫里亞提擔任夏洛特的家教以表善意,但兩個家族的和解最終卻黯然失敗,莫里亞提家的犯罪事業也死灰復燃。如今的奧古斯特對外捏造自己的死訊、躲在夏洛特哥哥麥羅的國防科技公司裡,猶如與世隔絕、沒有身分的幽靈。他不計前嫌,答應協助夏洛特和詹米找出林德的下落,同時陪他們潛入歐洲各地的美術館和拍賣會,將偽畫集團一網打盡。
但是,當主導偽畫集團的莫里亞提家手足頻頻在暗處召喚,奧古斯特還能夠堅守承諾嗎?不斷爭論該不該信任他的夏洛特與詹米,又該如何放下懷疑,解決福爾摩斯和莫里亞提即將爆發的又一場家族戰爭?
┤推薦好評├
「相信我:你不會想錯過如此天才之作的續集。」──克羅伊‧班傑明(《永生者》作者)
「系列第一集《夏洛特的研究》的書迷絕不會失望,新認識這群角色的讀者也會享受本書步調快速的劇情……徹底讓人捨不得放下。」──《VOYA》
「優美的文體、刺激的動作戲、一點點的浪漫情愫,加上兩位心思複雜、引人共鳴的主角,這本續集不可錯過。」──《書單雜誌》星級評論
「卡瓦拉羅這位初試啼聲的作家將柯南‧道爾筆下的偵探組合(或說是他們的遠親)帶到二十一世紀,將福爾摩斯設定成足智多謀的少女,敘事者華生則擔任她的粉絲兼同夥…….一部令人投入的謀殺懸疑故事。」──《出版人週刊》
| FindBook |
有 14 項符合
福爾摩斯家族II:奧古斯特的終局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圖書名稱:福爾摩斯家族II:奧古斯特的終局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布瑞塔妮‧卡瓦拉羅Brittany Cavallaro
詩人、小說家兼老派福爾摩斯研究者。她在米得伯里學院取得文學學位,並在威斯康辛─麥迪遜大學獲得詩歌類創意寫作學位,現為威斯康辛─密爾瓦基大學的英國文學博士候選人。
在福爾摩斯的同好社群中,她接觸到一個遊戲,參加者會假裝夏洛克、華生醫師、莫里亞提等角色都是真實的歷史人物,而眾所熟知的那些偵探故事均是有憑有據的回憶錄,亞瑟‧柯南‧道爾爵士其實是華生的文學經紀人。這個遊戲啟發了她創作《夏洛特的研究》等書的靈感。
她目前和丈夫與寵物貓定居在密西根,並且擁有一系列豐富的獵鹿帽收藏。歡迎參觀她的個人網站:www.brittanycavallaro.com
相關著作:《福爾摩斯家族:夏洛特的研究》
譯者簡介
蘇雅薇
倫敦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臺師大翻譯研究所雙碩士。喜歡為了休閒而閱讀,為了翻譯而閱讀。畢生志向是躲在書頁後面,用自己的筆,寫別人的故事。譯有《最好別想起》、《雌性物種》、《福爾摩斯先生收IV》等書。
半個福爾摩斯迷,翻譯過程中不時陷入想找出各種原著彩蛋的無限迴圈。
譯作賜教:pwk072347@gmail.com
相關著作:《福爾摩斯家族:夏洛特的研究》
布瑞塔妮‧卡瓦拉羅Brittany Cavallaro
詩人、小說家兼老派福爾摩斯研究者。她在米得伯里學院取得文學學位,並在威斯康辛─麥迪遜大學獲得詩歌類創意寫作學位,現為威斯康辛─密爾瓦基大學的英國文學博士候選人。
在福爾摩斯的同好社群中,她接觸到一個遊戲,參加者會假裝夏洛克、華生醫師、莫里亞提等角色都是真實的歷史人物,而眾所熟知的那些偵探故事均是有憑有據的回憶錄,亞瑟‧柯南‧道爾爵士其實是華生的文學經紀人。這個遊戲啟發了她創作《夏洛特的研究》等書的靈感。
她目前和丈夫與寵物貓定居在密西根,並且擁有一系列豐富的獵鹿帽收藏。歡迎參觀她的個人網站:www.brittanycavallaro.com
相關著作:《福爾摩斯家族:夏洛特的研究》
譯者簡介
蘇雅薇
倫敦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臺師大翻譯研究所雙碩士。喜歡為了休閒而閱讀,為了翻譯而閱讀。畢生志向是躲在書頁後面,用自己的筆,寫別人的故事。譯有《最好別想起》、《雌性物種》、《福爾摩斯先生收IV》等書。
半個福爾摩斯迷,翻譯過程中不時陷入想找出各種原著彩蛋的無限迴圈。
譯作賜教:pwk072347@gmail.com
相關著作:《福爾摩斯家族:夏洛特的研究》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