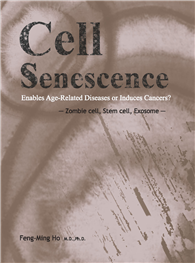圖書名稱:我想結束這一切
★授權22國外語版權
★入圍雪莉‧傑克森獎最佳長篇小說
★《出版人週刊》、《柯克斯書評》、《書單》、《圖書館期刊》星級推薦
★NPR年度好書、亞馬遜網路書店當月選書
大雪紛飛的公路上,「我」和男友傑克連夜開車要去拜訪他住在鄉下農莊的父母。沉悶的車程中,我們斷斷續續聊著天,卻不時被不明的手機來電干擾,電話另一頭的人,似乎對我的往事、生活習慣和目前動態全都瞭若指掌,我一再掛斷,神祕的語音留言卻一直伴隨著我們來到傑克的家。
深冬的農莊彷彿與世隔絕,傑克家人的熱情招待也無法驅散我一路上累積的不安:地下室裡多年前的畫作上,傑克畫的小孩旁邊總是有個突兀的人形;他的母親不停拔著已經稀疏的頭髮、抱怨耳朵裡傳來的怪聲;據說家裡還有另一個兒子,聰明絕頂但行為異常,曾經如影隨行地跟蹤傑克、模仿他的外表、入侵他的生活……
我們趕忙告辭,回程途中經過的商店,竟有素昧平生的店員表示替我感到害怕。而在遇雪封閉的學校裡停車休息時,原本對這些異狀不以為意的傑克發現有人從車外偷窺,終於激動地追出去,卻就此消失在空蕩的校舍,留下想要逃離但孤立無援的我。
陰森的場景、詭異的話語,膨脹的孤寂與恐懼從四面八方包圍而來,我該怎樣才能結束這一切?
在陌生荒涼而充滿壓迫感的場景中,看似甜蜜熱戀的男女主角面對感情的不安、遲疑、倦怠逐漸聚焦放大,使他們不斷重新估量彼此了解的程度、懷疑自己愛與信任的能力、焦慮於內心感受與客觀現實之間的脫節錯位,終至惶恐得無法辨別身邊詭譎的景物與事件,究竟是心魔的象徵還是真實的威脅。這是一部兼具懸疑性與文學性的驚悚小說,也是關於孤獨、疏離感與存在危機的深刻探索與漫長辯證。
作者簡介
伊恩‧里德Iain Reid
一九八一年生於渥太華,曾為加拿大廣播公司編寫劇本,出版《我想結束這一切》之前,另著有兩本紀實類作品《One Bird's Choice》及《The Truth About Luck》,其他文章散見於《紐約客》、《國家郵報》等報刊。
繼《我想結束這一切》成為國際暢銷小說、售出電影版權之後,新作《Foe》也再度刷新他的暢銷紀錄,並將由曾打造《漢娜的遺言》與《精神病學家》影集版的Anonymous Content製作公司進行影視改編,他本人將擔任執行製片。
譯者簡介
吳妍儀
中正大學哲研所碩士畢業,現為專職譯者,近年的譯作有《再思考》(麥田)、《哲學大爆炸》、《冷思考》(漫遊者文化)、《男人的四個原型》(橡實文化)、《死亡禁地》、《復活》(皇冠)等書。


 2020/02/07
2020/02/07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