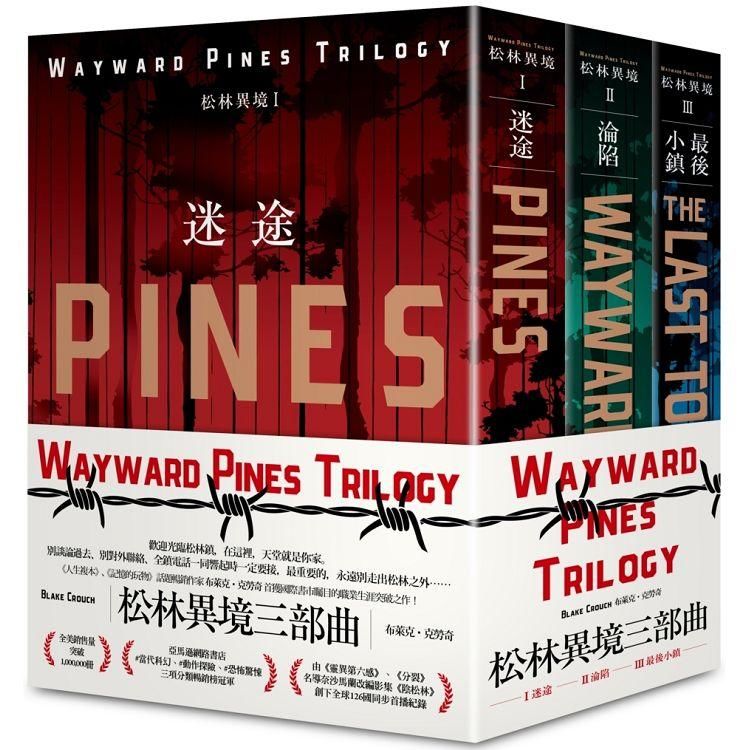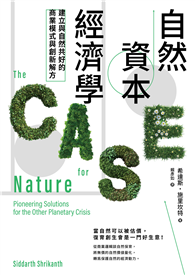他醒來時發現自己仰躺在地上,陽光亮晃晃地照在臉上,還聽到潺潺流水聲。他的視神經痛得要死,還可以感覺到頭蓋骨底部傳來持續卻不會痛的跳動,顯然是偏頭痛即將發作的前兆。他轉動身體,用手撐地坐了起來,將頭埋在兩膝之間。眼睛還沒打開,就已經感覺到周遭在浮動,彷彿坐標軸被切斷、成了蹺蹺板似地不停上下搖擺。他深深吸入一口氣,覺得好像有人用高爾夫的鋼製挖起桿用力重擊過他左邊最上方的肋骨。他呻吟著,還是強迫自己張開眼睛。他的左眼一定腫得很厲害,因為看出去的視線只剩一條非常窄的細縫。
他從沒見過這麼綠意盎然的畫面,又長又軟的綠草一直蔓延到河岸。清澈的河水在鵝卵石間飛快奔馳。河岸的另一邊聳立著一座超過千尺的懸崖。岩壁上長了許多簇高大的松樹,空氣中松香瀰漫,還有流水的清爽甜味。
他穿著黑長褲、黑西裝,白色的牛津襯衫上沾滿血漬。一條黑色的領帶自領口鬆垮垂下。
他試著起身,沒想到膝蓋癱軟,無法支撐身體的重量,他往後跌坐,震動的力道之大讓肋骨感到一陣劇痛。他鼓起勇氣再試一次。第二次,成功了。雖然雙腿軟得像麵條一樣,但好歹還能站。他感覺到地面宛如甲板似地晃動。他慢慢轉身,腳步踉蹌,小心跨出一大步以保持身體平衡。
他背對河流,眼前出現一大片空地。遠處的鞦韆和溜滑梯的金屬表面被正中午的毒辣太陽曬得閃閃發亮。
舉目望去,連個人影都沒有。
他看到公園旁有棟維多利亞式的房子,更遠的地方則是一排小鎮大街的建築。整個鎮最長不會超過一英里,四周被高達千尺的岩壁環抱,紅色斑紋的岩石如高牆般隔絕外界。而小鎮就像古羅馬露天劇院的競技場座落在正中央。最高的頂峰陰影處仍有積雪,但他所在的山谷卻十分暖和,頭上的天空則是一片萬里無雲的湛藍。
他先檢查長褲的口袋,再檢查單排扣西裝。
皮夾不見了。現金不見了。證件不見了。鑰匙不見了。手機不見了。
唯一留下的,是內袋裡一支小小的瑞士刀。
* * *
當他終於走到公園的另一頭時,神智清醒許多,卻也更加困惑。糟糕的是,他頸部感到的跳動已經轉變成偏頭痛。
他只記得六件事情:
現任總統的姓名。
他媽媽的長相。雖然記不起她的名字或聲音。
他會彈鋼琴。
他會駕駛直升機。
他三十七歲。
除此之外,這個世界和他所在的地點猶如一張他看不懂的外國學名表。他可以感覺到真相就在腦中的某處跳躍,可是即使他手伸得再長也抓不到。
他走上一條寧靜的住宅區道路,仔細觀察每一輛他經過的車子。其中有一輛會是他的嗎?
街道兩側的房子維持得相當好,剛油漆過的外牆、白色柵欄圈住的翠綠草地、黑色郵箱上拼出每戶人家姓氏的白瓷磚。
幾乎每個後院都生氣勃勃,不只種了花,還種了許多蔬菜和水果。
所有顏色都如此純淨、鮮明。
走到第二個街區的一半時,他感到一陣抽痛。走了這麼遠讓他有些上氣不接下氣,左胸的痛楚迫使他不得不停下腳步。他脫下西裝,把襯衫下襬從褲帶裡拉出來,解開胸口的鈕釦,拉開領子。看起來比他想像的還糟,他的左胸有個很長的暗紫瘀血印子,中間暗黃色的傷口又長又寬。
顯然他是被什麼東西撞了。而且力道極大。
他用手輕觸頭蓋骨的表面。頭痛還在,而且愈來愈嚴重,可是除了左胸的傷口,他身上其他部位似乎都沒受傷。
他把襯衫的鈕釦扣回去,下襬塞進褲腰,繼續在街上走。
得到的結論很模糊,他大概是出了什麼意外吧?
可能是被車子撞。也可能是跌倒。更可能是被人攻擊,所以他身上的皮夾才會不翼而飛。
他應該立刻去報警。
不過……
要是他做了什麼壞事呢?犯了罪之類的?
可能嗎?
也許他應該再等一下,看看待會兒還會再想起什麼事。
他對這個鎮似乎沒什麼印象。他突然發現自己一邊蹣跚走著,一邊唸著每個郵箱上的姓氏。是潛意識嗎?是因為在他擷取記憶的過程中,他知道其中一個郵箱會寫著他的名字嗎?知道如果他看見了,就能想起所有的一切嗎?
小鎮中心的建築物出現在松林樹梢間,就在幾個街區之前了。這是他第一次聽到車輛行進的聲音、遠遠的說話聲和中央空調的嗡鳴聲。
他在馬路中停住腳步,下意識地歪頭。
他瞪著一棟兩層樓紅綠相間的維多利亞式房子前的郵箱。
瞪著郵箱側面上的名牌。
他的脈搏變快,雖然他不知道為什麼。
麥肯錫
「麥肯錫。」
這名字對他沒有任何意義。
「麥肯……」
可是第一個音節似乎讓他想起什麼。或者,該說是激起了一點情緒反應。
「麥肯。麥肯。」
他是麥肯嗎?那是他的名字嗎?
「我叫麥肯。嗨,我是麥肯,很高興認識你。」
不對。
他舌頭唸出這名字的感覺並不自然。這名字不像是他的一部分。老實說,他討厭這個名字,因為它讓他聯想起……
恐懼。
真奇怪。不知道為什麼,他打從心底畏懼這個字。
曾經有個叫麥肯的人傷害過他嗎?
他繼續走。
再過三條街,他來到大街和第六街的交叉口。他在樹蔭下的長凳坐下,小心而緩慢地深呼吸。他環顧四周,試圖尋找任何看起來熟悉的事物。
沒有一家連鎖商店。
他坐的位子的斜對角是家藥房。
隔壁則是小餐館。
小餐館隔壁是棟三層樓的建築,垂掛的招牌上寫著:
松林大飯店
咖啡豆的香味讓他不由自主地站起身來。他左右查看,看到半條街外有間叫「熱豆子」的咖啡店。味道一定是從那裡飄出來的。
呣……
他想起來他對咖啡很講究。他很喜歡喝咖啡。雖然在目前的情況下,他寧願想起什麼別的,但至少這也算是拼湊自己是誰的過程中一塊小小的拼圖。
他走到咖啡店,拉開紗門。很精緻小巧的一家店。光是聞味道,他已經知道這裡的咖啡一定很不錯。右手邊的吧檯上擺著濃縮咖啡機、磨豆機、果汁機和各式調味飲料的玻璃瓶。三張高腳凳上都坐了人。吧檯對面則有幾張沙發和椅子靠著牆放。書架上排著不少褪色的平裝書。兩個實力懸殊的老先生在角落下棋。牆上掛了一系列中年婦女的黑白自拍照片,同樣的表情、不同的對焦,大概是當地藝術家的作品吧?
他走向收銀員。
二十多歲的金髮辮子頭女店員終於注意到他,他覺得她美麗的眼睛裡似乎閃過了一絲恐懼。
──她認識我嗎?
他在櫃檯後的鏡子看到了自己的影像,立刻明白為什麼她會露出嫌惡的表情。他左半邊的臉上有著大片瘀血,更糟的是他的左眼突出,腫得只剩一條縫。
──我的天啊!有人狠狠揍了我一頓。
除了可怕的瘀青之外,他看起來其實還不壞。估計他大概有六呎高,也許六呎一吋。黑色短髮,兩天沒刮的鬍子像影子似的籠罩住下半張臉。西裝下的肩膀輪廓和牛津襯衫下的胸線顯示他的身材結實強壯。他覺得自己看起來很像廣告行銷公司的高階主管,如果他能刮個鬍子、換件衣服,應該就百分之百合乎成功商界人士的刻板印象了。
「請問想喝點什麼?」女店員問。
他實在很想喝杯咖啡,可是他身無分文。
「你們的咖啡很棒嗎?」
女店員面露困惑。
「嗯,是。」
「全鎮最好的嗎?」
「這個鎮上就我們一家咖啡店,不過,是的,我們的咖啡非常棒。」
他傾身靠向櫃檯。「妳認識我嗎?」他輕聲問。
「什麼?」
「妳認得我嗎?我以前來過這兒嗎?」
「你不曉得自己以前有沒有來過這兒?」
他搖頭。
她仔細看著他好一會兒,想判斷眼前被揍得很慘的男人是認真的,還是瘋了,還是在耍她。
最後她說:「我相信我以前沒看過你。」
「妳確定嗎?」
「嗯,這是個小鎮,不是紐約巿。」
「有道理。妳在這兒工作很久了嗎?」
「一年多了。」
「所以我不是這家店的常客囉?」
「絕對不是。」
「我還能再請教妳另一件事嗎?」
「當然。」
「這裡是什麼地方?」
「你不知道你身在何處?」
聽到這問題,他猶豫了,一部分的自己並不想承認他是如此絕望無助。終於,他還是搖了搖頭。女店員眉頭皺在一起,彷彿對他的反應無法置信。
「我不是在耍妳。」他說。
「這兒是愛達荷州的松林鎮。你的臉……你出了什麼事?」
「我……我不知道。鎮上有醫院嗎?」話一出口,他立刻感覺到一陣不祥的預感爬上他的背脊。
只是不祥的預感嗎?
還是勾動了什麼深藏的記憶,才會讓他打從心裡覺得不舒服?
「有,再往南走幾條街。你應該馬上去急診室。我幫你叫輛救護車,好嗎?」
「不用麻煩了。」他從櫃檯後退。「謝謝……妳叫什麼名字?」
「瑪蘭達。」
「謝謝妳,瑪蘭達。」
再度走進陽光下讓他稍微失去了平衡感,也讓他的頭痛加劇。路上沒車,所以他橫過馬路,走到大街的另一邊,往第五街的方向前進。一個年輕媽媽帶著小男孩經過,孩子小聲地發問,聽起來像是:「媽咪,是他嗎?」
女人噓了孩子一聲,皺著眉,轉過來看著男人道歉:「真對不起。他不是故意要冒犯你的。」
他走到第五街和大街的交叉口,在一棟兩層樓的棕石建築前停下腳步。雙扇大門的玻璃上印著「松林鎮第一全國銀行」。他看到有個公共電話亭立在銀行旁的巷子前。
他跛著腳盡快走向電話亭,拉上門,把自己關在裡頭。
他從沒看過這麼薄的電話簿,他一頁又一頁地翻著,希望能看到什麼喚起自己的記憶。可是那不過是列印了幾百個名字的八張紙,就和這個鎮裡其他的東西一樣,對他都沒有任何意義。
被他扔下的電話簿在金屬線的牽引下前後跳動,他把前額靠在冰涼的玻璃上。
電話上的按鍵吸引了他的目光。
靈光一閃,他不禁微笑。
──我記得我家裡的電話號碼。
在拿起話筒前,他先在鍵盤上按了幾次以確定自己真的記得,他的指尖毫無困難地按著,彷彿肌肉也有屬於自己的記憶。
他打算要求對方付費,希望老天保佑有人在家,嗯……是說他有家人的話。當然,他沒辦法告訴他們是誰打來的,畢竟他到現在還想不起自己的名字,可是也許他們會認出他的聲音,願意接受這通電話。
他拿起話筒,放在耳朵上。
按下鍵盤上的零。
沒有嘟嘟嘟的撥號音。
他壓了壓掛勾,還是一樣。
他驚訝地發現自己居然立刻滿腔怒火。他用力掛上話筒,從心底湧出的恐懼和怒氣像突然竄出的大火吞噬了他。他將右手往後猛然一拉,意圖一拳打碎玻璃,也不顧指關節會受傷,但他左胸肋骨的痛突然間貫穿全身,讓他癱軟倒在電話亭的地上。
他頭蓋骨底部的劇痛更嚴重了。
他的視線先是重疊,再變模糊,最後終於轉成全黑……
* * *
當他再度睜開眼睛時,電話亭被籠罩在陰影中。他抓著連接在電話簿的金屬線,用力將自己拉起來。透過骯髒的玻璃,他看見太陽被小鎮西邊岩壁遮住了一半。
太陽一消失,溫度馬上掉了華氏十度。
他仍然記得他家的電話號碼。他又在鍵盤上按了幾次加深印象,再拿起話筒看看是不是有撥號音。一片寂靜中有一點點他之前似乎沒聽到的機器雜訊聲。
「喂?喂?」
他掛上話筒,再拿起電話簿。先看姓氏,他瀏覽著,期待有哪一個字會牽動他的記憶或讓他有情緒反應。然後看名字。他的食指在頁面上一路往下滑,努力試著忽視頭蓋骨底部揮之不去的疼痛。
第一頁。沒有。
第二頁。沒有。
第三頁。沒有。
到了第六頁末端時,他的手指頭停住了。
麥肯和珍.史考瑞
松林鎮東三街四○三號 559-0196
他很快地掃視過最後兩頁。史考瑞是松林鎮電話簿上唯一的麥肯。
他用肩膀輕輕撞開摺門,在傍晚時分走出電話亭。太陽已經完全沉入岩壁後面,天色很快暗了下來,氣溫也逐漸下降。
──我今晚要睡在哪兒呢?
他蹣跚地走上人行道,一部分的他無聲地尖叫著,勒令自己立刻去醫院。他又病、又渴、又餓、又困惑,而且身無分文。全身都在痛。每一次吸氣,他的肺頂到肋骨引起的痛楚讓他愈來愈難呼吸。
可是他的內心對「去醫院」這件事還是非常抗拒,而在他離開大街往麥肯.史考瑞的地址前進時,他才發現是為了什麼。
仍然是……恐懼。
他不知道原因。完全沒有道理。可是他一點都不想踏進松林鎮的醫院。
現在不想。永遠不想。
那是種很奇怪的恐懼。沒有特定的理由。就像夜裡在森林中獨行一樣,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怕什麼。也就是因為如此神祕,所以感覺更加可怕。
往北再走兩個街區,他到達第三街。他的胸部在他向東轉、背向巿區走時,不知道為什麼痛了起來。
他經過的第一個郵箱上印著二○一號。
所以史考瑞家應該再往下走兩條街。
前面的草地上有幾個孩子在嬉戲,輪流從噴水器旁跑過。走過籬笆時,他試著挺直身體,維持一定速度,但左胸肋骨的劇痛讓他還是忍不住往右偏斜。
他靠近時,孩子們全靜止不動,毫無掩飾地盯著他,看他慢慢走過院子前的人行道,混合了好奇和不信任的眼光讓他頗不自在。
他越過另一條馬路,腳步愈來愈慢。三棵巨大的松樹張開枝葉遮蓋住街區上的大片天空。
這一區全是色彩鮮明的維多利亞式房子,門牌號碼都是三字頭。
再過一條馬路,史考瑞家就要到了。
他的手心開始冒汗,他腦袋後的脈搏咚咚咚咚地跳,彷彿是一組被埋在地底的低音鼓。
眼前的畫面又晃了一下。
他緊緊閉上眼睛,再睜開時,視線又正常了。
他停在下一個路口。他本來就覺得渴,現在嘴巴更是變本加厲地又乾又澀。他掙扎著呼吸,卻在喉嚨嚐到膽汁的苦味。
──等到你看到他的臉,你就會明白為什麼了。
──一定會。
他猶豫地往前跨一步,踏上馬路。
快入夜了,冷空氣從山上降下,聚集在山谷裡。
反射在山頂積雪的微光將環抱松林鎮的岩石染上一層淡淡的粉紅,和愈來愈暗的天空呈現同一色調。他想領受周遭的美,想被感動,可是身體的痛讓他無心欣賞。
一對老夫妻手牽著手,靜靜地以散步的速度超過他。
除此之外,街上既空曠又安靜,完全聽不見大街上的噪音。
他穿越過平坦的黑色瀝青,踏上另一側的人行道。
前方的郵箱上印著四○一號。
下一個就是四○三號了。
現在他得一直瞇著眼睛,否則看到的全是雙重影像,而偏頭痛也更嚴重了。
艱難的十五步後,他站在漆著四○三號的黑色郵箱旁。
「史考瑞」
他抓住前院籬笆的尖端,穩住自己的身體。
他伸長手,拉開半腰高的柵欄鐵門上的閂子,用已經磨損的黑皮鞋稍微往前推。
門開了,轉軸發出刺耳的金屬摩擦聲。
矮門輕輕地撞上籬笆。
人行道上鋪的舊磚塊一路延伸到架了遮雨棚的前廊。兩張搖椅中夾著一張小小的鍛鐵桌。紫色的房子,綠色的飾邊。透過輕薄的窗簾,他可以看見裡頭的燈光。
──去吧!你總得把事情弄清楚。
他踉蹌地走向大門。
要壓抑下噁心欲吐的感覺愈來愈難,還要加上雙重影像的糾纏。
他踏上前廊,伸出手,剛好抓住門框才沒摔下去。他努力撐住身體。他抓住敲門的銅環,將它往上提,雙手無法控制地抖個不停。
他完全不給自己再考慮一下的機會。
他將銅環在金屬片上敲了四下。
感覺像有人每隔四秒就在他的頭上重擊一拳。他的視線出現許多小小的黑洞,像小昆蟲似地到處亂飛。
他可以聽到門的另一邊踩在硬木地板上由遠而近的腳步聲。
他的膝蓋頓時癱軟。
他抱住一根支撐前廊屋頂的柱子保持平衡。
厚重的木門被拉開,一個應該是他父親年紀的男人透過紗門瞪著他。高而瘦的身材,頭頂上有一撮白髮,山羊鬍,臉頰上不明顯的紅血管顯示他喝了不少酒。
「請問有什麼事?」男人問。
他站直身體,用力眨眼對抗嚴重的偏頭痛。他放開手,費力地站穩。
「你是麥肯嗎?」他可以聽到自己聲音中的懼意,相信眼前這個男人也聽得出來。
真討厭自己這副膽小怯懦的樣子。
老先生傾身靠向紗門,仔細打量自家前廊上的陌生人。
「你有什麼事?」
「你是麥肯嗎?」
「是。」
他移近一點,老先生的身影清楚許多,他能聞到他呼出的空氣中帶著紅酒特有的酸甜味道。
「你認識我嗎?」
「什麼?」
到了此時,恐懼已經發酵成怒氣。
「你。認。識。我。嗎。是你把我害成這樣的嗎?」
老先生說:「在這之前,我根本從來沒有見過你。」
「真的嗎?」他的雙手不由自主地握成拳頭。「這個鎮還有其他叫麥肯的人嗎?」
「據我所知,沒有。」麥肯推開紗門,鼓起勇氣踏上前廊。「兄弟,你看起來不大好。」
「我確實不大好。」
「你出了什麼事?」
「你告訴我啊!麥肯。」
屋子裡傳出一個女人的聲音:「親愛的?沒什麼事吧?」
「對,珍,沒事!」麥肯瞪著他。「不如我開車送你去醫院吧?你受傷了。你需要—」
「我不會跟你去任何地方的。」
「那麼,你到我家來做什麼?」麥肯的聲音透露著不耐煩。「我剛才說要幫你。你不要。好。可是……」
麥肯還在講,可是他的話卻開始消失,被他胃部發出的如雷響聲淹沒,聲音之大簡直像有一列火車正高速向他衝來。他眼前的黑洞數量更多了,世界不停晃動。他的腿再也不能支撐自己的身體。連五秒鐘都不行,如果他的頭沒在那之前先爆炸的話。
他抬頭看著麥肯,他的嘴巴還在動個不停。那列火車發出巨響衝向他,密集的聲量一拳一拳殘忍地重擊著他的頭。可是他沒辦法把視線從麥肯的嘴巴移開,老先生的牙齒閃閃發光,上下接合,不斷地製造出聲音。天啊!那個聲音,那種抽痛—─
他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膝蓋癱軟。
甚至沒有發覺他正在往後倒。
上一秒鐘他還站在前廊。
下一秒鐘他已經躺在草地上。
背部著地,直挺挺地躺著,頭顱因重重撞上地面而昏眩不已。
現在,麥肯在他上方盤旋,先檢視他,再將雙手按在膝蓋上,彎腰。老先生不知道仍然在說些什麼,可是腦子裡的火車聲實在太大了,他什麼都聽不到。
他就要失去意識了……他可以感覺到,再過幾秒鐘……他不想再受疼痛的折磨,失去意識確實蠻不錯的,可是……
答案。
就在那裡。
這麼接近了。
一點道理都沒有。可是麥肯的嘴巴裡有東西。他的牙齒。他無法將視線移開,他不知道為什麼,可是他要找的東西就在那裡。
真相。
一切的解答。
然後他突然想到了……不要再掙扎。
不要再這麼想找到它。
不要再想了。
就讓它自己來找他吧!
那排……牙齒……那排牙齒……那排牙齒那排牙齒那排牙齒那排牙齒那排牙齒……
它們不是牙齒。
它們是一片閃閃發亮的格柵,上頭鑲了字:
麥肯
就鑲在最前面。
坐在他旁邊副駕駛座的史塔寧斯沒機會看到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史塔寧斯顯然很喜歡自己的聲音,所以從博伊西出發往北開了三個小時之後,他仍然一直說個不停。自從一個小時前他發現只要每五分鐘講些「我倒沒那麼想過」或「嗯……真有趣」之類的話就可以矇混過去後,他的耳朵已經自動關上了。
當他看到大卡車水箱罩上的車廠名稱「麥肯」出現在史塔寧斯的窗戶外距離只剩幾英尺時,離他上次搭話的時間正好差不多五分鐘了,所以他剛巧轉頭準備隨便說點什麼。
他才看見那兩個字,還來不及反應,史塔寧斯那側的窗子就已經被炸成成千上萬片碎玻璃。
安全氣囊從機柱爆出來,可是遲了百分之一秒,剛好錯過他撞向擋風玻璃的頭。撞擊的力量很大,大到他的頭撞穿玻璃。
林肯大型轎車的右車身被擠爛,粉碎的玻璃和扭曲變形的金屬四濺,史塔寧斯的頭更是直接被大卡車的水箱罩格柵撞上。
他可以感覺到擠壓進來的大卡車引擎噴出熱氣。
汽油和剎車油突然冒出的臭味。
到處都是血漬。鮮血從破裂的擋風玻璃內側流下來,噴灑在儀表板上,噴進他的眼睛裡,從史塔寧斯的殘骸上不斷噴出。
他駕駛的轎車被大卡車斜斜推過分隔線。就在它被推向巷口有個電話亭的棕石建築之前,他已經昏了過去。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松林異境三部曲(幽林X高牆意象設計新版套書)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629 |
驚悚/懸疑小說 |
$ 710 |
歐美小說 |
$ 809 |
文學作品 |
$ 809 |
Literature & Fiction |
$ 899 |
中文書 |
$ 899 |
美國文學 |
$ 899 |
超值套書 |
$ 899 |
Literature & Fiction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松林異境三部曲(幽林X高牆意象設計新版套書)
別談論過去、別對外聯絡、全鎮電話一同響起時一定要接,最重要的,永遠別走出松林之外……」
如果沒看見峭壁下的骨骸、如果沒聽到林中傳來的尖叫、如果不是怎麼繞也離不開松林鎮,
也許,他會相信這裡真是天堂。
●《人生複本》、《記憶的玩物》話題暢銷作家布萊克‧克勞奇首獲國際書市矚目的職業生涯突破之作!
●全美銷售量突破1,000,000冊
●亞馬遜網路書店#當代科幻、#動作探險、#恐怖驚悚三項分類暢銷榜冠軍
●由《靈異第六感》、《分裂》名導奈沙馬蘭改編影集《陰松林》,創下全球126國同步首播紀錄
這裡有如畫的風景、純樸的人民,
周圍卻是通電的圍牆與荒涼的絕境,
松林鎮的美好幻象之下,是個黑暗的謎團,
然而松林之外的秘密,卻更加駭人……
I迷途 PINES
歡迎光臨松林鎮,在這裡,天堂就是你家。
伊森‧布爾克在松林裡的河邊甦醒,腦中只記得六件事:現任總統的名字、他母親的長相(但不記得她的姓名或聲音)、他會彈鋼琴、他會駕駛直升機、他三十七歲、他身受重傷且亟需就醫。
伊森身上既沒有證件也沒有皮夾,他蹣跚走到鎮上,發現鎮民們過著純樸鄉村生活。鎮上的人說從沒見過他這個人,伊森好不容易記起他家在西雅圖,查號台卻表示查無此人。
松林鎮的夜晚寒冷寧靜,只聽得見蟋蟀鳴叫,伊森循聲撥開草叢,卻發現蟲鳴是從擴音器裡傳來;他與一名鎮民交談,卻發現她不知道什麼是臉書、誰是歐巴馬、還認為現在是一九五○年;伊森不顧傷勢,一心想逃離這座陰陽怪氣的小鎮,他闖入松林,卻聽見不知名生物的淒厲尖叫,更在岩壁下方發現破碎的骨骸。更詭異的是,不管伊森怎麼走,總是會鬼打牆般地重新回到鎮上。
他不知道這個小鎮到底隱藏了什麼秘密,但他可以確定的是:這裡絕不是天堂。當伊森再度試圖逃跑,全鎮五百多支電話一同響起,他看見原本純樸善良的鎮民換上華麗的嘉年華禮服,還拿起鐵鍬、菜刀、榔頭等武器聚集到廣場上……
怎麼可能會有走不出去的小鎮?為什麼沒人相信他是誰?為什麼他不能與外界聯絡?通電圍牆是為了不讓鎮民出去、還是防止外面的東西進來?伊森發現這個鎮遠比他想像中的恐怖許多,然而更巨大、更駭人的秘密,還在松林之外等著他……
II淪陷 WAYWARD
松林鎮也許不是天堂,但絕對是最後的庇護所,
若是想逃離這段神祕而美麗的無期徒刑,死亡會朝你直撲而來……
伊森•布爾克窺見了松林鎮的黑暗秘密,他原本想逃,卻赫然發現外頭的世界比疑雲密布的小鎮更加駭人。為了保護家人和鎮民,伊森不得不和一手打造松林鎮的科學家碧爾雀合作,接下小鎮警長一職。但在調查一群看似企圖叛逃、還涉嫌謀殺無辜鎮民的「徘徊者」時,伊森發現他的昔日好友竟也是其中一員,更發現碧爾雀比他想像中的更瘋狂,兩人之間的裂痕因此愈來愈大。
更雪上加霜的是,伊森的妻子泰瑞莎快要無法忍受松林鎮的詭異生活,執意挖掘危險的真相,而他的兒子似乎在學校接受了洗腦教育,竟將創造松林鎮的碧爾雀奉為上帝。
眼看家人愈來愈疏離,伊森掙扎著,是否要推翻碧爾雀的高壓統治?是否該告訴妻子與鎮民,這美麗的小鎮其實既是牢籠也是堡壘?此時,又有另外一場狂歡會即將到來,而外面世界中蠢動著的危險愈來愈強大。若是通電圍牆的電力被切斷,還有什麼能擋得住那些虎視耽耽、渴望入侵小鎮的東西……?
III最後小鎮 THE LAST TOWN
這裡是愛達荷州一座名為『松林鎮』的小鎮。
座標44° 13 0"N,114° 56 16"W。有人聽見嗎?
圍牆還環繞著小鎮的時候,松林鎮的人們雖然活在二十四小時的監視之下,至少能安全地呼吸;雖然他們不能擅自離鎮、不能對外聯絡,至少不必和家人生離死別。管如此,仍然有人認為這裡是天堂──直到伊森‧布爾克戳破了幻象,激怒了小鎮的創造者,使他惡意切斷了通電圍牆的電力、讓地獄進門肆虐。
伊森懊悔不已,認為從前鎮民雖然活在二十四小時的監視之下,至少能安全呼吸;雖然不能擅自離鎮、不能對外聯絡,至少不必和家人生離死別。但伊森已經沒時間自責,因為他還得保護鎮民和妻兒、帶領他們到安全之處,然後找到重新啟動通電圍牆的方法。昔日他拚命逃離且恨之入骨的地方,如今竟成了必須全力捍衛的家園。
但伊森沒料到,鎮民棲身的避難所並不如他想像中安全,從外面世界返回的探險者也帶來更令人絕望的消息。在這一切混亂中,他甚至必須面對最親近的人隱瞞已久的祕密,而最讓伊森措手不及的,莫過於關乎松林鎮命運的殘酷真相……
他揭開了松林鎮的美麗外衣,也擊碎了它的邪惡骨架,卻發現裡頭藏著的,只是人類最脆弱的本質。當生存已變成最奢侈的願望,他們要付出多少代價才能換得?
┤推薦好評├
《羊毛記》作者休‧豪伊:「你絕對猜不到克勞奇下一步要將你帶往何處。」
《懸疑雜誌》(Suspense Magazine):「布萊克.克勞奇在《松林異境》裡創造了一個逼真而恐怖的世界。」
全美最大讀書網站Bookreporter.com:「每個人都可以在《松林異境》找到自己想看的東西。神祕的謀殺案、大量的動作戲、精采的科幻故事,足以迷倒一大群讀者,讓他們守在出口不斷尖叫:『布萊克!布萊克!布萊克!』這系列寫得非常好,栩栩如生,緊張刺激。在口耳相傳中,它的名聲日漸響亮,相信它的粉絲數目也會跟著成倍數成長。」
美國書評網站Top of the Heap Reviews:「看完《松林異境》後你會咒罵布萊克.克勞奇為什麼沒有馬上推出下一集……也許一百分的小說在世上並不存在,但對我來說,這一本已經趨近完美。」
美國恐怖電影、電視、小說評論網站bloody-disgusting.com:「我和許多人一樣,在閱讀《松林異境》時不禁懷疑作者花了這麼多時間布局是否值得。可是克勞奇在第一集結束時埋下了一個會讓史帝芬‧金羞愧臉紅的厲害伏筆。」
作者簡介:
布萊克.克勞奇Blake Crouch
一九七八年出生於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從小就愛說故事,弟弟喬丹(Jordan Crouch)是他的第一個聽眾,兩兄弟長大後甚至還合寫了一本哥德驚悚小說《毛骨悚然》(Eerie)。克勞奇擁有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語文與創意寫作學位,並發表了為數眾多的中、短篇小說和雜文。二○一一年出版的獨立作《逃》(Run)已是亞馬遜網路書店電子書暢銷排行榜前十名的熱門小說,隔年的《松林異境》三部曲更是讓他正式獲得國際矚目的突破之作,全美銷售量超過一百萬冊,並由美國福斯電視台改編為影集《陰松林》。他的近作《人生複本》(Dark Matter)和《記憶的玩物》(Recursion)均迅速以高價售出電影、電視版權,已推出的影視改編作品另外還有懸疑影集《一善之差》(Good Behavior)。
他自述其寫作風格深受多位名家影響,包含《納尼亞傳奇》作者C.S. 路易斯、《長路》作者戈馬克.麥卡錫、驚悚小說大師史蒂芬.金與《隔離島》作者丹尼斯•勒翰。
克勞奇現居克羅拉多州杜蘭戈巿,仍舊持續創作驚悚刺激的故事。《羊毛記》作者休豪伊如此誇讚克勞奇:「他的確很會寫作,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怎麼訴說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
相關著作:《松林異境2:淪陷》《松林異境3:最後小鎮》《松林異境:迷途》
譯者簡介:
卓妙容
臺灣大學會計系畢業,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企管碩士。曾任職矽谷科技公司財務部十餘年。譯有《打造暢銷書》、《金融吃人魔:如何與高風險市場共舞》、《美人心機》、《百分之七的溶液》等書。
章節試閱
他醒來時發現自己仰躺在地上,陽光亮晃晃地照在臉上,還聽到潺潺流水聲。他的視神經痛得要死,還可以感覺到頭蓋骨底部傳來持續卻不會痛的跳動,顯然是偏頭痛即將發作的前兆。他轉動身體,用手撐地坐了起來,將頭埋在兩膝之間。眼睛還沒打開,就已經感覺到周遭在浮動,彷彿坐標軸被切斷、成了蹺蹺板似地不停上下搖擺。他深深吸入一口氣,覺得好像有人用高爾夫的鋼製挖起桿用力重擊過他左邊最上方的肋骨。他呻吟著,還是強迫自己張開眼睛。他的左眼一定腫得很厲害,因為看出去的視線只剩一條非常窄的細縫。
他從沒見過這麼綠意盎然的畫面,...
他從沒見過這麼綠意盎然的畫面,...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