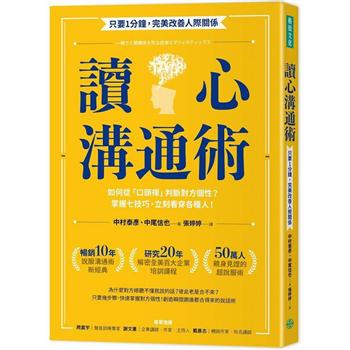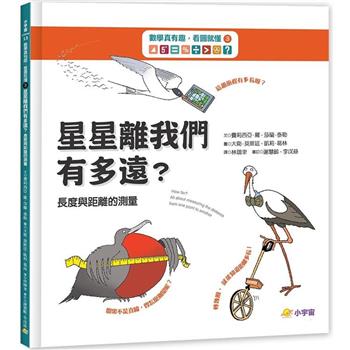第五章 優勝美地(節錄)
七月十五日
順著莫諾山道,前往谷地東邊接近山頂之處,之後往南走,到優勝美地邊緣小而淺的山谷。我們大約在中午抵達後紮營。午餐後,我急忙前往高地。從印第安峽谷(Indian Canyon)西邊的山脊邊緣可眺望頂峰,那是我見過最壯闊的景色。美熹德河上方的盆地幾乎盡收眼底,有雄偉的圓丘與峽谷、大片黑黝黝的森林往上蔓延,還有一片壯麗的白色山峰直指天際。一切都綻放光芒,散發出的美感宛如火焰之光,注入我們體內。四處陽光普照,沒有一絲風打擾這片沉靜。我從未見過如此耀眼的風景,宏闊的山巒之美如此豐富無垠。若非親眼目睹這番景色,無論我以如何華麗的詞藻,也無法窮盡此處的偉大與充滿靈性的光輝。我在一陣狂喜中吶喊,比手畫腳,令卡洛大吃一驚。牠跑向我,聰明的眼神疑惑擔憂地望著我,似乎認為我太滑稽,這才讓我恢復理智。有隻棕熊似乎也看見我方才的誇張行徑。我才走幾步就看見一隻棕熊躲在樹叢中。牠顯然認為我很危險,立刻拔腿就跑,匆忙間還在糾結的熊果屬樹叢中絆倒。卡洛往後退,彷彿憂懼得雙耳下垂,似乎在期盼我去追那頭熊並開槍,畢竟牠經歷過不少與熊的戰爭。
我沿著逐漸往南方下降的山脊前進,終於來到一處龐大懸崖的坡頂。這座懸岩位於印第安峽谷與優勝美地瀑布之間,來到這裡,這名聞遐邇的谷地全景一覽無遺。壯觀的岩壁化為無數的圓頂與山牆、高塔與城垛,以及單純的峭壁,隨著瀑布奔落的轟隆水聲而顫動。平坦的底部有如花園,到處是陽光普照的草原,還有松樹與橡樹林;美熹德河威武掃過其間,在陽光下熠熠發光。巨大的提賽克(Tissiack,或稱為「半穹丘」〔Half-Dome〕)從谷地較高之處拔地而起,高度近乎一哩,外觀雄偉勻稱,宛若有生命,是所有岩石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見過的人莫不誠心讚嘆。無論把目光移向瀑布、草原或後方的山,最後仍將回歸此處——這是奇妙的懸崖,陡直的深度與鬼斧神工的雕刻令人目眩神迷,散發出堅毅之情,在蒼穹下屹立數千年,歷經雨雪冰霜,地震雪崩,卻依然洋溢著青春活力。
我沿著谷地邊緣往西漫走;峭壁的邊緣多半已磨蝕成圓形,要找能把整座山壁從頭看到尾的地方並不容易。每回找到這樣的地方,都必須小心翼翼站穩,身體挺直,這時總忍不住擔心,要是岩石裂開,導致我失足墜落怎麼辦——這次一摔可是超過三千呎。不過,我的四肢並未顫抖,也毫不懷疑可以信賴自己的肢體。我唯一擔心的是這裡的片狀花崗岩層有些節理空隙較大,且與峭壁面平行,容易崩裂。每回從這些地方退回之後,我總因為方才所見的景象興奮不已,並告訴自己:「可別再探出邊緣了。」只是在優勝美地的景色面前,謹慎勸誡發揮不了功用;在優聖美地的魔力之下,身體有自己的意志,想往哪兒走就往哪兒走,幾乎難以控制。
在這令人難忘的峭壁走了一哩左右,我走近優勝美地溪,讚嘆此處悠閒、優雅與自信的姿態,在狹窄的河道上勇往直前,唱著最後一段山歌,迎向自己的命運——在閃亮的花崗岩上流幾桿(rod,約為五公尺)後,化為炫目的水沫,往下俯衝約半哩,進入另一個世界,消失在美熹德河之中,那裡的氣候、植被、居民都截然不同。從最後一個峽谷冒出來之後,又流入絲帶般的寬闊激流,之後往平緩下坡流入水潭,讓興奮不已的灰色水流稍事休息,為最後一跳做準備。隨後,水緩緩滑到水潭邊緣,再從另一處光滑的斜坡流下,加速往懸崖邊緣前進,以崇高的自信迎向宿命,自由躍入空中。
我脫掉鞋與長襪,小心沿著奔流的溪水而下,手腳緊緊攀著光滑的岩石。轟隆怒吼的水就在我頭附近奔流,委實刺激。我原本以為,斜斜的冰磧沉澱終點就是垂直的岩壁,而我從不那麼陡峭的斜坡末端探出身子,應可看到整座瀑布奔往底部的形態與行為。但我發現,原來還有一處小峭壁頂端擋住我的視線,那小峭壁頂太陡峭,無法涉足。我敏銳掃視,發現在峭壁邊緣有約三吋寬的狹窄岩架,剛好夠我放上後腳跟。但小峭壁頂過陡,我無法越過,走到岩架所在之處。最後,在小心審視岩石表面之後,我發現在激流邊緣後方一段距離處,有一段不規則岩層。如果我想要到小峭壁邊緣,唯一的辦法就是讓手指攀著那一片不規則的岩層。不過,一旁的斜坡看起來平滑陡峭,相當危險,而上下與身旁的急流轟隆,令人心驚膽跳。我明知不該冒險前去,但還是去了。一叢叢的艾屬植物從附近的岩縫冒出,我嘴裡塞滿艾屬的苦葉,盼能阻止暈眩感。之後,心中一股平常沒有的謹慎油然而生,我安全爬到這小岩架上,腳跟穩穩踩著,並水平挪二、三十呎,總算看見往下俯衝的水流。水流下降到這個高度時已經呈現白色。我在這裡清清楚楚看見瀑布吟唱著俯衝,分散成雪白如彗尾的長光。
我停留在那狹窄的岩架上時,並未特別感受到危險。瀑布的形體、聲音與動作無比壯觀,且近在咫尺,因此遏止了我的恐慌,而在這種地方,身體會自行留意安全。我其實不太清楚自己究竟在那裡停留了多久,或是如何返回。總之,我在那裡度過輝煌的時光,大約天黑之後回到營地,享受勝利之喜,隨後隱隱的疲憊感浮現。以後我將避免前往那樣奢侈、那麼讓人繃緊神經的地方,但這一天的冒險實在值得。我初次看見內華達高山,第一眼俯看優勝美地、傾聽優勝美地溪的死亡之歌,以及目睹這條溪飛越龐大的絕壁,每一項都足以成為一生中最珍貴的財富。這是最值得紀念的一日,甚至可以因此狂喜而死。
七月十八日
一夜好眠。雖然我在半夢半醒中,以為自己站在峭壁邊緣,一旁是白色的洪流往下奔去,但山谷似乎沒有崩塌。怪的是,我現在身處平靜的森林中,距離瀑布邊緣已有一哩以上,卻更加感受到那趟冒險旅程的危險。
從足跡來看,這裡似乎常有熊出沒。大約中午時分又下了一場暴雨,雷聲震天,那是帶有金屬碰撞感的巨響,再漸漸化為低沉的遙遠呢喃。有幾分鐘,滂沱的雨水有如瀑布,接著又下了冰雹,有些直徑長達一吋,質地堅硬冰冷,形狀不規則,和威斯康辛州常見的一樣。聰明的卡洛驚奇盯著冰雹落下,打在樹木顫抖的枝枒間。雲景壯觀。下午平靜晴朗,相當清新,冷杉、花朵與地面的蒸氣,帶來甜美新鮮的芬芳氣息。
七月十九日
觀看破曉與日出。淡粉紅與紫色的天空,緩緩變成水仙黃與白,陽光流瀉至山峰之間的隘口,進入優勝美地穹丘,使得這些地方的邊緣如火燃燒;中間地區銀冷杉尖塔般的樹頂沾染光芒,營地旁的樹林在燦爛日光中興奮不已。萬物甦醒,歡欣鼓舞;鳥兒與無數的蟲子開始有了動靜,鹿悄悄退到灌木叢裡的濃密枝葉中;朝露消失,花朵張開花瓣,每一個脈搏皆有力跳動,所有生物細胞歡歡喜喜,連岩石似乎也充滿生命力。眼前景致宛若人臉般容光煥發,充滿熱情,而藍色天空在地平線處已泛白,宛如一朵巨大的花靜靜彎腰,籠罩一切。
大約中午,巨大的積雲和往常一樣逐漸在森林上方聚集。從中傾瀉而下的暴雨,是我見過聲勢最驚人的。銀色的之字形閃電光芒宛若長矛,長度更勝以往,而雷聲之大令人震撼,熱烈碰撞、密集發生,以強大的力量說話,彷彿每次雷擊都會粉碎一座山,但或許只有幾棵樹被擊碎;我在附近散步時,總會看見地上散落著遭雷擊的樹木。終於,清晰的雷鳴被低沉的聲響取代,越漸模糊,朝雷聲迴盪的山坳遠去,那裡似乎歡迎雷鳴回家。之後又是一聲聲的轟然雷鳴接踵而至,接下來雷霆萬鈞的雷擊,或許會將巨大的松樹或冷杉從頭到尾劈成長條與裂片,往四面八方散落。現在雨來了,同樣氣勢宏輝地以流動的水幕罩住高山與低谷,透明的薄膜宛如一張皮膚,放在大地崎嶇的結構上,讓岩石閃亮發光,並在壑谷集合,湧入溪流,讓它們以震天吶喊呼應雷聲。
追溯一滴雨水的歷史多有趣!從地質學來看,最初的雨水滴落在沒有葉子、初新生的內華達山脈地景,並不是很久以前的歷史。這些落下的雨水和當初大不相同!陣雨開心落在美麗的荒野,每一滴雨落下之處莫不迷人——山巔、閃亮的冰河河道、巨大平滑的穹丘頂、森林與花園、長著灌木的冰磧土上;雨水濺起水花、閃耀、啪嗒作響、洗滌四下。有些來到高處覆蓋白雪的山泉,增加豐沛的儲量;有些來到湖邊,洗淨山之窗,拍拍平滑如玻璃的湖面,掀起波紋漣漪、泡沫與水花;有些進入大小瀑布,彷彿急於想加入它們的舞蹈與歌聲,激起更細緻的水花;山中快樂的雨滴既幸運又努力,每滴都是高處的瀑布,從雲中的懸崖與凹地,落到岩石間的絕壁與凹處,從天空霹靂隆隆之處,來到瀑布水聲轟轟之處。有些落入草原與沼澤,悄悄爬進看不見的草根中,溫柔躲藏起來,宛如置身巢中;雨滴滑動、四處滲透,搜尋與找到分派的工作。有些從樹林的尖塔落下,從閃亮的松針之間篩下,彼此輕輕呢喃著平安與鼓勵。有些雨滴的快樂目標是在礦石晶體側邊發光——石英、角閃石、石榴石、鋯石、電氣石、長石——打在金塊結晶,以及歷經長途旅行而磨損的天然金塊上;有些發出低而頓的咚咚鼓聲,落在藜蘆屬、虎耳草屬、杓蘭屬的寬大葉子上。有些快樂的雨滴直接落入花萼中,親吻百合的唇瓣。無論還得走多遠、要裝多少容器,都同樣悉心填充:有的是小到看不見的細胞,有的容器裝半滴水就滿了,有的則大如山間的盆地湖。在備受祝福的雨水中,每一滴雨都是湖與河、花園與樹林、山谷與山嶺的銀色新星;大地擁有的一切都反映在雨滴晶瑩剔透的深處;雨滴是上帝的使者、天使送來的愛,雨的氣象萬千與展現的力量,使得人類最卓越的表演顯得微不足道。
暴雨結束,天空清朗,最後一波雷鳴消失在山巔。雨滴在哪裡——那閃亮的線條變成什麼了呢?有些藏在長著翅膀的水蒸氣中上升,速速返回天空;有些進入植物中,爬到看不進的門戶,來到細胞的圓形房間中;有些鎖在冰晶裡;有些在岩石結晶體中;有些在冰磧石的孔隙裡,保持小小的泉水流動;有些隨著河流踏上旅程,加入汪洋這更大雨滴中。從一種形態轉化到另一種形態,從一種美變換成另一種美,雨滴持續改變,從不休息,悉數帶著愛的熱忱加速,與星辰一同唱出永恆的創造之歌。
-
第七章 奇特經驗(節錄)
八月二日
多雲、陣雨,與日昨相仿。整日在北穹丘素描,直到下午四、五點。我全心沉醉於優勝美地的美景,設法畫下每棵樹、每座岩石的所有線條與特色。在毫無預警之下,心中忽然浮現了一個念頭:我的朋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的巴特勒(J. D Butler)教授就在下方的山谷。我一心一意只想見他,那股令人驚訝的興奮之情,宛如他突然碰了我,要我抬頭看。我不假思索便放下工作,從北穹丘西面的山坡奔下,沿著谷壁邊緣尋找一條通往底下的路。我來到側面的一道峽谷,從綿延不絕的樹木與灌木叢來看,認為這裡應可通往山谷。雖然時間已晚,我立刻開始往下,彷彿被難以抵抗的力量拉著走。但過了一會兒,常識阻止我續往前行;待我找到旅館時天早已黑,訪客已入睡,沒有人認識我,我的口袋空空,甚至連外套也沒穿。因此,我迫使自己停下腳步,恢復理智,要自己別在黑暗中尋找朋友——我只是有一種奇特的心靈感應,認為他就在那裡。我拖著身子穿過森林,返回營地,但是明早就下山找他的決心未曾動搖。我從未有過如此難以解釋的念頭。多日來,我坐在北穹丘,要是有人在我耳邊悄悄說巴特勒教授在山谷,我肯定無比詫異。當我離開大學時,他說道:「約翰,與我保持聯絡,我要看你發展事業。答應我,一年至少寫一封信給我。」七月我在山谷的第一處營地,曾收到他五月時寫的信。他在信中說,今年夏天可能造訪加州,盼能見到我。不過,他並未提到見面地點,也未說明他可能循哪條路來,加上我整個夏季身處荒野,絲毫不抱相見的期待,也沒把這件事放在心上,直到這天下午,他似乎親自從我面前飄過。明天答案就會揭曉;無論是否合理,我都認為應該走一趟。
八月三日
度過美好的一日。我像指北針找到北極,找到了巴特勒教授。昨晚的心靈感應、超自然啟示或無論如何稱呼的經歷,果然應驗。說來奇怪,他剛由庫爾特維爾山道進入谷地,經過酋長岩(El Capitan),正要上來山谷時,我就感覺到他的存在。若他看到北穹丘的第一眼,就用很好的望遠鏡觀看,或許會看到我從工作中跳起,朝他奔來。這堪稱是我人生中最明確的超自然奇蹟;畢竟我從少年時代開始醉心於美好的大自然之後,就不再對招魂術、預知能力、鬼故事等諸如此類的事物感興趣;那些事物顯然較為無用,美妙之處也遠遜於開放、和諧、樂音飄揚、充滿陽光與日常之美的大自然。
今天早上,我想到前往旅館會遇見其他旅客時不免煩心,因我沒有適當衣服,免不了一番困窘。不過,兩年來身邊盡是陌生人,我鐵了心要見老朋友;我找了一條乾淨的工作褲、喀什米爾羊毛襯衫與類似夾克的外衣——我營地衣櫃裡最好的服裝——將筆記本繫在腰帶上,便跨著大步,踏上奇怪的旅程,卡洛就跟在後頭。我穿越昨晚發現的峽谷,原來那就是印第安峽谷。峽谷裡沒有步道,布滿岩石與灌木叢,相當崎嶇難行,因此卡洛不時喚我回頭,帶牠脫離險峻。從峽谷陰影出來之後,我發現一名男子在草原上製作乾草,遂詢問巴特勒教授是否在這山谷中。「我不知道,」他回答,「去旅館問問吧,很容易問到答案。現在山谷裡的遊客不多。昨天下午有一小群人來,我聽見有人叫作巴特勒教授,或者巴特菲之類的名字。」
在昏暗的旅館前面,我看到一群旅人在調整釣具。他們一語不發,好奇盯著我,彷彿我從雲間穿過樹林掉落,我想大概是因為我奇怪的衣著。我詢問辦公室在哪兒,他們說,鎖起來了,旅館老闆不在,但我或許可以找老闆娘哈金森太太,她在會客廳。我在困窘的狀態下進入房裡,在空蕩蕩的大房間等待,敲了幾扇門之後,老闆娘總算出現了。她說巴特勒教授應該在山谷裡,但要確認的話,她得從辦公室拿房客登記本查查。我在最後抵達的幾個人名中,很快發現教授熟悉的筆跡。一看到他的名字,我的靦腆就煙消雲散;原來他同友人往山谷上去了——或許是到春天瀑布(Vernal Fall)與內華達瀑布(Nevada Fall)——我歡欣地趕忙追去,確定找到了要找的人。不到一個小時,我便抵達內華達峽谷頂端的春天瀑布,而就在水霧之外,我發現一名相貌出眾的紳士,他和我今天見到的其他人一樣,以好奇的眼光走近我。待我大膽詢問他認不認識巴特勒教授拉特蘭市(Rutland)是同學。」「他現在在哪呢?」我追問,沒讓他繼續話當年。「他和一名同伴到瀑布後面去了,想攀登那巨大的岩石,你從這裡就可以看到它的頂端。」他的嚮導這會兒開口了,說巴特勒教授和同伴去爬「自由之帽」(Liberty Cap)。如果我在瀑布源頭等,他們下來時應該會碰得到面。於是,我從春天瀑布旁的階梯往上走,一心前往自由之帽岩頂,而不是在那枯等,只盼能早點見到面。無論一個人的人生多麼快樂滿足、無憂無慮,總有些時候會渴望見到活生生的朋友。然而沒走多遠,我就在春天瀑布頂端看見他在灌木叢與岩石間,他半彎著腰,沿路摸索,袖子捲起、背心打開,手拿帽子,顯然又熱又累。他見到我來,就在一塊大石坐下,抹去額頭與頸部的汗水。他以為我是山谷嚮導,遂問我該如何前往瀑布的階梯。我指著用小石堆標示的小徑,於是他告訴同伴找到路了;只是,他尚未認出我。之後,我直接站到他面前,看著他的臉,伸出我的手。他以為我是要幫助他起身。「沒關係。」他說。之後我說:「巴特勒教授,你不認識我嗎?」「恐怕不認識。」他回答;但當他迎向我的眼神時,馬上認出我。他驚訝極了,沒想到我會找到在灌木叢迷路的他,全然不知我就在他幾百哩的範圍內。「約翰.繆爾、約翰.繆爾,什麼風把你吹來了?」於是我告訴他,昨天傍晚他進入山谷時,我時,他似乎更加好奇,想知道究竟為何會有個傳訊人來找教授。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反而以軍隊簡單嚴厲的口吻問:「誰要找他?」「我要找他。」我同樣嚴厲地回答。「為什麼?你認識他?」「是,」我說,「你認識他?」他很驚訝山上竟然有人認識巴特勒教授,何況教授才剛到山谷。於是,他總算平等看待這陌生的登山者,客氣回答:「是,我和巴特勒教授很熟。我是阿爾沃將軍,很久以前,咱們還年輕的時候,在佛蒙特州的就感覺到他的存在,那時我在北穹丘素描,離他大約四、五哩遠。這當然讓他更驚奇了。在春天瀑布底下,嚮導和上了馬鞍的馬在等待,我們沿著步道走,返回旅館的途中一路聊,說起在學校的日子、在麥迪遜的朋友與學生,以及大家如何蓬勃發展等等。我們不時瞥向四周朦朧暮色中逐漸模糊的壯觀巨岩,並再次引用詩人的話——果然是難得的漫遊。
抵達旅社之前,時間已不早,阿爾沃將軍正等待教授回來晚餐。教授介紹我的時
候,將軍似乎比教授更驚訝我從雲之國度直接過來找到朋友,事先完全不知道他在加州。他們直接從東部前來,尚未拜訪加州友人,應該沒有人知道他們在這裡。正當我們坐著用餐時,將軍往椅背一靠,望著坐在餐桌周圍的人,將我介紹給十幾個賓客,包括方才提過,瞪大眼睛的釣客:「你們知道,這位先生從沒有道路的廣大山區下來,在朋友巴特勒教授抵達的這天就出發尋找;他怎麼知道朋友在這?他說,只是憑感覺。聽說蘇格蘭人有預知能力,這是我聽過最奇異的一個例子。」他滔滔不絕地說。教授則引用莎士比亞的話:「賀瑞修,天地間有許多事,已超出你的哲理想像範圍⋯⋯正如旭日在東昇之前,有時會把自己的形象畫在天空;事情發生之前總有跡象,今日的痕跡也已進入明日。」
飯後我們聊了許久麥迪遜的日子。教授要我找個時間,到夏威夷島與他紮營旅遊,而我則設法說服他與我回到內華達山脈高處的營地。但他說:「現在不行。」他不能拋下將軍;我訝異得知,他們明天或後天就要離開山谷。我慶幸自己不夠偉大,繁忙的世間並不會想念我。
| FindBook |
有 15 項符合
我的山間初夏:國家公園之父約翰.繆爾的啟蒙手記(收錄《故道》、《心向群山》作者羅伯特.麥克法倫專文長篇導讀)的圖書 |
 |
我的山間初夏:國家公園之父約翰.繆爾的啟蒙手記(收錄《故道》、《心向群山》作者羅伯特.麥克法倫專文長篇導讀) 作者:原文 John Mui / 譯者:呂奕欣 出版社:臉譜 出版日期:2020-07-03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普通級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我的山間初夏:國家公園之父約翰.繆爾的啟蒙手記(收錄《故道》、《心向群山》作者羅伯特.麥克法倫專文長篇導讀)
——《故道》、《心向群山》作者羅伯特.麥克法倫(Robert Macfarlane)長篇專文導讀——
「我慶幸自己不夠偉大,繁忙的世間並不會想念我。」
與《湖濱散記》、《沙郡年紀》齊名
國家公園之父、環保運動先驅約翰.繆爾的初心所在
喚起世界對自然、環境保育關注的百年重要經典
約翰.繆爾,美國當代最重要的一位自然哲學家與文學家,同時也是發明家、生物學家、地質學家、探險家,從十九世紀末即開始推展近代環境、自然保育運動,他的日記、文章與演說,在國際間掀起環境保育意識,進而催生多座國家公園及自然保護區,被譽為「國家公園之父」和「現代環保運動之父」。而他一生共發表三百多篇文章及出版十多本重要著作,記述他的自然哲學與環保理念,在自然文學上的創新與建樹,與愛默生、梭羅等人齊名,深刻影響了後世。
而謬爾對於自然保育意識的萌芽,就要從本書記錄下的這個夏天談起。
1869年,繆爾受邀跟隨著牧羊人與羊群於內華達山區巡遊,度過一整個夏天。在那裡,他進行著對植物、動物、岩石的研究,同時深受山林美景與生態感動,期間撰述多篇散文隨筆,深刻直接地記錄下於山間的所見所聞,及其內心受到的啟發。
「我初次看見內華達高山,第一眼俯看優勝美地、傾聽優勝美地溪的死亡之歌,以及目睹這條溪飛越龐大的絕壁,每一項都足以成為一生中最珍貴的財富。這是最值得紀念的一日,甚至可以因此狂喜而死。」
「在山間氣息中沉睡就像死亡,醒來時人生又煥然一新!寧靜的破曉時分是黃色與紫色,隨後金色太陽光芒湧現,為萬物染上光芒。」
「這裡沒有痛苦,沒有沉悶空虛的時間,沒有對於過去的恐懼,也沒有對於未來的驚慌。群山得神的庇佑,充滿神之美,沒有空間留給微不足道的個人希望或經歷。飲用如香檳的水是純粹之喜,呼吸充滿生命力的空氣也是;四肢的動作都是享受,全身在接觸到美的時候也能感受得到,就像對於營火或陽光的感受不光是靠著眼睛,還能透過皮膚接收輻射熱,產生無以名狀的強烈喜悅。身體似乎變得和諧單純,和晶體一樣完整。」
「在巍峨山脈的書頁中,會讀到熱與冷、平靜與風暴、狂暴的火山與磨蝕大地的冰川等千萬種風情。於是我們見識到,大自然的毀滅其實是在創造,於不同的美之間轉換。」
這個夏天的經歷對他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使他貢獻一生於自然保育,促成美國政府頒布森林保育政策,更使美國成立全世界第一座國家公園「優勝美地國家公園」。本書中,他直率誠實地記下這段日子在山間的所見所聞,以及大自然帶給他的感悟、讚嘆與洞見,在他優美的筆調如實記述之下,大自然不加矯飾的美躍然紙上,即使著作完成至今已逾百年,我們仍然能跟著文章回到那片尚未受到人為開發的山林之中,以澄淨的心靈之眼,體會自然的純粹之美及其無可取代的價值。
【各界讚譽】
王迦嵐 健行筆記總監
李偉文 作家、環保志工
阿泰與呆呆 【TaiTai LIVE WILD】
徐銘謙 台灣千里步道協會副執行長
張惠菁 作家
詹宏志 作家、PCHome網路家庭董事長
劉克襄 作家、自然生態觀察者
──推薦
山林開放的時代,渴望環境倫理的經典!這本書讓你眼睛不只看著山頂,跟隨繆爾行過夏日山間的腳步,丈量你的心靈與大自然的距離遠近。如果能真正接受冰、雪、雨、雲、河川、地震的隨遇安住,也就能理解,人的需求無非就是一個硬麵包而已。繆爾不只書寫山岳,還是促成國家公園保育的行動者,他啟發後人:自然的大美不是一棵樹或一座山,而是息息相關的生態系構成的多樣與整體,而個人對於保護這種大美具有無可推卸的責任。
——徐銘謙,台灣千里步道協會副執行長
繆爾的散文出奇地親密。他的著作有日月星辰的照亮,山區充滿礦物質的冷冽空氣,以及針葉林的樹脂味也躍然紙上。沒有其他自然作家像繆爾這樣,對於大自然時時感到驚奇,也沒有人像繆爾,急於將那份驚奇傳達出來。繆爾經歷的是「無窮無盡的美麗風暴」,而讀者就和他一起經歷這風暴中。
——羅伯特.麥克法倫(Robert Macfarlane),《故道》、《心向群山》作者
啟發了現代環保主義的關鍵人物,他對自然的熱情和發自內心的熱愛令人印象深刻。所幸,繆爾的散文能喚起那些美好回憶,荒野再次在其中綻放。
——《衛報》(Guardian)
繆爾是一位地質學家、探險家、哲學家、藝術家、作家和編輯,對於他的每一項崇高事業,他都以投注以深刻的洞察力和盡職盡責的精神,這使他成為了大師。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繆爾著作中的豐饒,比我所知的其他荒野作家更深扎於這片土地之中。
——《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
一位偉大的山之人……約翰•繆爾仍然是美國文化生活中如高塔般的存在,也被國際公認為是現代保育的奠基人之一。
——馬克•科克(Mark Cocker),作家
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發現我們對世界做了什麼而感到震驚時,繆爾的崇敬和奉獻精神將迫切重要,可能將使我們的懊悔轉變成為未來而戰的動力。
——愛德華•霍格蘭(Edward Hoagland),美國自然、旅行作家
──詹偉雄 策畫・選書.導讀──臉譜出版山岳文學書系 meters
現代人,也是登山的人;或者說——終究會去登山的人。
現代文明創造了城市,但也發掘了一條條的山徑,遠離城市而去。
現代人孤獨而行,直上雲際,在那孤高的山巔,他得以俯仰今昔,穿透人生迷惘。漫長的山徑,創造身體與心靈的無盡對話;危險的海拔,試探著攀行者的身手與決斷;所有的冒險,顛顛簸簸,讓天地與個人成為完滿、整全、雄渾的一體。
「要追逐天使,還是逃離惡魔?登山去吧!」山岳是最立體與抒情的自然,人們置身其中,遠離塵囂,模鑄自我,山上的遭遇一次次更新人生的視野,城市得以收斂爆發之氣,生活則有創造之心。十九世紀以來,現代人因登山而能敬天愛人,因登山而有博雅情懷,因登山而對未知永恆好奇。
離開地面,是永恆的現代性,理當有文學來捕捉人類心靈最躍動的一面。
山岳文學的旨趣,可概分為由淺到深的三層:最基本,對歷程作一完整的報告與紀錄;進一步,能對登山者的內在動機與情感,給予有特色的描繪;最好的境界,則是能在山岳的壯美中沈澱思緒,指出那些深刻影響我們的事事物物——地理、歷史、星辰、神話與冰、雪、風、雲⋯⋯。
登山文學帶給讀者的最大滿足,是智識、感官與精神的,興奮著去知道與明白事物,渴望企及那極限與極限後的未知世界。
這個書系陸續出版的書,每一本,都期望能帶你離開地面!
▍詹偉雄──策畫.選書.導讀
台大圖書館學系、台大新聞研究所畢業。曾擔任過財經記者、廣告公司創意總監、文創產業創業者,參與博客來網路書店與《數位時代》、《Shopping Design》、《Soul》、《Gigs》、《短篇小說》等多本雜誌之創辦,著有《美學的經濟》、《球手之美學》、《風格的技術》等書。退休後領略山岳與荒野之美,生活重心投注於山林走踏與感官意識史研究。2019年協助青年登山家張元植與呂忠翰攻頂世界第二高峰發起「K2 Project 8000 攀登計畫」,目前專職於文化與社會變遷研究、旅行、寫作。
作者簡介:
約翰.謬爾John Muir
出生於蘇格蘭東洛錫安的鄧巴鎮,1849年,全家搬遷至美國威斯康辛州。年輕的繆爾在父親的農場上,過著刻苦工作的日子。他在一次工廠意外中險些失明,之後開始探索漫步與寫作的喜樂,成為創新的自然作家。他的日記、文章與演說,在國際間掀起環境保育意識,進而催生美國葛蘭特將軍林地(General Grant Grove,隸屬於國王峽谷國家公園)、紅杉(Sequoia) 與優勝美地(Yosemite)國家公園,以及故鄉東洛錫安的數個重要保護區。繆爾備受尊敬,成為現代環保運動之父。
他一生共發表三百多篇文章及出版十多本重要著作,記述他的自然哲學與環保理念,在自然文學上的創新與建樹,也與愛默生、梭羅齊名,深刻影響了後世。除本書外,他另著有《我們的國家公園》(Our National Parks, 1901)、《優勝美地國家公園》(The Yosemite, 1912)、《阿拉斯加之旅》(Travels in Alaska, 1915)、《墨西哥灣千哩徒步行》(A Thousand-Mile Walk to the Gulf,1916)、《陡峭的小徑》(Steep Trails, 1918)等書。
譯者簡介:
呂奕欣
師大翻譯所筆譯組畢業,曾任職於出版公司與金融業,現專事翻譯。
章節試閱
第五章 優勝美地(節錄)
七月十五日
順著莫諾山道,前往谷地東邊接近山頂之處,之後往南走,到優勝美地邊緣小而淺的山谷。我們大約在中午抵達後紮營。午餐後,我急忙前往高地。從印第安峽谷(Indian Canyon)西邊的山脊邊緣可眺望頂峰,那是我見過最壯闊的景色。美熹德河上方的盆地幾乎盡收眼底,有雄偉的圓丘與峽谷、大片黑黝黝的森林往上蔓延,還有一片壯麗的白色山峰直指天際。一切都綻放光芒,散發出的美感宛如火焰之光,注入我們體內。四處陽光普照,沒有一絲風打擾這片沉靜。我從未見過如此耀眼的風景,宏闊的山巒之美如此豐富無...
七月十五日
順著莫諾山道,前往谷地東邊接近山頂之處,之後往南走,到優勝美地邊緣小而淺的山谷。我們大約在中午抵達後紮營。午餐後,我急忙前往高地。從印第安峽谷(Indian Canyon)西邊的山脊邊緣可眺望頂峰,那是我見過最壯闊的景色。美熹德河上方的盆地幾乎盡收眼底,有雄偉的圓丘與峽谷、大片黑黝黝的森林往上蔓延,還有一片壯麗的白色山峰直指天際。一切都綻放光芒,散發出的美感宛如火焰之光,注入我們體內。四處陽光普照,沒有一絲風打擾這片沉靜。我從未見過如此耀眼的風景,宏闊的山巒之美如此豐富無...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導讀——
赤子之心,不免澎湃:繆爾與那一世代人的十九世紀
詹偉雄(文化評論家,meters書系總策畫)
And this our life, exempt from public haunt.
Finds tongues in trees, books in the running brooks, sermons in stones, and good in everything.
我們的生活,沒有人眾的喧豗,但是在樹裏可以發現喉舌,流水裏發現書卷,在岩石裏發現訓誡,處處都可以發現益處。——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劇作《皆大歡喜》(As You Like It, Act II, scene 1, line 15 ),梁實秋譯
The trees encountered on a country strol...
赤子之心,不免澎湃:繆爾與那一世代人的十九世紀
詹偉雄(文化評論家,meters書系總策畫)
And this our life, exempt from public haunt.
Finds tongues in trees, books in the running brooks, sermons in stones, and good in everything.
我們的生活,沒有人眾的喧豗,但是在樹裏可以發現喉舌,流水裏發現書卷,在岩石裏發現訓誡,處處都可以發現益處。——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劇作《皆大歡喜》(As You Like It, Act II, scene 1, line 15 ),梁實秋譯
The trees encountered on a country strol...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登山與現代——meters書系總序/詹偉雄
導讀 赤子之心,不免澎湃:繆爾與那一世代人的十九世紀/詹偉雄
引言/羅伯特.麥克法倫
第一章 隨著羊群穿過小丘
第二章 美熹德河北支流的營地
第三章 麵包缺糧危機
第四章 前往高山
第五章 優勝美地
第六章 霍夫曼山與特納亞湖
第七章 奇特經驗
第八章 莫諾山道
第九章 布羅迪峽谷與莫諾湖
第十章 圖奧勒米營地
第十一章 回到低地
植物譯名對照表
導讀 赤子之心,不免澎湃:繆爾與那一世代人的十九世紀/詹偉雄
引言/羅伯特.麥克法倫
第一章 隨著羊群穿過小丘
第二章 美熹德河北支流的營地
第三章 麵包缺糧危機
第四章 前往高山
第五章 優勝美地
第六章 霍夫曼山與特納亞湖
第七章 奇特經驗
第八章 莫諾山道
第九章 布羅迪峽谷與莫諾湖
第十章 圖奧勒米營地
第十一章 回到低地
植物譯名對照表
|